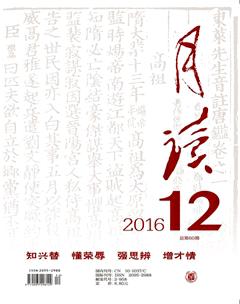黃雀鲊與胡椒
董改正
“鲊”是一種用米粉、面粉等加鹽和其他作料拌制切碎而成的菜,可以貯存,類似腌制。此法古已有之,安祿山得寵時,每月都能得到唐明皇賞賜的“野豬鲊”。而以此“名垂千古”的,是宋代太師蔡京。
《清波雜志》載,蔡府用整整三間房子,堆放“黃雀鲊”,壇子從地面到屋頂,十分壯觀。蔡京雖然不理民間疾苦,但也不會天天在家吃這個。口味再重的人,拿腌制食品當零食也受不了。況且,他飯局肯定很多,胃只有那么大,哪里能吃得了那么多?所以直到他被扳倒時,三屋子“黃雀鲊”也沒怎么動。
胡椒是調味品,如果不開西餐館或是干香料批發,一般不會買很多,因為容易受潮,要時常打理。唐代宰相元載當然不會干這個,他不圖那么點利。胡椒在西方貴重如硬通貨,為胡椒引發的戰爭有很多次,如公元408年,西哥特人與羅馬人的戰爭。西方人不會“鲊”,熱天里,過夜的肉就會有味道,沒有胡椒的烤肉無法入口,所以貴族稀罕,但西方卻沒有出現元載這樣的奇人。
元載出身寒微,做到宰相不容易,智商和權術不會差。但他卻貯藏了八百石胡椒,他把大理寺當成了自家倉庫,胡椒就擺在那里。如何保管呢?書中沒有記載,想必是大理寺的辦公人員在適當的時候,會參與翻曬的。
元載也倒了,滿門絞殺。今日再看蔡京和元載,覺得他們的行為不可思議,失去了理智:哪里能吃得掉?世上所有的荒誕,大概都是出于理智的缺位吧?有個小品寫得好玩,說某人買了幾套房子,從此失眠了。他不是擔心房子跑掉了,而是覺得空在那里可惜,他要讓自己睡一覺醒來,再到另一間房里去睡。其實,荒誕的豈僅僅是追逐
房子?
我們的追逐里,有沒有“黃雀鲊”和“胡椒”?當我們笑別人偏執和荒唐時,我們是不是也在上演同樣的荒誕劇?有多少追逐是必須的?有多少勞心勞力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的?如果仔細思考,會發現我們的屋子里,也堆放了不少“黃雀鲊”,貯藏了不少“胡椒”。
找到自我,找回初心,才能避免陷于荒誕的攫取而忽視本真的幸福,對為官者是這樣,對普通大眾的人世修行也是
如此。
(選自《羊城晚報》2016年8月7日,薦稿人:潘光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