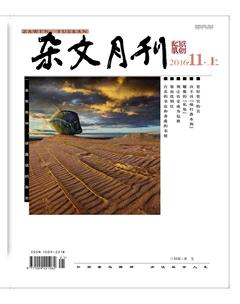“站在死中,去看生”
沈棲
“站在死中,去看生”,這是著名作家史鐵生生前留下的一句名言。戰國時代的列子與當代的史鐵生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倘若來一番“穿越時空”,那么,兩者的生死觀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先說說列子的生死觀。列子是與老莊并列歸入道家流派的。有學者認為,“《列子》除了第一篇《天瑞》的前半部分著眼于對本體論的闡發之外,從第一篇后半部分直到全書末尾,都是對生死理論的表述”,可見生死觀在列子思想中所占據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實,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生死觀,見智見仁,眾說紛紜。
列子是以一套“元氣化生”的理論來詮釋人的生死。他認為:“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人的生命由陰陽二氣和合而成,同時又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死乃是這種變化的終極——氣之聚散而歸于寂滅。列子還明確地將人的“元氣化生”即生命分為四個階段:“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死亡也,則(氣)之于息焉”,向至虛本體回歸,獲得另一意義的永恒的“生命”,這可說是“物質不滅”的另類說法。
列子從多個角度闡述了“身即是幻,而生者必終”的生死觀,旨在打消世人對生的過度眷戀和對死的極度恐懼。一部《列子》的基本思路,我認為就是:從“群有以至虛為宗”的本體論命題出發,經由對認識手段的反思達到對“生實暫來,死實暫往”和“死則返其極矣”的服膺,從而祛除困惑和懼慌,坦然地接受死亡。設若一個人沒有戀生怕死的奢望,那他就能從容地做到“達生樂死”,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過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
史鐵生堪稱列子“達生樂死”理念的當代傳承者和實踐者。史鐵生短暫的一生,命途多舛:1969年到陜北延安地區插隊,21歲生日當天住進醫院,從此再也沒有能站起來。1981年患了嚴重的腎病,手術后只留下一個受損的右腎。軀體的千瘡百孔給史鐵生的內心帶來極大痛苦,寫作成為他精神苦悶的唯一宣泄——以一種文學的詩化手法和自我寬慰的心態去面對苦難和困境。在長達近40年與疾病相搏的時間里,史鐵生似乎承擔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難,但他沒有抱怨,沒有消沉,更沒有絕望;相反,他正確地認清了生與死的本質,用一種“神性”的眼光打量著外界“賜予”他的沉重苦難。他甚至極而言之:“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么?”
似乎沒有資料說明史鐵生生前對列子及其思想有何評說,但人們還是可以清晰地體悟到在他的思緒潛流中不時激起“達生樂死”的浪花。史鐵生雖說病魔纏身,常受生活的重軛,但他明言:“我不想用活著的壓抑來換取身后的余名。”他溫情脈脈地將目光投向人類永恒的美好——愛,并把它視為“站在死中,去看生”的題中應有之義。他愛含辛茹苦的母親,愛和睦相處的鄰里,愛昔日共同求知的同窗,愛在戰天斗地中結下情誼的戰友,愛給他莞爾一笑的路人,愛有志向的年輕人,甚至對小生靈也充滿愛憐之情。一個飽受殘疾之苦、隨時會與“死神”相遇的人卻如此渴求愛、祝福愛,并且以非凡的視角闡釋愛,這需要何等的情懷,何等的哲思!史鐵生清醒地意識到死的必然和生的痛苦,但在“愛”的支撐下,把這一切都詩化并賦予其生命的神性涵義——將生命寓于過程的哲理性思考,同時還有著對精神世界彼岸的殷切期待,委實是其心靈的一種訴求。
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以生克死,向死而生”是近代以來現代科學賦予現代人的生存理念,其實這是“井蛙之論”,至少他們罔顧中國傳統文化,沒能涉獵和認同列子。毋庸諱言,我國長期“樂感”文化的積淀使得人們的哲學視野難以顧及“死”這樣具有一定深度的話題,即便偶爾言之,也多為諸如“不知生,焉知死”之類的遁詞,但列子則不然。而當代的史鐵生更是以其作品粘附著他對生死問題的無限追問和詰疑,其成名作《我與地壇》中云:“我常會一連幾小時專心致志地想關于死的事”,想的結論是什么呢?且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死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我與地壇》);“我有時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為什么還想活呢?因為你還想得到點什么,你覺得你還是可以得到點什么”(《秋天的懷念》);“無論生死,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晝信基督夜信佛》);至于那部長篇未竟稿《回憶與隨想:我在史鐵生》,讀者不僅能夠感受史鐵生面對生存與死亡,尤其是死亡時的坦然,更會為其“用生命寫作”的熱情而動容。——這些充滿良知和睿智的論述幾乎可以解讀為列子“生實暫來,死實暫往”的現代版。
美國耶魯大學哲學教授Simon Critchley曾花了半年時間,結集古往今來190位哲人的死亡故事,編成《哲人其萎》一書,他們在死亡之際都有一個共同的態度:淡定與從容。遺憾的是,此書沒能將我國的列子和史鐵生編入。“誰學會了死亡,誰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靈,就能無視一切束縛和強制。”(蒙田語)在我看來,列子和史鐵生無疑已然臻于這一令人歆慕的人生佳境。
【童 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