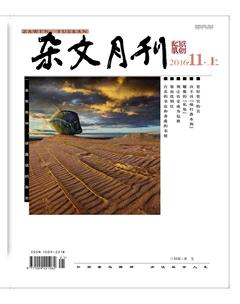閑話“學者當官”
劉天放
有人說學者當官是“死胡同”,不過從歷史上看,并非總是如此。如學者型官員趕上了明君賢主,下場就好;如不幸遇到了昏君,學者當官沒一個有好下場。那句“學而優(yōu)則仕”成就了中國數(shù)千年由文人輔佐帝王治理天下的局面,但知識分子是否善于做官,適應官場,仍是歷史待解的一個課題。
古代官員中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文人學者居多。歷史上,學者當官的大有人在,因為如不當官,就沒有話語權(quán)。《論語·子張》中子夏說:“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即做官之人如果有多余的經(jīng)歷就該學習;讀書人如果還有精力就該去做官,以便進一步推行仁義。當官意味著手中握有權(quán)力,能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在僅靠權(quán)力卻少有民主和法治的環(huán)境下,沒權(quán)力什么事情都辦不成。
而“士”與“官”,一直糾纏不清,士文化的發(fā)揚,也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擔當。有人認為,從唐朝興科舉以來,唐宋時期的房玄齡、狄仁杰、王安石、歐陽修,明清的劉伯溫、張居正、曾國藩、張之洞等都是優(yōu)秀的學者型官員。中國社會素有“官本位”傳統(tǒng),千百年來根深蒂固。做學問相同,而做官的道理也算相通。只是,官場并非學場,有其特殊的規(guī)律可循。所以,學者當官不成功的例子也是舉不勝舉。傳統(tǒng)社會曾是學者為官的天堂,而上世紀初中期一般都是他們做官的地獄,因為封建后期的新時代似乎不太需要傳統(tǒng)士大夫。
如果真有“天降大任于是人”的擔當,真有家國情懷的驅(qū)使,學者當官最好,但這需要合理的制度,恰當?shù)姆諊獠婚_“皇權(quán)即天下”這個死結(jié),學者當官當然下場難看。如想做官不把持人脈,不去溜須拍馬,先當奴才,甚至不去尋租、行賄受賄,熬死也甭想升遷。像當年的傅斯年、胡適那種學者當官的瀟灑,怕是空前吧?龍應臺也屬另類,批判性和獨立思考一直是她的座右銘,可不少人仍批她是“政客”。當理想照進現(xiàn)實,學者型官員并非一帆風順,好像人們的潛意識里,只要當官就掉進了染缸。
當下,官員從上到下幾乎全是大學畢業(yè),碩士、博士也不少,基本都是“學者”。雖然這里也有做官從精神追求到物質(zhì)滿足的某些變化,但身份并沒有多大改變。近年學者掛職也很流行。人們關(guān)注當代版的“學而優(yōu)則仕”,前有王志,后有張頤武。而鍾南山更是好例子。雖然他的官銜有些是虛的,但大家從非典、霧霾等事件上看他,都對他報以專業(yè)的信任。鍾南山名氣大,可他自己也承認,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里,他得罪了不少人。
兩種身份之間來回轉(zhuǎn)換,的確不是件容易事。“獨立”一般作為知識分子的標志。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們不能輕易被資本、權(quán)力等所裹挾。學者是獨立的,而官員必須有“立場”,這一分寸不好把握。從前,不少學者一方面不齒于與官僚集團為伍,另一方面又被官僚階層所左右;“官”與“學”的界限一直就模糊。有人擔心,官員學者化正有呈現(xiàn)庸俗化的趨勢,骨子里仍是“學而優(yōu)則仕”那一套慣性思維在延續(xù)。的確,既想當好官,又要做學問,極為困難。不過,隨著政治的逐漸清明,民眾的認知程度提高,學者型官員更受青睞。很難想象一個不學無術(shù)的官老爺,能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服務中有什么作為。有責任的學者型官員,才有可能把團隊引到正確的方向。由是,好制度下,誰有能力誰做官,至少沒有生命之憂。
【郭德鑫/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