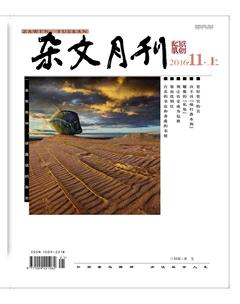“偷對偷”與“騙對偷”
王育棟
上網看意大利導演維托里奧·德·西卡執導的黑白影片《偷自行車的人》。影片講述二戰結束后的羅馬,充斥著失業與貧困。安東在失業兩年后,終于找到一份廣告張貼所的工作,前提是要有一輛自行車。為了這份工作,妻子將床單、床罩等值錢東西當了,買了輛自行車。次日一早,兒子布魯諾將自行車擦得锃亮,安東先騎車送兒子去學校,然后到廣告張貼所領取海報、漿糊等,在老工人的帶領下貼了第一張廣告。孰料當他踩在梯子上獨自張貼海報時,一名小偷偷走了他的自行車。他緊追未果,于是發動老朋友幫助尋找自行車。經過千難萬難,終于發現小偷的住所,卻被其鄰居團團包圍,幸虧機警的兒子找來警察解圍,他與警察進到小偷屋子里搜查,房間里一貧如洗,哪有自行車的影子。沮喪之余,他在一家體育場外發現樓門口停著一輛無人看管的自行車,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趁比賽散場混亂之際,他毅然上前,誰料剛推自行車,就被主人發現,逃脫未果,被眾人押往警察局。兒子沖進人群,拉著他大哭,直叫“爸爸、爸爸”,主人心軟,放了他,讓他“給孩子做個榜樣”。影片的結尾,安東木然地走在大街上……看完影片,心情無比沉重,六十多年前羅馬底層民眾的艱難生活仿佛如在眼前!
由此影片,不由想到了自己。我們是自行車大國,丟自行車的事可謂家常便飯。我自己便被偷過兩輛。1984年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實習期月工資四十五元,一輛“永久”牌二八自行車要一百多元,還得托關系才能買到。爺爺用賣棉花的錢給我買了輛。物理系的張虎帶學生春游,借去騎,發生車禍,被一輛大卡車將前輪撞成麻花狀,所幸人無事。司機將車修好后,賠了一百元。此車我調回臨汾后一直騎著,結果一天中午午休時,上鎖后停在家屬樓外,被人偷了。我當即趕到二手自行車市場尋找,毫無蹤影。后來,妻子的那輛“飛鴿”二六自行車也在地下室被偷了。一輛自行車,相當于我近三個月的工資。好在我不像影片中的安東,全靠它謀生,否則真是慘了,只當是破財消災。還有一事,師大保衛處一干事講,某天,進行體育生面試,一考生見有人給考官送禮,可他身無分文,于是起了歹念,在學校辦公樓前,瞄上了輛女式自行車,下手,正巧被這名干事看到,發現其所偷正為妻子的自行車,于是上前將其捉住。偷自行車在中國一度很普遍,當然與貧困難脫干系。可我們何曾拍過半部《偷自行車的人》?
巧的是,前幾日,一大學同學分享了個視頻。一男司機開輛別克商務車,靠邊停車,去另一邊撒尿。這時,過來個小偷,透過車窗,發現車座上放著手機與一沓百元大鈔,于是試圖撬開車門,被主人發現。主人問:“伙計,打不開是不是?”小偷點頭。主人亮出一把大鑰匙,上面印有“開鎖”字樣,“專業開鎖的,二百塊給你搞定”。小偷拿出二百元來。主人用遙控器打開車門,坐了進去,鎖上車門。小偷著急地說:“把車門打開,讓我進去!”主人徐徐搖下車窗說:“開你娘的腳,這是我的車,瓜慫!”踩下油門絕塵而去。如果說在《偷自行車的人》中,清白之人安東是被逼偷車,以偷對偷,留給觀眾的是無盡的思考;而此視頻中,那名車主用騙的手法來對付偷車賊,帶給觀眾的則是幾聲干笑。前者讓人在同情弱者之余,也對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現狀進行反思,考慮如何改變它;而后者的滑稽結尾,除了贏得幾聲廉價的笑聲外,還剩什么?
說到別克商務車,再補充一事:女兒在美國南達科他州阿伯丁市留學時,其房東開一輛別克商務車,停車從來不鎖車門。一次去購物,回來發現車里竟坐著名男子,正試圖用鑰匙發動車輛。他上前詢問,該男子言“我怎么用鑰匙發動不了我的車子了”。原來該人也駕駛一輛同樣的別克商務車,也習慣了不鎖車門,這是上錯車子了。順便補充一句:影片中,羅馬人的自行車也都是不上鎖的。
【王 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