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地
三井獸
在紐約的洛克公園,人們會爬到屋頂或樹上去看“J博士”的比賽;在路易斯維爾和肯塔基,阿蒂斯·吉爾摩爾會隨時停住昂貴的跑車,穿著昂貴的西裝便上場打球;凱文·杜蘭特在華盛頓的街球場,第一次發現了自己的價值;而亞瑟·阿吉則在芝加哥的場地追尋著自己的籃球夢;費城的室外球場證明了真正的好球員就是從這里走出的;而在洛杉磯,那些綽號“野獸”、“鋼鐵俠”或者“大亨”的街球傳奇,擁有跟“魔術師”和科比一樣的光環——這就是10年之前的街頭籃球——現在?球場空了,球網孤零零地隨風搖擺,曾經瘋狂的觀眾都不知道去哪兒了,而那些優秀的球員也隨之消失了。他們曾經被問道“誰會成為下一個明星?”現在這個問題變成了“還有誰想打球?”而答案是幾乎沒有。至少不是在這里,不是在街頭。到底發生了什么?籃球誕生于街頭,但現在屬于街球的光芒消失了,這里變成了黑暗之地,不論在球場,亦或是球迷心里。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一切都沒有了。”前馬里蘭大學明星球員厄尼·格拉漢姆說道,他曾在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的街球場留下過輝煌。這并不是某一原因造成的,現在的球員更喜歡在室內打球,他們想通過更有組織的比賽來展現他們的水平,而不是在街頭的小比賽中獲得名氣。同時,他們不想冒著受傷或者暴力的危險,畢竟NBA和NCAA都有休賽期。“很多人都不認為街球還有價值。”猛龍后衛凱爾·洛里說道。
這種態度在很早就有苗頭了,高中球員在假期都會把精力放在各種訓練營和比賽,AAU(業余體育聯盟)或其他業余比賽也都搬進了室內。“AAU是為每個人準備的大舞臺。”湖人后衛德安吉洛·拉塞爾說,他曾是一名從俄亥俄轉學到路易斯維爾的五星畢業生,“如果你沒打過AAU,要想走出自己的小鎮就要靠運氣了。AAU會幫助任何孩子,你可以優先進入頂級大學,有機會和頂尖的同齡球員較量,你能一舉成名。”
室內比賽的吸引力不僅僅是對名利、獎學金或未來的追求,這里更加安全,比室外的突發情況更容易控制,畢竟建筑物有墻壁和私人入口,而你不能在每個公園都放置一個金屬探測器。“如果沒有嚴格的審查和設置,你不可能在一個普通的公園里見到勒布朗·詹姆斯打球。”名人堂成員吉爾摩爾說,“現在的孩子們比我們那時候更重視人身安全,而在室外,他們的安全往往得不到保障。”
雖然NBA球星們的安保措施很完善,但他們也不太可能出現在街頭球場。科比曾在加利福尼亞的威尼斯海灘弄傷了自己的手腕,阿里納斯也在華盛頓當地的古德曼聯賽中傷了膝蓋,并影響了職業生涯。傷病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缺席比賽以及影響賺錢,街頭比賽緊密的日程對球員身體的損耗是不可估量的。“多米尼克·威爾金斯在室外打球,他也能跳得起來。”塔拉斯·布朗說道,他是資深的AAU教練,也是凱文·杜蘭特的教父,“但他們總說擔心自己的膝蓋。你的膝蓋在40歲的時候同樣也會損傷,他們就是不想在外面打球而已。”
NBA球員不再在室外打球,很大一部分NCAA球員也不會再到公園里打球,因為大學有夏季聯賽的規則。“暑期對于學校來說很普遍,但我為我的球員們感到抱歉。”岡扎加大學主教練馬克·費尤說,“他們只會休息 10天,然后第一期暑假練習就開始了,而一周后第二期又開始了。以前你會在5月份讓隊員們放松,但現在必須給他們一份訓練計劃,并且希望他們做到上面的一切。”孩子們依然想打籃球,也依然在打籃球,不過卻不是在他們習慣的室外球場了。
下面就來一場全美街球之旅吧,領略一下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路易斯維爾、費城和華盛頓的街頭球場風采,了解它們的曾經,看看它們現在的樣子,并且尋找我們失去的東西。
紐約
鮑勃·麥卡洛還記得一對來自法國的夫婦沿著紐約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道散步時,發現了一個銹跡斑斑的牌子掛在街邊的柵欄上:洛克公園。“他們停下來,拍了一張照片。”麥卡洛說,微笑蔓延在這位73歲的老人臉上,“每個人都想在這里打球,每個人都聽說過洛克公園。”如果有一個街頭籃球的圣地,它一定就在第155號大街附近,比鄰哈林河。
老一輩的人都習慣把它稱為“哈林花園”,這并不夸張,因為如果麥迪遜廣場花園被稱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籃球舞臺,那么這里就是它在戶外的“兄弟”。在這里,朱利葉斯·歐文被現場播音員稱為“利爪”,而不是“J博士”;在這里,阿倫·艾弗森和斯蒂芬·馬布里組成了夢幻后場;在這里,“跳躍的靈魂”拉夫·阿爾斯通從當地的傳說成長為一名NBA控衛;在這里,賈巴爾、威爾金斯、張伯倫、詹姆斯、科比、杜蘭特,以及其他很多超級巨星都曾遭遇“滑鐵盧”。
這里讓街頭籃球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洛克依然有足夠的影響力,但它現在已經不是真正的洛克公園。老視頻中球迷爬上屋頂和樹梢看球的場面消失不見了,在7月份的一個晚上,兩屆衛冕經典娛樂籃球錦標賽冠軍肖恩·貝爾對抗D.G.菲爾姆斯的比賽幾乎沒有人來看,就連貝爾替補席上的座位都是空的——洛克可能是每個人都想上場比賽的地方,但貝爾的團隊只能派出6個人。“它已經變了。”在34年前創立EBC聯賽的格雷格·馬魯斯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在打籃球,而現在他們都在做其他的事情。”
這與暴力無關——馬魯斯不允許任何籃球之外的活動在這里發生,或許其他地方充斥著大麻和酒精,但洛克不可以。穿著橘色背心的安檢員會在球迷入場前檢查每個人的背包,警察也會在球場內外巡邏,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籃球,而不是披著籃球外衣的馬戲團。這也與傷病無關——兩年前,洛克公園就鋪上了木質地板,晚上還會蓋上防水布,到了寒冷的冬天就被收起來妥善保管。在潮濕的天氣里,這里可能有點兒滑,但如果下雨,比賽就會被搬到附近的球館里,所以球員們不能抱怨地板的磨損會導致受傷。
洛克公園的問題其實就是整個街頭籃球問題的根源,這里就是沒有足夠的球員。“每30個街區就有一個錦標賽。”馬魯斯說,他指的是洛克聯賽、擁有24年歷史的迪克曼聯賽、曼哈頓的亨特大學聯賽以及布朗克斯的果園海灘聯賽,“很多球員都會一個接著一個地打比賽,就像流水一樣一路走來。”當然,誰曾在這里打過比賽并不重要,人們在意的是當下看到什么樣的比賽。
霍克比·洛克在1947年創立之時只是希望給孩子們做一些積極的事情,麥卡洛就是被洛克照顧的孩子之一,洛克的妻子瑪麗總拿兩人的親密關系開玩笑。“我就像他們的私生子。”麥卡洛說道。
洛克在1965年死于癌癥,而麥卡洛在完成了本尼迪克特大學的學位后,接管了其導師的職責。他開始設置一些簡單的規定,并且為有興趣的球員提供球衣。不久,洛克公園就成為了比賽場所,但當時的球迷并不喜歡“J博士”,他們心中的傳奇是像弗雷德·布朗和“山羊”這樣的街球手。
在今年的開幕慶典上,布朗穿著卡其長褲和深色襯衫站在洛克公園的門口,他的身材依舊壯碩,但是并沒有上場打球的計劃。他回到這里只是很開心,因為這是讓他成名的球場。“人們并不在乎你是20歲、30歲還是50歲,只要你熱愛比賽,你在這里打過球,人們就會尊敬你。”布朗說,“只是現在這里更加商業化,人們來到這里只想看到某些球星,但我們是來看比賽的。”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甚至洛克都沒有辦法解決。事實上,NBA和大學比賽都有電視轉播,曝光的程度越高,球員越關注自己的價值。“當詹姆斯·哈登在停擺期來這里比賽的時候,他僅僅出場了5分鐘,整個城市就被圍得水泄不通。”迪·蘭卡斯特說,他當時是哈登球隊的教練。但如果只是布蘭登·惠特克,這個紐約當地孩子在二級聯盟的康科迪亞大學只是名普通的球員,觀眾可以不買他的賬,那么兩屆錦標賽MVP肖恩·貝爾又怎么解釋呢?為什么在舒適的7月夜晚,來到洛克公園欣賞一場純粹的籃球比賽對人們來說就那么難?
“就算天氣很熱,如果有球星來打比賽,這個地方都會被擠滿。”馬魯斯說,“可人們只有在大人物來的時候才會想起洛克公園,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不知道籃球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20年后,洛克公園依然會在這里,我的孩子可以接替我的工作,但我不確定這里的未來。”
洛杉磯
在威尼斯海灘,“野獸”這個名字如雷貫耳,但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住處和手機號碼,因為在球場上,比賽就代表著他的名字。“野獸剛剛離開。”布萊恩·C·瓊斯說,他十分了解洛杉磯的籃球格局,因為這塊場地就是他曾經的生存地。
多年前,威尼斯海灘和洛杉磯其他街頭球場一樣,出產過許多“沒有名字”的傳說,如果你表現得足夠厲害,就可以得到財富和地位。但隨著歲月的流逝,西海岸最好的球員們開始在拋光的地板上,以及有空調的健身房中打造自己,并對水泥球場嗤之以鼻,而他們的天賦也正被逐漸剝奪。
你可以很容易就在谷歌上搜到身高1.98米,體重118公斤的“野獸”泰倫·威廉姆斯,畢竟他贏得了2013年紅牛之王街頭籃球聯賽的冠軍,但要想在街頭球場找到他并不那么容易。“街頭籃球在加州……已經淡化了。”威廉姆斯說,這位傳奇前鋒來自二級聯盟加州州立大學圣伯納迪諾分校,而他的綽號正是拜洛杉磯街球的標簽人物拜倫·戴維斯所賜,“現在的孩子不像我們會到水泥球場上打球了。”
這是事實,那些見證過街頭籃球最輝煌時刻的名字早已漸漸被人們淡忘了——“跳躍的喬伊”、“鉤子”、“糟糕的圣誕老人”、“小蟲”、“野獸”,這些人在70年代至90年代間相當受歡迎。“街球已死。”喬恩·納什說,為了把洛杉磯籃球帶回室外,他在2008年創立了威尼斯籃球聯賽,“我不想這么直白地表達,但是……”
在6月假期的第一個周末,尋找天使之城的街球高手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追求。棕櫚公園?一個男孩投了幾個籃然后就跑掉了;海洋公園呢?美麗的鵝卵石填滿了整潔的圣塔莫尼卡社區,但球場空無一人;馬維斯塔公園倒是有多個球場可以用,但只在中午開放,而且打不了5對5;達比公園終于有場正規的比賽,可惜那里的街球手輸給了一支一級聯盟的大學女子球隊。
“這里已經不像從前了。”前華盛頓州大的后衛杰里·麥克奈爾說,他只能跟一個朋友在韋斯特切斯特公園空蕩蕩的球場上單挑。而在羅杰斯公園,一群青年人踩著滑板從長滿枯草的小山上滑下,這項運動看上去遠比籃球受歡迎。
對于德懷恩·保利來說,這是一個困難,也是一個現實。他曾是洛杉磯有名的街球手,少年時期曾加入過NBA名人堂成員邁克爾·庫珀、馬奎斯·約翰遜和“魔術師”約翰遜在英格爾伍德組織的籃球對抗賽。“那時候,洛杉磯所有偉大的球員都會和隊友們一起在暑假來到街頭球場,和這里的孩子們一起打球。”保利說,他曾為佩珀代因大學效力,并在1986年的NBA選秀大會上被快艇隊在第三輪第7位選中。“‘魔術師來打球的時候從沒帶過保鏢,這些家伙就是想舒服地打場球。”
現在,職業球員們還會舒服地打球,但他們不會去室外。當NBA在2011年陷入停擺的時候,德魯聯賽吸引了很多NBA球星,詹姆斯、科比、杜蘭特都來到這里,路虎和寶馬停滿了體育館周圍。“野獸”和他的女朋友走上紅毯,拜倫·戴維斯是一支球隊的教練,來自西海岸的說唱歌手尼普西·胡塞爾也坐在前排觀看比賽。“競爭太激烈了。”前南加州大學的球員J.T.特雷爾說,他也參加了比賽,“這里有我喜歡的一切,它是洛杉磯最好的籃球聯賽,你能享受到其他地方都沒有的專業籃球。”
有很多理論都在試圖解釋洛杉磯籃球離開街頭的原因,比如有的人不想毀了昂貴的球鞋,有的人擔心受傷、暴力,但它可能沒那么復雜,精英球員尋求最高競爭,只是在2014年之前,它不是一直在戶外進行嗎?
如果你的運氣好,可能會在洛杉磯街頭看到一場精彩的比賽,但那真是太難了。馬維斯塔公園在白天空空如也,可傍晚之后,這里也會人頭攢動,三個球場上都有比賽,人們想要找出下一個燈光球場的霸主。德米特里·米勒今年18歲,周五晚上他會用25分鐘車程從洛杉磯中南部趕到這里,他總是在尋找好的公園球場,同時希望洛杉磯其他公園也能有這樣的競爭性和活力。“你不能只去洛杉磯的一所公園打球。”他說。
威尼斯海灘正在播放著《白人不能飛》,可更多人還想看到“野獸”和他的隊友們的比賽。只有13歲的年輕DJ“Kiss”正在臺上搖頭晃腦地說唱,并把其團隊的品牌T恤發放給臺下的觀眾,而VBL聯賽的主持人莫斯皮正用充滿娛樂性的嗓音介紹了即將上場比賽的球員。
在這場以七十年代球員為主的表演秀中,雙胞胎兄弟“馬里奧”和“路奇”是為數不多的白人球員,但“野獸”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么娛樂性。他的投籃被犯規干擾了,然而并沒有得到哨聲。“嘿,他犯規了!”這位VBL聯賽的三屆MVP朝著裁判喊道。
對他來說,街頭籃球不只是一種消遣,它代表著一切。但事實呢?就像這場糟糕的比賽一樣,街球籃球的本質正在悄悄溜走。
芝加哥
無論何時,只要賈巴里·帕克來到芝加哥南部的街球場,他的父親桑尼·帕克都會叫上自己的朋友來看兒子的表演。“當然,很多地方都是不安全的。”曾在1976年選秀大會第17順位被選中的桑尼說,“過去,我們都會收到一些警告,‘小心點兒,兄弟。但現在不一樣了,當賈巴里來到公園打球時,我必須得讓所有人都知道他來了。”
暴力在美國是一個常見問題,特別是芝加哥。在這座美國街頭籃球最發達的城市中,警察夏天會在公園中加班來遏制犯罪。2012年,芝加哥已知的謀殺案就有503起,是全美最高的。2013年,這個數字稍有下降,但415起謀殺案依然是全美之首。在這些罪行發生最多的地方,正是公園和街頭球場。“公園越來越危險了。”芝加哥中部著名的圣塞賓納教堂神父邁克爾·弗萊格說,“現在買把槍簡直比買臺電腦都容易。”
暴力事件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重大負擔,它也成為很多街頭球員恐懼的因素。“暴力是芝加哥街球的一部分。”當地的體育營銷員羅伯·格拉漢姆說,“我曾經開車考察芝加哥街頭的每個球場,但它們和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樣了。”邁爾斯·羅爾斯是華盛頓古德曼聯賽的工作人員,他曾經為了耐克街球錦標賽的籌辦而到其他城市考察,考察的結果是——把比賽從街頭搬到室內。“我打電話告訴他們的工作人員,‘你還是別想在芝加哥辦比賽了。”羅爾斯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人會在街頭球場上打球。”想想看,室外錦標賽不得不搬到室內,多么滑稽。
在西區的一條街上,幾乎每一家的窗戶都是由碎玻璃和鐵柵欄組成。穿過這條街卻是另一番景象,修剪整齊的灌木以及兩層高的石頭墻圍繞著私人花園,一直延續到加菲爾德公園的西側。亞瑟·阿吉把車停在他小時候住的房子前,慢慢落下車窗。“跟我來。”阿吉說,這位芝加哥本地球星在1994年主演了紀錄片《籃球夢》。他開著SUV穿過小巷,直奔曾經讀書的德拉諾小學。他叼著雪茄下了車,看著空蕩蕩的操場,失望地搖了搖頭。
在這塊球場上,阿吉曾經用眼花繚亂般的籃球技術征服了導演史蒂夫·詹姆斯,于是他的經歷被拍成了電影,并奪得了1994年圣丹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6月中旬,阿吉與幾個朋友——包括曾經出現在《籃球夢》中的香農·約翰遜——來到這里拍攝一部電視真人秀。這里沒有打球的孩子,也沒有比賽,籃球重重彈擊水泥地的聲音已經消失了。阿吉并不驚訝。“這里已經變了。”他說,“人們都想遠離暴力,但這里一點保護措施都沒有。”
為了看一場比賽,約翰遜小時候不得不爬到學校的房頂,那時候從來沒有人來搗亂,球場是最安全的地方。“這里曾是神圣的地方。”約翰遜說,“現在卻隨時可能經歷流彈。”
沒有一點跡象顯現這塊球場能夠熱鬧起來,但阿吉沒有喪失信心,他確信下一站會有一番火爆的場景。“嘿,我們去加菲爾德公園!”他說。但那里同樣清靜,而其他社區公園同樣如此。由“小孩”比利·哈里斯統治過的著名的杰克遜公園不再擁擠;一個父親領著孩子在林肯公園孤獨地投著籃;五個年輕人在霍納公園打著球,四個籃筐上連球網都沒有;附近的加利福尼亞公園球場同樣寥寥幾人。
這不應該是芝加哥應有的籃球氛圍,已經擁有幾十年歷史的西蒙高中和惠特尼高中誕生過無數的籃球天才,德懷恩·韋德、德里克·羅斯、安東尼·戴維斯、托尼·阿倫都是從這里走出去的,而賈巴里·帕克和賈利爾·奧卡福也是NBA的希望之星,而他們都是標準的“芝加哥制造”。
如今你已經很難在室外找到有天賦的球員,精英們都在耐克聯賽里打球,桑尼·帕克也會組織一些室內聯賽。芝加哥有這樣一個規定,每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都會對外開放所有體育館,給當地的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打球場所”。“你在公園里看不到最好的球員。”桑尼·帕克說。
暴力在這里并不只是電視新聞,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孩子們每天上學前都被叮囑要走安全的路線,阿吉的父親就在2004年遭到搶劫并遇害,而弗萊格神父的兒子也在1998年被殺害了,地點就在距離教堂三條街的地方。弗萊格試圖用籃球帶來和平,他在教堂組織了和平籃球錦標賽,讓那些敵對幫派的成員和平共處。
打籃球確實能讓人短暫地忘記這座城市的混亂,43歲的阿吉最終在摩爾公園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這讓他仿佛回到了剛打球的時候,不過現在他已經不能用花哨的腳步來戲耍對手了。這里沒有惡意犯規,一切都是按照規則來的,但阿吉很享受這里的一切。他組建了自己的球隊,教會青年人團結與和諧的氛圍。“我的過去都已經是回憶了,現在,我感覺很好。”他說。
這曾經也是桑尼·帕克過去的生活方式,他整天都呆在球場上,一伙人走了就等著加入下一伙,他從來都不會感到孤單。在一個街區里,打得最好的孩子們會接到另一個街區的挑戰,而他們也會在比賽后成為朋友。這就是街頭籃球的本質——競爭和尊重。
華盛頓/巴爾的摩
NBA傳奇摩西·馬龍曾在“大M錦標賽”被評為MVP,馬里蘭大學的明星球員厄尼·格拉漢姆也是在這些比賽中一步步成長的,喬治城大學的傳奇教練約翰·湯普森在這里發現了埃德·斯普里格,他曾是帕特里克·尤因的親密戰友。“大M錦標賽”是梅爾文·羅伯茨贊助發起的,他還為比賽修建了球場,位置就在華盛頓與馬里蘭的交界處東林蔭道700號。
羅伯茨將球場建在了自己的梅爾文餐廳旁邊,人們可以在夏天的晚上一邊用餐一邊欣賞本地球星的表演。“人們來到這里就像參加野餐一樣。”每次都會特地從巴爾的摩驅車趕來的格拉漢姆說,“你在這里幾乎能看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優秀球員。”
從巴爾的摩球場到馬里蘭西雅特市的國王球場,從華盛頓的古德曼聯賽到梅爾文錦標賽,比賽氣氛非常歡樂。以前,這些球場上白天到處都是熱愛籃球的孩子們,晚上的比賽更會聚集很多球迷前來觀戰。當杜蘭特還是個13歲的孩子時,他的教父兼導師塔拉斯·布朗把他帶到了國王球場,讓他在這里鍛煉球技。“他需要在良好的環境下打球,這里的氣氛非常合適,每個人都不想輸。”可現在,這些球場非常安靜,即使是明媚的6月午后,這些曾經熱鬧非凡的球場都空無一人。
梅爾文錦標賽沒有了,餐廳也已經倒閉10年了,創始人梅爾文已經在2011年去世了。“現在一切都沒有了。”格拉漢姆說,“我的兒子24歲,他在馬里蘭大學打球,他從未在室外場地打過球。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總覺得我們討厭室內的比賽,可他們同樣應該理解我們的經歷,知道我們為什么喜歡在街頭打球,這些都是他們從未經歷過的。”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與其他地方沒什么不同——AAU錦標賽占據了大多數孩子們的暑假,大學球員都會在夏天參加訓練營,暴力事件在球場上屢有發生,但真正將馬里蘭、華盛頓和弗吉尼亞地區的街頭籃球扼殺的,是人們漠不關心的態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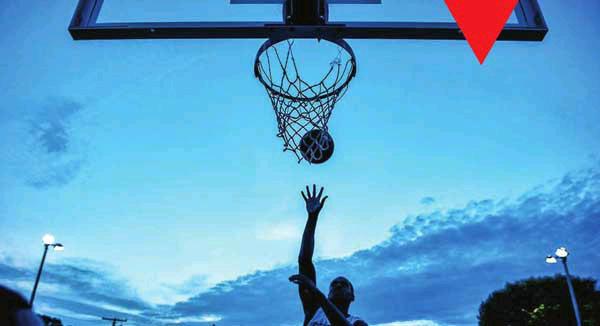
由于利益的驅使,街頭比賽的主辦者越來越少,比如在巴爾的摩,當79歲的洛倫佐·普拉特與世長辭后,他所創建的巴爾的摩籃球協會也解散了。華盛頓有兩個著名的聯賽,分別是杰夫·約翰遜在華盛頓東北地區創建的沃茨聯賽和邁爾斯·羅爾斯在東南部創立的古德曼聯賽,但它們并不能幫助街球復蘇。“我們可不想坐以待斃。”約翰遜說,“我不想看到自己喜歡的街球就此消失。”羅爾斯的想法也和他一樣。“當修建球場的時候,它就注定要在那里了。”在談到古德曼聯賽時,羅爾斯說,“為的就是讓我們在街頭打球。”
羅爾斯見證過古德曼聯賽為華盛頓帶來的一切:《華盛頓郵報》稱,在2011年,球場周圍100英尺內的犯罪率為零,但他也明白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么。從1996年開始,他就是古德曼聯賽的組織者,是他讓這個一度面臨解體的聯賽走到今天,但只有羅爾斯一個人是不夠的。為了讓這個古老地區煥發活力,政府決定在這里發展零售業,還要建地鐵站和新房子——這些新規劃都可能會在籃球場附近。即使球場本身的條件得不到太多改善,周邊建設的改變也能帶動球場打球的人群。“我就是從這里開始打球的。”正在場邊看孩子們打球的休·瓊斯說,或許他在AND1的綽號“小鯊魚”能更被人熟知,他現在已經36歲了,曾經在古德曼聯賽打了13年。“我總會在場邊等著上場打球,這就是我童年最重要的事。”
街頭球場就是聯結社會的紐帶,現在你能在古德曼聯賽中感受到它全盛期的輝煌。晚上7點之前,人們就紛紛來到球場,一些人會在球場的角落里隨便買點東西當晚餐。查爾斯·福爾摩斯是“季票擁有者聯盟”的領頭人,他通常會自己站在邊線處等待比賽的開始,14年來,他從未錯過比賽。球員熱身時,一個女孩騎著摩托車穿過球場,現場DJ帶著三個人搖擺著身體走了進來,在倒數第二場比賽開始前,球場里開始放進大量煙霧。54歲的羅爾斯在兩個當地人的陪伴下走進場地,他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拿著熱狗,跟已經在場地里的裁判打著招呼,享受著全場觀眾的歡呼和掌聲。
這里曾有這個城市最好的球員,16歲的杜蘭特在這里被完爆后馬上又完爆對手,泰·勞森也曾是最受歡迎的小個子,他們面對的對手甚至比某些NBA球員更好。現在,古德曼聯賽成為了大學畢業生們保持狀態的地方——他們往往沒有球隊接收,來到這里是為了保持狀態,等待著職業球隊的召喚。
由于古德曼聯賽并沒有得到NCAA的認證,之前并沒有頂尖的大學球員在這里比賽。不過5年前,羅爾斯花了1800美金在NCAA注冊成功,可還是很少有大學球員來這里打球——他們都會呆在喬治城的麥克多諾球館。當一個聯賽沒落時,我們只能目送它遠去。“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算不上頂尖的球員。”格拉漢姆說,“但我曾經和最好的球員一起比賽,我也曾在這里擁有屬于自己的球迷,他們為我歡呼,還會穿著我的T恤為我加油,可現在這樣的場景已經一去不返了。”
路易斯維爾
憑借著膽識和希望,“扣籃怪人”達瑞爾·格里菲斯帶領著路易斯維爾闖進了1980年的全國決賽。在上世紀70年代早期,年輕的格里菲斯經常開著車到肖尼公園,找效力于肯塔基上校隊的阿蒂斯·吉爾摩爾打球。那時候,格里菲斯是無法阻擋的。“我記得有一次,阿蒂斯退回籃下防守,達瑞爾運球直沖籃下,他高高飛起將球扣進籃筐。”肖尼公園的DJ布拉德利說,“伙計!要知道那可是在吉爾摩爾頭上扣籃啊!全場的觀眾都瘋狂了!”但吉爾摩爾本人可不承認這件事:“我不記得被他扣過。”
雖然街球文化在不斷變遷,可肖尼公園的聯賽一直在這座城市的角落里固執地存在著,不知不覺間已經走過了46個年頭。1969年,曾經在杰克遜州立大學打球的本·沃特金斯想要在這個地區建立一個最好的聯賽,于是肖尼公園聯賽誕生了。人們很快就接受了它,沃特金斯還記得,肖尼公園最多曾涌入了6000多位觀眾,那簡直讓格里菲斯、吉爾摩爾和名人堂球員威斯·昂塞爾德眼花繚亂。
如果有什么原因能讓街頭籃球煥發新生的話,那就是它能讓城市的人們在周末多了一個休閑的好去處,很多人并不想讓街頭籃球搬進球館里。“這里的人們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讓更多民眾能夠來街頭球場打球。”曾經在肖尼公園打球的高中明星尼爾·羅賓遜說——他現在是西路易斯維爾的區長。
6月末的一個周日,球員們冒著33度的高溫揮汗如雨,超過20支球隊在打比賽。而在場地外,10多名當地的警察在比賽現場巡邏。自上世紀90年代后,肖尼公園也受到了暴力的侵害,5年前就發生過三起槍擊案。“這里曾經罪惡滋生,幾乎每天都有暴力發生,人們根本無法愉快地打球。”肖尼公園曾經的管理者拉里·伍德斯說,“但現在情況好轉了,我們擁有嚴密的安保措施,可以盡情享受夏天打球的樂趣。”肯塔基上校隊也曾經在這里打球,他們會和那些高中球隊比賽,讓那些毛頭小子領教一下職業球員的厲害。當然,有時候他們還會和大學球隊比賽。在肯塔基,如果你在肖尼公園打過球,那可是一個非常值得自豪的經歷。
現在,路易斯維爾的人們還會在街頭球場上看到格里菲斯、昂塞爾德和吉爾摩爾這樣的傳奇人物,但那些希望之星基本上不會到這里來,比如蒙特雷斯·哈雷爾,這位火箭內線盡管還沒有在NBA中真正證明自己,但每個人都期待著他能來到肖尼公園打球,不過他本人顯然不這么想。“我沒有什么需要證明的。”哈雷爾說,“我也沒有什么想要戰勝的對手,我的目標和對手都在NBA。”像哈雷爾這么想的人不在少數,高中聯賽的崛起讓許多天才遠離街頭。阿爾岡金公園、切卡索公園和懷安多特公園本來和肖尼公園一樣,是路易斯維爾本土天才球員的樂園,可現在他們都不愿意在這里打球了。“高中聯賽改變了一切,它讓街頭球場不再是年輕人的最佳選擇。”路易斯維爾公園管理處的主任馬蒂·斯托奇說。
當然,還是有人在室內和室外兩種模式間自由切換,阿德里安·迪爾曼就是這樣一位教練,他會帶領球隊參加肖尼公園的聯賽,同時他也在執教著夏夫利高中女子球隊,他的女兒賈瑪麗就效力于這支球隊。為了讓球員們經歷專業訓練,迪爾曼特別雇用了一名私人教練,賈瑪麗也會客串助理教練,訓練隊友們的腳步。幾周前,迪爾曼帶著他的女孩們來到了肖尼公園,他想讓自己的隊員們感受一下,自己小時候最愛的路易斯維爾籃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人山人海的公園里,迪爾曼的隊員們都走散了。最后,他在一塊位于角落的場地里找到了她們——這群女孩正在和一支男子球隊比賽。在迪爾曼載她們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個街頭球場時,她們還強烈要求停車,下去看看有沒有什么其他的對手能打一場。“她們非常喜歡街頭球場。”迪爾曼說,“這讓我非常驚訝。”
費城
在費城的切拉舒爾球場中間,一道夸張的裂縫將場地分成兩半,看起來就像地震過后留下的地表斷層。當賈奎安·紐頓運球突破防守后想要進行下一步動作時,他踩到了小石子,重重摔了一跤。周圍的人們都被嚇了一跳,因為這一下摔的太重了。“該死!”賈奎安大叫一聲。
他的父親喬·紐頓從看臺上站起身來,看了兒子一眼后,又緩緩坐下了。幾年前,喬帶著兒子來這里參加比賽,曾經身為一名NCAA球員的他深深地了解,想要當一個合格的控衛——父子二人都打這個位置——絕對不能只靠在球館中機械式的訓練和毫無身體接觸的比賽,街頭球場才是磨煉優秀后衛的地方。于是,他帶著兒子來到了這里——一個位于費城西南部、曾經被他稱之為“家”的地方。后來,賈奎安接到邁阿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你看到他摔倒后的樣子了嗎?”一個小時后,喬·紐頓對索尼·希爾說,“我是說,伙計,他要去邁阿密了,這么嬌氣可不行。”
希爾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在他的記憶中,費城的街頭球場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比賽和各式各樣的天才球員。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會在各個球場間穿梭,并能遇到很多NBA球員。他的投籃技術就是跟費城傳奇蓋伊·羅杰斯學的,當然,他也見過籃球史上最偉大的傳說威爾特·張伯倫。希爾認為,這一切都要歸功于費城第一個職業夏季聯賽的創立——1960年,費城的職業球員們為了在休賽期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競技狀態,創立了查爾斯·貝克紀念聯賽。希爾也夢想著擁有自己的聯賽,于是他創建了索尼·希爾社區聯賽,網羅了高中和大學里的精英球員來參加。隨后,他又在城市的其他球場復制了自己的夢想,舉辦16屆的費城中央北部聯賽就是他的杰作。
但今天,即便是一向樂觀的希爾也感到了無助和迷惘,他所熱愛的城市和街頭籃球已經變了味,比賽里的球星都是些“娘娘腔”,一點兒小石子就讓他們畏首畏尾。他會責怪球員,但更多的是責怪這個社會“金錢至上”的精神。希爾本人就深深嘗到過“沒錢”的苦頭。當年貝克聯賽土崩瓦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公牛前鋒吉恩·班克斯的違約。以今天的工資標準來說,街頭聯賽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開支。“所有人只會朝錢看。”希爾說,“我看不到籃球比賽的純粹性,看不到人們對籃球的熱愛,也看不到以前那種愿意為比賽獻身的精神了。”這就是賈奎安·紐頓們得到的教育——獎學金和以后的合同重于一切,而籃球帶來的快樂可以被無視。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費城街頭依然會舉行一場又一場的比賽,很多球員和名人都會來到街頭球場上,幾乎每場比賽都會有上百人觀看,而卡蒂諾·莫布里、拉希德·華萊士和凱爾·洛里都曾是這里的常客。
但相比之下,大學球員更喜歡在球館里面打球。16街區的薩斯奎漢納球場雜草叢生、這里的聯賽在2004年就幾乎已經消失了。如果你問一些教練和球員們,這座城市最好的街頭球場是哪兒,他們肯定會無奈地聳聳肩,洛里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不知道你能在哪兒找到打球的人。”他早就不在街頭球場打球了,“我說的不只是我自己,所有職業球員都不在街頭球場打球了。”現在,費城惟一正統的街頭聯賽就是拉希姆·桑普森的“選拔聯賽”了,這是以高中生為班底的聯賽,它生存的原因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因為桑普森不想停止它。
他14年前創辦了這個聯賽,盡管在薩斯奎漢納球場里總會有固定的觀眾,但他的口袋里的收入總是入不敷出。每周四,桑普森都要為周末的比賽支付場地費,此外他還需要付給裁判費用,還要支付看臺費,但這絲毫沒讓他失去熱情。后來,桑普森開始擔任體育雜志的兼職寫手,這讓他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贊助商,現在耐克為他的聯賽注入了資金,桑普森更換了耐克的新籃板,他的球員穿上了統一的運動服,看臺上的座位也修葺一新,他的全明星球員們還穿上了杜蘭特的新款球鞋。
這個城市惟一失去的是什么?答案就是最好的球員。有81名NCAA球員出現在“選拔聯賽”中,可在7月份轉會市場開啟時,桑普森必須停止聯賽——在這時候想要找到那些頂級球員簡直太難了。“總會有許多教練和所謂的專家告訴球員們,不要在街頭的球場上打球。”桑普森說,“事實上,他們也從來沒來過,都是道聽途說的。一個從沒在街頭球場打過球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場上告訴孩子們不要去戶外打球的呢?”高中聯賽確實能讓球員更好地曝光和出名,可是街頭籃球能讓他們學會堅強。“在這里,你會用自己的表現贏得觀眾的歡呼聲,你也會在一次次跌倒中成長。”他接著說,“當然你會說在室內球館,既有空調又有超過2000名觀眾的尖叫聲,環境比街頭好,關注度也遠遠更高,可最起碼我能肯定一點,街頭球場上絕不會有在籃筐下哭著叫媽媽的窩囊廢!”
這就是賈奎安的父親帶他到切拉舒爾球場打球的原因,他用了三年時間,就是想把兒子鍛煉成一個優秀的費城后衛——無所畏懼,勇氣與球技兼具的優秀球員。現在,賈奎安總是請求自己的父親,能不能再回到費城的街頭球場去打球。“你怎么能對一個想去打球的孩子說不呢?”喬·紐頓十分不情愿地把他帶了回來。但就是在那次跌倒之后,賈奎安明白了父親的顧慮。“我是在這里長大的,但在這里打球對身體的傷害確實很大。”賈奎安說,“不只是疼痛,還有害怕受傷的恐懼,為了我的職業生涯,我決定以后不再回到這里打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