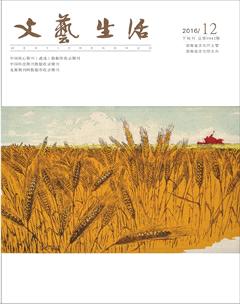倚樓聽風雨:市場經(jīng)濟席卷之下的藝術(shù)生存現(xiàn)狀分析
張放
摘 要:在當代中國,藝術(shù)生存的現(xiàn)狀呈現(xiàn)出了多元而又單調(diào)、過剩而又匱乏的局面,勢必會影響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的進程,這些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本文通過對精英、大眾兩種藝術(shù)文化形態(tài)中的典型文藝現(xiàn)象做出分析,從而找出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出了對在市場經(jīng)濟之下,如何堅守我們的文藝陣地,如何讓文藝更好的服務(w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如何建立新的人文精神等等重要課題研究的急迫性。
關(guān)鍵詞:藝術(shù)生存;文化思潮;文化形態(tài);人文精神通
中圖分類號:J8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36-0283-01
當前的中國,在經(jīng)濟全球化大潮的席卷下,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更加富有挑戰(zhàn)性的時代。而當下的藝術(shù)發(fā)展,卻更多的呈現(xiàn)出了多元而又單調(diào)、過剩而又匱乏的局面,有些現(xiàn)象,我想應(yīng)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所以,我就把精英、大眾兩種藝術(shù)形態(tài)中,某些較為典型的文藝現(xiàn)象找了出來。通過分析,不難看出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面存在著的問題。
一、精英藝術(shù)形態(tài)中的人文精神正在潰退
所謂“精英文化”,是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以及傳播的文化。它不會適應(yīng)嘈雜的物質(zhì)社會,而是人們內(nèi)心渴求、卻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驅(qū)逐時才能感悟到的,是在人們靜心思索或遭遇物質(zhì)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時才冉冉上升。精英首先需要“精神”,它要在創(chuàng)新與社會思想進步上有所作為,要引導社會向和諧方向發(fā)展,而不是附庸風雅,遠離布滿泥濘的底層生活。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由于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所謂“精英”的作家、藝術(shù)家們在創(chuàng)作上紛紛轉(zhuǎn)向,有的懷舊,有的媚俗,場面十分混亂。似乎游離于現(xiàn)實,卻不得不把“理想”、“藝術(shù)追求”等的“破碎虛空”,排在經(jīng)濟效益的后面。
作為“第五代導演”領(lǐng)軍人物的張藝謀,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意義。他早期的作品像《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掛》,都在力圖表現(xiàn)“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極具人文關(guān)懷。即便有評論家說他是“制造被看”,但是他在這個時期的精神走向,應(yīng)該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并且存在著一定的文化批判。張藝謀此后的作品,像《秋菊打官司》,則是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當代現(xiàn)實,這種“直面”精神,使作品進入了一個具有新的的藝術(shù)境界,也把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推向了高峰。可在《一個也不能少》之后,張藝謀突然轉(zhuǎn)向,《我的父親母親》,看似懷舊,卻是放棄理性。有評論家說,張藝謀這是在“向農(nóng)業(yè)文明頻頻眷顧,也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的信號出現(xiàn)了,小農(nóng)情感的尾巴露出來了。”也許是受此輿論影響,張藝謀又決定要從農(nóng)村回到城市,接連拍了兩部都市劇:《有話好好說》和《幸福時光》。然而,這種用溫馨的抒情調(diào)子打造出來的“都市傳奇”,根本無力對現(xiàn)代都市文明作出任何具有本質(zhì)意義的批判性揭示。向現(xiàn)代都市進軍的文化策略受挫之后,他便拍起武俠片《英雄》來了。幾億資金打造出的《英雄》,在視覺方面,果然是無與倫比,美倫美奐。鋪天蓋地金黃燦爛的落葉、蝗蟲般的箭簇、柔若柳絲的寶劍、色調(diào)純美的服飾等,真是讓觀眾享受了一次視覺的盛宴。然而,這些外在的、技術(shù)性的完美,卻掩飾不住故事的匱乏。情節(jié)的單薄、人物的蒼白使這部電影無法逃脫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命運。至于以后的作品《十面埋伏》和《滿城盡戴黃金甲》,就更不必再詳談了。而就在評論界大加討論張藝謀的“商業(yè)化的古典主義”媚俗時,張導演又推出了《三槍拍案驚奇》的古裝驚悚喜劇。我們不難看出:在當一個藝術(shù)家感到無力面對現(xiàn)實,又不敢對現(xiàn)實做出批判性的價值評判時,他就只能回到?jīng)]有思想追求的古典套路中,來作為無力面對現(xiàn)實的“體面逃逸”。
其實,向商業(yè)文化“舉白旗”的絕不是張藝謀一個。我們的“精英們”幾乎是集體投誠,都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向“主流”和“大眾”靠攏。還能堅持批判立場的精英,已經(jīng)稀缺。沒有人文精神支撐的“精英文化”,還能走多遠?
二、大眾藝術(shù)形態(tài)中充斥了大量的偽中產(chǎn)階級趣味
在精英文化逐步“枯萎”的情勢下,曾經(jīng)排在后面的大眾藝術(shù)則變得異常活躍,一個“大眾娛樂”的時代已經(jīng)降臨。
以王朔為代表的市井文學和以趙本山為代表的農(nóng)民文化藝術(shù)都儼然成了主流,以衛(wèi)慧、棉棉、九丹為標牌的“小女子文學”,也隨著商業(yè)大潮而迅速起家,登上了大雅之堂。雖然他們的表達形式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驚人一致:他們脫離社會現(xiàn)實,不正視民間疾苦。無論小說小品還是電視劇,總愛表現(xiàn)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的生活趣味,揮霍奢靡,一群男女整天以“你情我愛”為生活中心。而當今的中國,過著這種生活的人才多少?
每年春節(jié)文藝晚會也都是這一套,對老百姓真正關(guān)心的現(xiàn)實問題,在我們的文藝作品中是越來越少了。有的甚至把最基本的道德標準和價值立場都搞顛倒了。央視春節(jié)晚會連續(xù)演出趙本山的“忽悠”小品系列為例,大年三十晚上,給全國億萬觀眾上的一堂“寓教于樂”的生存哲學課:“誰能騙誰英雄,誰老實誰狗熊。”創(chuàng)作者好象和騙子是一伙兒的,站在同一個道德立場上,一起愚弄那個老實人。把欺詐當作智慧來炫耀,把忠厚當作愚鈍來嘲諷,這是一種什么道德立場和價值觀呢?然而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堂皇的宣揚“無奸不商”等資產(chǎn)階級道德觀的作品,連續(xù)得了幾年的“觀眾最喜歡的節(jié)目”。這不禁讓整天聽著建設(shè)“誠信”、“和諧”社會的人們,覺得滑稽之極。
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是我們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shè)的必經(jīng)之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可市場經(jīng)濟之下,如何堅守我們的文藝陣地,如何讓文藝更好的服務(w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如何建立新的人文精神等等,應(yīng)該是當代文藝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1]趙曙光.媒介經(jīng)濟學案例分析[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