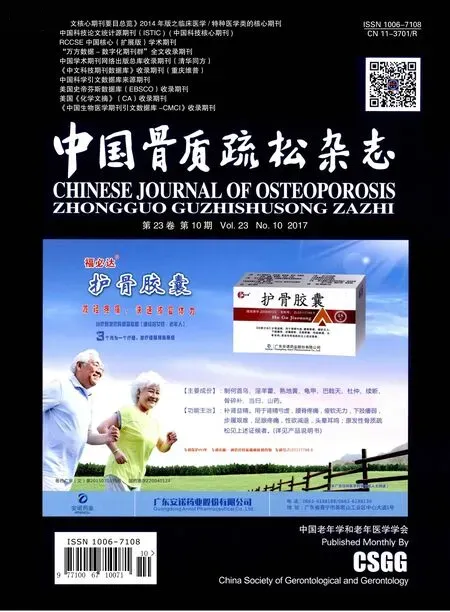骨代謝標志物在骨質疏松癥中醫藥診療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申浩 趙海燕 魏戌 章軼立 謝雁鳴
1.北京市豐臺區長辛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北京 100072 2.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北京 100102 3.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北京 100700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一種累及多臟腑,并在多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下的以骨代謝異常、骨量低下、骨微結構損壞、骨強度受損和脆性骨折危險性增高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骨病[1,2]。研究顯示[3]:北京地區41歲以上女性人群中,骨量減少人群占40.1%,骨質疏松人群占24.6%。北京豐臺區長辛店地區56歲以上男性骨質疏松癥的發病率高達31.59%[4]。骨質疏松癥研究年度報告(2012-8至2013-8)指出[5],目前中國骨質疏松患者呈快速增長趨勢,尤其是由骨質疏松引起的脆性骨折的發病率。女性一生發生脆性骨折的危險性(40%)高于乳腺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的總和[2]。
研究[6]表明,中醫藥在提高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的骨密度,改善其疼痛癥狀,預防骨質疏松性骨折發生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骨代謝指標雖不是作為骨質疏松癥診斷的金標準,但通過檢測血、尿中骨代謝生化產物或相關激素水平,可以了解骨組織新陳代謝的情況,是評價骨代謝狀態、判斷骨質疏松診斷分型、預測骨折風險、評價藥物療效的重要參考指標,目前已廣泛應用于中醫骨質疏松癥的診療過程[7,8],現綜述如下:
1 骨代謝標志物與中醫體質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
中醫體質學說是以中醫理論為主導,研究人類各種體質特征、體質類型的生理、病理特點,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應狀態、病變的性質及發展趨向,從而指導疾病預防和治療的學說[9]。體質現象是人類生命活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指在機體新陳代謝過程中,由先天稟賦和后天培養基礎上所形成的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狀態,具有相對穩定的、綜合的、固有的特質。這種固有特質在很多情況下決定個體對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病性和病理過程的傾向性,及早的發現體質與致病因子的相關性,可以為疾病預防和治療的提供重要依據。骨代謝標志物測定可用于骨質疏松的早期發現,骨代謝標志物與中醫體質類型結合研究,可有助于早期發現不同體質人群可能發生及發展的疾病。梁惠陶等[10]對192例年齡40~66歲健康中老年體檢人群進行辨識體質,并測定其Ⅰ型原膠原N-端前肽(PINP)和血清Ⅰ型膠原交聯C-末端肽(S-CTX,即β-Crosslaps),發現痰濕質和氣虛質患者的PINP和β-Crosslaps明顯高于其它體質,提示氣虛質和痰濕質的人群要比其他體質更加注重預防骨質疏松。唐苗苗等[11]通過將絕經后的受試者分為OP組(30例)、骨量減少組(30例)及骨量正常組(22例)共三組,以中醫體質辨識量表進行評估,同時檢測并分析患者血清骨代謝指標的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和骨堿性磷酸酶(BALP)、雌二醇(E:)及紅細胞膜脂肪酸水平,發現OP組痰濕體質檢出率及分值顯著高于骨量減少組及骨量正常組,痰濕體質分值隨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值的減少而增高,且與骨吸收指標TRACP呈顯著正相關,提示痰濕質OP患者具有骨紊亂病理特征,其BMD隨痰濕體質分值的升高而減少,中醫痰濕體質是OP的重要致病特質之一。
2 骨代謝標志物與骨質疏松癥的中醫證候之間的關系存在相關性
中醫學認為骨質疏松屬于“骨痿”、“骨痹”的范疇[12]。《素問·痿論篇》云:“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骨枯髓減,發為骨痿”。腎主骨生髓,其充在骨,《素問·生氣通天論》云:“腎氣乃傷,高骨乃壞”。腎精空虛則髓化無源,骨骼失養而致骨質疏松,因此“腎虛”是骨質疏松癥的發病基礎。《素問·刺節真邪》云:“虛邪之中人也,灑晰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于骨,則為骨痹”,《醫林改錯》云:“元氣既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讀醫隨筆》云:“經絡之中,必有推蕩不盡之瘀血,若不速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為勞損者”。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血瘀氣不行則“不通則痛”,血瘀可致氣血流通障礙,水谷精微不能布散周身以濡養臟腑,從而加重腎虛,骨髓不得充潤,使“骨痿”病情加重[13]。因此骨質疏松癥患者的病機多為腎虛血瘀,腎虛為本,血瘀為標。
骨細胞代謝是在血液微循環中完成的,研究證實[14]血瘀造成骨內微循環障礙,如血液長期處于高凝狀態,細胞與體液之間不能進行正常的物質交換,從而引起鈣、磷及骨細胞和破骨細胞活性改變,骨代謝發生異常,骨轉換速率加快,加速了骨量丟失的進度,最終導致BMD下降,發生骨質疏松。張波[15]等骨質疏松癥腎虛血瘀證與骨吸收標志物的相關性研究,證實骨質疏松癥中醫證型與骨吸收標志物S-CTX及骨密度、25羥維生素D、雌二醇等檢測值呈一定的相關性,且腎虛血瘀型與其他型各檢測值比較,均有顯著性差異。任之強[16]等通過檢測女性原發性骨質疏松癥(POP)“腎虛血瘀”證患者不同年齡段血細胞參數及骨代謝標志物水平,探討“血瘀”與骨代謝相關性發現POP患者血瘀引起骨代謝異常,骨轉換和骨量丟失加快,發生骨質疏松。帥波等[17]通過探討原發性骨質疏松癥患者中醫證候與血清骨轉換標志物β-Crosslaps、N-MID和PINP水平、血清IL-6、TNF-α含量及疼痛分級的相關性,證實骨轉換標志物β-Crosslaps及血清IL-6、TNF-α含量與中醫本痿標痹證候積分存在正相關,
可作為病情進展評價及療效判定的指標,為闡述“本痿標痹”的病機提供部分臨床依據。龔英峰等[18]通過探討骨代謝生化指標中β-Crosslaps、PINP與原發性骨質疏松癥中醫證型的關系,證實骨代謝生化指標β-Crosslaps、PINP水平可作為區別原發性骨質疏松癥氣滯血瘀型與其他證型的客觀檢測指標之一。章文峰等[19]通過探討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常見中醫證型與血清護骨素的關系,認為絕經后骨質疏松癥中醫證型與OPG水平相關,血清護骨素水平可作為區別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氣滯血瘀證型與其他證型的客觀檢測指標。
3 骨代謝標志物是骨質疏松癥中醫臨床評價的重要指標
血清Ⅰ型原膠原氨基端前肽(PINP)和血清Ⅰ型膠原交聯羧基末端肽(S-CTX)是中藥新藥治療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臨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8]中明確推薦的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臨床有效性評價指標。P1NP與CTX是國際骨質疏松基金會(IOF)推薦的骨代謝標志物特異性指標,能準確反應人體內骨形成與骨吸收的情況[20]。在骨質疏松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細胞因子參與骨代謝過程,通過促進或抑制成骨細胞、破骨細胞的發育及活性,對骨重建起加速或延遲作用,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P1NP與CTX等骨代謝指標的改變[21]。骨質疏松的骨丟失與高骨轉換率是一致的,骨代謝標志物反映了整體骨轉換情況,從而可以用于判定骨丟失的情況。骨代謝標志物增高表示骨高轉換狀態,骨丟失速率加快[22]。周廣文[23]等通過觀察加味青娥丸對絕經后骨質疏松癥(PMOP)患者BMD及骨代謝指標的影響,結果提示高劑量組能顯著降低血清中的骨代謝標志物(P1NP,CTX)的含量,同時增加PMOP患者的BMD。孔西建[24]等通過益腎活血法對原發性骨質疏松癥患者骨密度、骨代謝及脆性骨折發生率的影響,結果提示試驗組的骨密度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同時試驗組能明顯降低β-CTX水平及脆性骨折發生率,提示益腎活血法可有效抑制原發性OP患者骨吸收,防止骨密度下降,降低脆性骨折發生率。劉維等[25]通過補腎活血法治療200例老年骨質疏松癥的療效及安全性。結果提示治療組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治療組的前后證候積分,腰椎骨密度、股骨頸骨密度、BGP、BAP、TRACP-5b、PINP、CTX較治療前均明顯改善(P<0.01)且明顯優于對照組,提示補腎活血法能有效提高老年骨質疏松癥患者骨密度、改善臨床癥狀,可能與其有效調節骨轉換代謝平衡相關。覃裕等[26]通過觀察仙靈骨葆膠囊治療骨質疏松癥的療效及其對骨代謝及骨轉換指標的影響分析,發現仙靈骨葆膠囊治療骨質疏松癥的療效顯著,能有效增加患者的骨密度,改善骨代謝及骨轉換狀態,控制骨量減少;且骨鈣素(OC)和I型膠原交聯C-末端肽(CTX-1)與患者BMD密切相關。
4 骨代謝標志物結合中醫學內容可能有助于早期發現骨量異常的狀態
骨強度由骨密度和骨質量決定[7]。采用雙能X線骨密度儀(DXA)測量BMD對骨質疏松癥的診斷的金標準,低BMD被認為是未來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但在OP的發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BMD測量反映的是骨代謝長期累積的骨量結果,不能及時反映目前的骨代謝情況及骨轉化率的變化情況[27]這就給骨質疏松的早期診斷和治療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骨質量是另一個影響骨強度的因素,其特性是由骨微細結構、骨轉換率、微損傷的積累、鈣化程度以及包括膠原蛋白和其他骨特異性蛋白的骨基質蛋白的特性共同決定的。其中,骨轉換率和骨基質蛋白的性質在每一個臨床階段可以通過測量血清和尿液中的骨代謝指標和骨基質標志物進行評估。骨代謝生化標志物能敏感的反映患者的骨吸收及骨形成情況,有助于早期發現患者骨代謝異常狀態,預測骨折發生的風險性,監測藥物的療效,在骨質疏松的早期診斷[28,29]及藥物治療作用評價中的應用有著重要的價值。及金寶等[30]通過觀察骨代謝標志物對社區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發生髖部骨質疏松及骨折的評估作用,發現PINP及S-CTX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未來10年內髖部骨質疏松及骨折概率具有正相關性,提示PINP及S-CTX在早期預警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中均有重要意義。在骨折患者中,骨代謝標志物水平異常升高,聯合使用骨轉換指標的檢測,有利于早期發現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高危人群,進而可采用有效的措施,預防骨折的發生[31,32]。
在骨質疏松人群出現病理性改變之前,往往會出現一些現代診斷技術(如BMD檢測)在早期檢測時不宜發現的功能性改變,如腰膝酸軟、腰痛、下肢拘攣、目眩等癥狀,這與腎虛、肝虛、脾虛、血瘀等中醫證候要素之間存在關聯性,對骨質疏松的發生有提示作用[33-35]。研究已證實[36]:“目眩”、“下肢拘攣”對早期預測骨質疏松性骨折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加入中醫癥狀組合的絕經后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預測模型,相對于僅有“BMD值+危險因素”組合能大大提高模型的預測靈敏度與特異度[37]。處于高骨轉換狀態OP患者,骨吸收增加時,患者出現疼痛,且疼痛程度與骨吸收標志物β-CTX成正相關,且與炎癥疼痛因子密切相關[17]。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OP的中醫證候與骨代謝標志物之間的關系,以進一步明確尋骨質疏松癥的中醫發病機制,開發出骨代謝標志物、中醫證候要素、危險因素、BMD值相結合的骨質疏松性骨折預測模型,從而為中醫藥更好的防治OP的發生提供科學依據。
5 結語
骨代謝標志物水平與骨質疏松癥的中醫體質、證候存在相關性,是中醫藥的治療骨質疏松癥的臨床療效評價的重要參考指標,將骨代謝標志物與中醫體質或中醫證候內容相結合,建立骨質疏松的早期風險預測工具,可有助于早期發現骨量異常的狀態,對預防骨質疏松癥的發生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