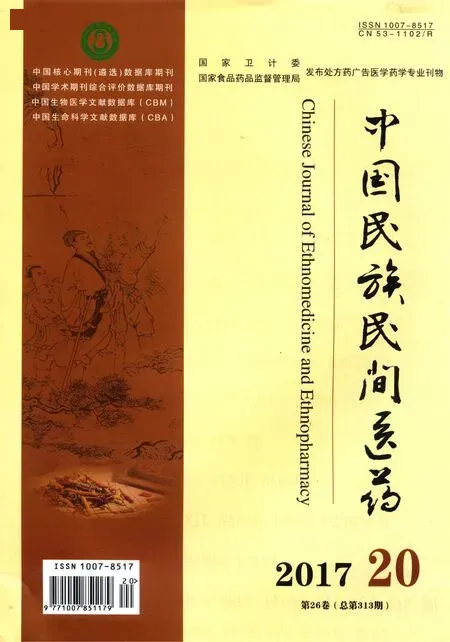苗族巫醫文化的心理學分析
吳小勇 陳 瑤
貴州省中醫藥(民族醫藥)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貴州 貴陽 550025
理論研究
苗族巫醫文化的心理學分析
吳小勇 陳 瑤*
貴州省中醫藥(民族醫藥)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貴州 貴陽 550025
苗族巫醫文化的起源與苗族文化中的鬼神信仰或迷信聯系密切,但其延續不僅與苗族的鬼神信仰或迷信有關,與巫醫治療的實用功能以及苗族社會長期形成的求助于巫醫治療疾病的行為慣性也密不可分。苗族巫醫治療中所使用的符箓、咒語及操作方式具有明顯的隱喻特征,以此實現對患者的心理暗示,其隱喻的內容則體現出苗族文化的核心特征。筆者試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苗族巫醫文化,以供參考。
苗族巫醫文化;社會心理基礎;隱喻
苗族巫醫歷史悠久,西漢劉向在《說苑·辨物》有言:“吾聞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面來者,皆平復如故”。現代史學家普遍認為,苗父是指遠古時代的苗、黎兩族居民的巫師[1]。多數研究者認為巫醫治療屬于心理治療的范疇,目前已有一些文獻對巫醫的心理治療機制進行了分析[2],但是少有研究通過心理學視角分析巫醫的文化現象,故筆者從心理學角度出發,旨在分析苗族巫醫文化的社會心理基礎及其表現形式的心理特征。
1 作為文化現象而存在的疾病
疾病不僅是一種生物學、生理病理學現象,也可列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于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傳統觀念的獨特性,族群成員對所遭受的疾病癥狀的認識往往也具有明顯的差異。比如,苗醫治療中的沸湯灌頂、沸油抹擦、履蛋等治療方法在其他中醫療法中幾乎未見,置于在西醫文化中更是難以解釋。特定族群成員遭受的疾病癥狀可從其文化中找出病因,并以一種具有文化特色的方式進行診斷、預防和治療。文化解釋模型認為,疾病只是一種解釋的模型,不同文化語境下疾病有不同的解釋與分類方式[3]。
在特定文化圈內,關于疾病的命名、分類、解釋和治療等都與該地區的文化密切相關。苗族醫藥體系是苗族先民千百年來同惡劣的自然環境進行抗爭的成果,“巫醫一家”、“神藥兩解”是其鮮明的文化特色,苗族巫醫的出現應與苗族先民對疾病的理解和體驗有著密切聯系。當把疾病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時,苗族巫醫的出現和延續就有了客觀依據,從而對苗族巫醫文化的社會心理基礎及其表現形式的心理特征進行分析就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
2 苗族巫醫文化的社會心理基礎
2.1 鬼神觀念 苗族信鬼好巫,早在傳說中的上古時期,苗族先民便已生活在一個彌漫著鬼神觀念的世界中。《國語·楚語下》有言:“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其后,三苗復九黎之德。”由此可知,與苗族淵源頗深的“九黎”、“三苗”部落群體,很早便有廣信鬼神的傳統。苗族長期延續和保留這一傳統觀念可能與多次飽受苦難的遷徙、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相對封閉的生存環境有關。對鬼神的信仰一方面造就了苗族“萬物有靈”和“自然崇拜”的世界觀,另一方面也讓苗族通過鬼神的方式去認識身邊的事物,比如湘西苗族有“山有山神,樹有樹神,巖有巖神,花有花神”的說法[4]。這種鬼神觀念同時也樹立了苗族對疾病的認識。苗族先民認為自然界各種物質都有一種自我生成與護衛自身的精靈之氣,將能侵襲人體致病的邪惡之氣稱之為鬼,在苗族巫醫中有“無鬼不生病”之說,把能扶助和護衛人體精靈之氣的稱之為神[5]。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苗族先民往往會祈求神靈保佑來治療疾病,這為巫醫的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
鬼神觀念屬于超自然信念,原始社會的人們對風雨雷電等各種自然現象既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與此同時又心存恐懼和疑惑,會讓其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著一切[6]。苗族巫醫正是借助人們所信奉的超自然力量來祛病強身,通過巫醫治療中所呈現的咒語和符箓可以發現其充滿了諸如“太上老君”、“邪魔”、“雜神野鬼”等超自然力量的概念,在治療方式上完全迎合了人們對于鬼神的認識,也印證了人們對于疾病致病原因的理解。巫醫治療在儀式上所產生的心理意義,遠大于在治療效果上產生的實際意義。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苗族巫醫的產生和延續并不取決于其治療效果,而是取決于苗族民眾對于鬼神文化的信仰或迷信。
2.2 巫醫治療的實用功能 雖然苗族巫醫產生和延續與其治療效果可能沒有必然聯系,但這并不否定苗族巫醫在某些疾病的治療上有著明顯的療效。目前多數研究者認可巫醫在心理治療上的作用,巫醫治療過程中的咒語、符箓、角色扮演等充滿各種心理暗示,通過潛意識層面改變患者的情緒和心境[7-8],同時,巫醫治療過程中的儀式本身就可以起到轉移患者注意力的作用,利于降低患者焦慮或恐懼的情緒[9]。苗族巫醫中的“化水術”、“禁咒術”等所起到的止痛止癢、鎮定安神、安胎催生的治療效果就源于此理。另外,心理神經免疫學認為心理行為因素在調節免疫功能中存在重要作用[10],在接受巫醫治療過程中,信奉鬼神的苗族民眾戰勝疾病的信念會被強化,這對疾病治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助益。在心理治療上存在的這些實用功能會使苗族巫醫贏得苗族民眾的信任和認可,從而為苗族巫醫的發展和延續注入活力。
2.3 風俗習慣 隨著苗族地區與外界的持續交融,西醫在苗族地區不斷為民眾所接受,苗族民眾對于鬼神的觀念趨于淡化。但現代苗族民眾仍會尋求巫醫治療疾病,認為尋求巫醫治療是一種“理所當然”[11]。目前作為支撐苗族巫醫產生和延續的基石——鬼神觀念正不斷消融,苗族地區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巫醫治療的習俗成為苗族巫醫得以延續的另一個支點。風俗習慣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其一旦產生,就會伴隨著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方式相對地固定下來,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社會發生變革,風俗習慣也不會因此在較短的時間內消亡[12]。
3 苗族巫醫治療中的隱喻現象
苗族巫醫文化的特色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主要通過隱喻的途徑得以表現。隱喻是人們借助具體的、有形的、簡單的始源域概念來表達和理解抽象的、無形的、復雜的目標域概念,從而實現抽象思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基本方式[13]。與此同時,隱喻具有明顯的文化特性。首先,對隱喻概念的理解會依賴于人們的文化經驗;其次,隱喻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在較高水平上反映文化的內容[14]。反而言之,特定的文化需要以隱喻為載體,植根在人們的內心之中。苗族巫醫作為苗族文化的表現形式,在治療過程中可以通過咒語、符箓和具體操作體現出“萬物有靈”、“圖騰崇拜”以及鬼神致病觀念[14]的苗族文化內容。苗族巫醫主要通過操作系列的隱喻以達到心理暗示的效果。
3.1 咒語 苗族巫醫治療所用的咒語往往以具體形象的鬼神來隱喻人們心目中各類的超自然力量,其中包括代表“善”的超自然力量,諸如太上老君、仙神、仙師、祖師、王母、觀音等神靈,這些形象多與苗族的圖騰有關;還包括代表“惡”的超自然力量,諸如邪魔、雜神野鬼、瘟、毒、兇神惡煞等邪惡形象,這些形象多與苗族民眾所認為的致病因素有關。咒語往往以生動形象的方式描述了“善”驅除或戰勝代表“惡”的過程,這一過程映射了苗族醫療的基本觀點,即去除破壞機體健康的因素。苗族素有“無毒不成病”的說法,此之“毒”即為侵襲人體的邪惡之氣,為“惡”。
3.2 符箓 “符”是道士書寫的一種筆畫屈曲、似字非字的圖形,“箓”是記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雜其間的秘文。道教聲稱,符箓是天神的文字,能治病、鎮邪、驅鬼、召神[15]。苗族巫醫的“化水術”和“禁咒術”中咒語末尾往往附上“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句[1],可見苗族巫醫治療與道教方術有一定關聯,與道教方術一樣,苗族巫醫同樣使用符箓作為治療手段之一。大部分符箓主要由文字輔以圖騰、星象、神秘符號等元素,該文字多屬于“拆字”后的重新組合,其寓意往往跟其中的圖形符號和被打散的文字原意有著某種關聯,但又常常并非望文生義、望圖生義所能釋義[16]。在圖文結合的符箓形成之前,有個漫長的“圖騰”時代,人們以繪畫的方式表達類似符箓所表達的意愿,可以說圖騰是符箓的前身。苗族巫醫治療過程中所使用的符箓中往往會出現日、月、牛、馬、雷、雨等文字,這些文字所代表的形象都與苗族先民的圖騰存在關聯,隱喻了圖騰所具有的超凡力量和作用。日、月可以帶來光明,驅散黑暗,消除恐懼;牛、馬則代表了家畜興旺[16],苗族巫醫“化水術”中的安胎水符箓的中間顯著位置寫著牛、馬字樣[15],這隱喻了人丁興旺的愿景;雨、雷代表了御鬼驅邪的無窮力量,其中雷具有迅疾的特點,具有強烈的威懾力,為邪晦所懼[15]。
3.3 治療操作 苗族巫醫的隱喻現象不僅表現在治療中使用的咒語和符箓上,也表現在治療的操作方式上。落翳術是苗族巫醫治療眼翳的常見方法,主要通過搬動家具使眼翳脫落,苗醫首先看患者的眼翳形狀、位置后指導患者回家以后移動或者清掃一些物品[1]。這種方法通過移動或者清掃家中物品來隱喻清除眼翳,達到心理暗示的效果。除此之外,苗族巫醫中的“什針術”、“捆扎術”[1]的操作方法也具有類似的隱喻特征,對患者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
4 結語
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的方式映射了其群體的文化特征,苗族巫醫文化的起源與苗族文化中的鬼神信仰或迷信有著密切關聯,而在醫療科學化的現代,苗族民眾在治病求醫中仍然求助于巫醫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是苗族巫醫在心理治療上存在的實用功能贏得了民眾的信任和認可,二是巫醫治療的習俗在苗族延續千百年,長期形成的行為慣性使得人們繼續求助于苗族巫醫。
苗族巫醫治療中,主要通過隱喻實現對患者的心理暗示,其隱喻的內容體現出苗族文化的核心特征。該方式可能與苗族先民的思維特征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苗族先民對人體的認知理論中可以發現,其思維方式存在著顯著的“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特色,這與中國傳統思維“象思維”高度一致。苗族“三要素論”的氣、血、水以及“三界學說”的樹界、土界、水界都以具體的形象來指代高度抽象的意義,這種思維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以陰陽五行等方式表達對世界萬物的理解亦是相類同的。可能正是苗族先民這種“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的思維特征決定了巫醫治療中往往采用隱喻的方式來傳遞或表達各類意象。
[1]杜江,鄧永漢,楊惠杰.中國苗醫絕技秘法[M].貴陽:貴州科技出版社,2014.
[2]尹紹清.古代中國人心理健康維護的社會性支持與自我支持的方法[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 2011, 30(3): 97-100.
[3]黃鋒.民族醫療中的“神藥兩解”現象解析——以粵北一個“排瑤”村莊為例[J].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0):35-40.
[4]張衛華.淺析湘西苗族巫術文化的特性[J]. 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04,15(2): 43-45.
[5]石志權,吳言發.略論苗族萬物生成論對苗族醫藥文化的影響[J]. 中國民族醫藥雜志,2009(6):60-61.
[6]陳永艷,張進輔,李建.迷信心理研究綜述[J]. 心理科學進展,2009,17(1):218-226.
[7]孫時進.巫術的心理學分析和批判[J]. 心理學探新,2001,21(4):16-19.
[8]許華堯.中國巫術文化和心理咨詢與治療本土化[J].石家莊學院學報,2007,9(3):79-83.
[9]吳利華.苗族巫醫的文化內涵及其功能——以鳳凰縣兩頭羊苗寨巫醫為中心[D].武漢:中南民族大學,2008.
[10]林文娟. 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J]. 心理科學進展,2006,14(4):511-516.
[11]徐雯棟. 制度與文化中的少數民族村醫——基于古村苗醫張孝祥行醫史的研究[D].武漢:中南民族大學,2013.
[12]鐘敬文. 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6.
[13]殷融,蘇得權,葉浩生.具身認知視角下的概念隱喻理論[J].心理科學進展, 2013, 21(2): 220-234.
[14]尹新雅,魯忠義.隱喻的具身性與文化性[J].心理科學,2015,38(5):1081-1086.
[15]曾召男.符箓[J].宗教學研究,1983(2):58.
[16]顏開.小議湖湘巫術“符箓”的內容構體[J].裝飾,2010,204(4):114-115.
R29
A
1007-8517(2017)20-0001-03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苗醫藥文化價值體系及現代轉型研究”(17XMZ040);貴州省重大應用基礎研究計劃(黔科合J重大字[2015]2002號);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地項目(2015JD072)。
吳小勇(1982-),男,漢族,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苗族醫藥文化。E-mail:ahxywu@gmail.com
陳瑤(1965-),女,漢族,碩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為中醫文獻研究。E-mail:ahxywu@gmail.com
2017-08-31 編輯:程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