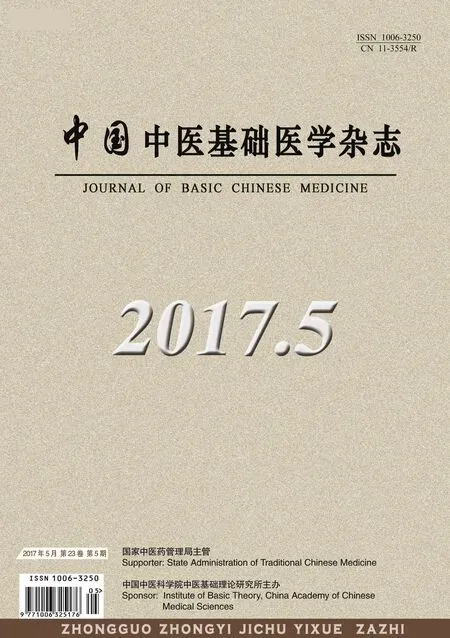徐靈胎有藥無方與有方無藥辨析
尹基龍,崔現超,徐 征
(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南京 210023)
【理論探討】
徐靈胎有藥無方與有方無藥辨析
尹基龍,崔現超,徐 征△
(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南京 210023)
清代醫家徐靈胎于《醫學源流論》首次提出“有藥無方”與“有方無藥”,此論直指當世醫家臨證處方用藥之流弊。徐靈性尋本溯源,究心醫典,所論“有藥無方”,臨證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又論“有方無藥”,執方治病,罔思藥證而不依癥別裁;示人“有方有藥”,守立方歸旨而兼善權變。用藥靈變若此,可臻善境。古人制方加減微妙精詳不可思議,后世諸家臨證活法靈機變化存心。古今異軌,制方之義,頗有不同。
有藥無方;有方無藥;有方有藥;徐靈胎
徐靈胎(1693~1771),名大椿,又名大業,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人。他究心醫學,著述嚴肅,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論》《慎疾芻言》《傷寒類方》《洄溪醫案》等。此外,還對《外科正宗》《臨證指南醫案》等著作加以評注,見識獨到,別具一格。
徐靈胎之治學嚴謹崇尚經典,發論醒世針砭時弊。先生之治醫,破書萬卷,無師自通,數古今杏林,當為鳳毛麟角。認為“一切道術,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唐以前之書,徒記時尚之藥數種,而可為醫者。今將學醫必讀之書并讀法開列于下,果能專心體察,則胸有定見。然后將后世之書遍觀博覽,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長而去其短矣。[1]”明辨醫學的源流和醫家個人見解之間的區別,惟此才能學有根柢,胸有定見,不至于落入俗套,無所適從。
1 有藥無方
此言見《醫學源流論·方藥離合論》:“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2]179”徐靈胎批時下醫家臨證依癥用藥,見一癥即用一藥,或用藥堆砌,不詳加辨證,流于表象,藥雖中癥而立方之法不存;或假兼備以幸中,廣絡原野。所列之藥有不中者,勢必誤己害人;或果切中病癥,然雜藥亂投,漫無章法,不知其所以取效者為何藥,亦不為后來者所師法;胸無定法,雜湊處方,此皆謂有藥而無方。
“有藥”者,一藥皆對一病癥,對于癥狀較少、病癥較輕者或可收良效,若遇癥狀復雜、寒熱交替之病癥則頗難收功。后世醫家多自擬處方,普遍存在藥味偏多,以十幾味為常見,甚至有二十余味、三四十味者,藥物劑量偏大的現象。陳超分析認為:“多于十三味藥物的大方且無組方規律者則可認為是中藥大處方。大處方的問題則尤其突出往往是有藥無方。[3]”
“無方”者,抑或有方之名而無方之實。方隨證出,證以統方,無證則無方,又有方不對證,或隨心所欲,濫為增損,使所用方藥偏離治療目標,與證不盡吻合。“古法之嚴如此,后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2]180。托名經方,實際上卻對原方任意增損,而使原方名存實亡。其論切中時醫泛用藥味、不切病機之弊,亦對后人影響深遠。如楊乘六說:“見某病即用某藥,一方中必下數十味,直是一紙藥賬矣。[4]”顧錫亦謂:“不遵古方,則牽強附和,補瀉混投,溫涼雜用,散亂無紀,何以取效?[5]”皆道出用藥之精義。
然徐靈胎亦有《醫學源流論·單方論》:“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癥,而其效則甚捷……凡人所患之癥,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濃,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癥,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2]181”此單方區別于復方,即小方意,可理解為一二味藥之方,亦“有藥”意。徐靈胎肯定“單方”對癥取效甚捷,辨證用藥之特長。“有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病癥或收奇效,亦明說有利必有害,凡遇病癥皆以單方治之,以“有藥”統之,則其藥性之偏無以制約,終非善法。近賢裘沛然認為,大方復法看似雜亂,其中自有深意。兼備之法,并非雜湊,其處方既寓有巧思又不失配伍之精密,是為中醫處方學造詣很深的境界[6]。裘沛然初始習以經方絲絲入扣,但遇疑難病癥往往無從下手,而他醫以復方大法頗得奇效,令人贊嘆深思。相反相成相激,復方復法復治,非臨證老到者不能。歷當代醫家,陳亦人、鄧鐵濤、周仲瑛、潘朝曦等皆有此論。
2 有方無藥
《醫學源流論·方藥離合論》謂:“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2]179”方誠為良方,非善用者不能盡其美。徐靈胎直言,更有醫者執守一方以治病,猶守株以待兔。然疾病變化萬千,首末殊情。方有一二味與病不相符者,亦不去之,不知其有意為之或智者一失?此徐靈胎所謂有方而無藥。
“有方”者,徐靈胎言:“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藥理之本源,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和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變化不窮。[2]180”徐靈胎一貫學務窮經,志尚師古:“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為之制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2]179。圣人先有定方,定方制法嚴謹,配伍精當。識藥性、察氣味、審臟腑,力求切合病機,藥中病除。此圣人之立方思遠義精,故固執原方,方證相應,如鼓應桴。以不變應萬變,或高出后人手眼幾何。
“無藥”者,徐靈胎言:“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唯臨證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7]”此述《傷寒論》諸方立法精妙,以經類經。復言“臨證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然亦有他者斷章取義,單引“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之語,妄詆徐靈胎“尊經復古守舊”等,有失嚴謹亦不嚴肅[8]。他嚴厲批評有方無藥者,執死方以套活病,罔顧病情變化而不知隨證治之,然方之治病有數而病之變化無定,醫者若此,死傷無算。
臨證亦有醫家原方搬用張仲景方藥,所用方藥與原方一致,一藥不多,一藥不少。一味不加一味不減的使用原方,是對隨意加減經方的一種矯正。但因不顧病情的變化強用原方,從而走向了隨意加減經方的另一級端,矯枉而過正[9]。
3 有方有藥
以“有藥無方”與“有方無藥”兩者結合,提出“有方有藥”的理解。徐靈胎雖未明言“有方有藥”,然他在《醫學源流論·古方加減論》中處處示人“有方有藥”的思想,直指臨證立方要旨。譬如“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癥,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癥,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徐靈胎認為:“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2]180”既有古方制方大義,又不失臨證活法圓機,非古方難用,誠不得其法也。
徐靈胎臨證運用古方,強調審證求因,力倡主方主藥,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且要隨病情之變化進行加減,不可盲目遣方用藥。《執方治病論》有言:“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癥,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癥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癥相合,然后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途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癥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2]186”徐靈胎所言極是,醫者臨證當明辨慎思,對所處方藥胸有定見;至于危重疑難之證須博考群方,以求變法,有方有藥,兼收并蓄。
4 啟示思考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所批判的“有藥無方”與“有方無藥”,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歷代醫家臨證面臨的必然問題。他深入剖析了方與藥之內的聯系,于“方藥離合論”“古方加減論”“單方論”“執方治病論”等諸篇中探討臨證處方用藥之法度,切中時弊,發人深思。
醫者臨證貴在辨證精準,再議方藥。據法選方,據方議藥,所立方藥恰到好處,增一味則嫌多,減一味則嫌少,無一藥游離,無一藥泛用,可謂有方有藥。然如何做到有方有藥,則必究徐靈胎之治學:學務窮經,志尚師古。從源以及流,上溯《內經》《難經》,下及時醫名流,必先胸有定見,后旁觸諸家,轉益多師,兼收并蓄;不可執迷一家之言,目障一葉。勤于臨證,靈活思辨,圓機活法,或可臻有方有藥之境。
[1] 徐大椿. 徐大椿醫書全集·慎疾芻言[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562.
[2] 徐大椿. 徐大椿醫書全集·醫學源流論[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
[3] 陳超. 中藥大處方對肝病的負面影響及其對策[J]. 中國全科醫學,2010,34:3929-3930.
[4] 楊乘六. 醫宗己任·四明醫案[M]. 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8:93.
[5] 顧錫. 銀海指南[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6.
[6] 裘沛然. 壺天散墨[M].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15-16.
[7] 徐大椿. 徐大椿醫書全集·醫貫砭[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24.
[8] 吳云波. 徐大椿《醫貫砭》學術價值管窺[J]. 南京中醫學院學報,1988,2:51-53.
[9] 趙鳴芳.經方應用的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上)[J]. 江蘇中醫,2000,9:1-3.
尹基龍(1990-),男,江蘇徐州人,醫學碩士,從事五臟系統病證的規范研究。
△通訊作者:徐 征(1975-),女,江蘇揚州人,副教授,醫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醫診斷學教學及教材編寫研究,Tel:15850505960,E-mail:xuzheng_75@163.com。
R222.15
A
1006-3250(2017)05-0607-02
201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