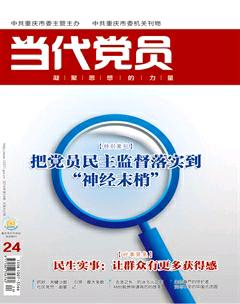戴胄的廉直
陳良
史料記載,戴胄為人堅貞正直。
唐貞觀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最高審判機關副職)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他:“這是關系到人命的官職,戴胄是最佳人選。”
戴胄剛上任,就遇到一件麻煩事。一天,皇親國戚、朝廷重臣長孫無忌應召參見皇帝,沒解佩刀就進入皇宮的東側門,出閣后,走到東門口,守門校尉才發覺。尚書右仆射(宰相)封德彝認為,校尉未及時發覺,應處死刑;長孫無忌失誤帶刀,應判徒刑二年,罰銅二十斤。唐太宗同意這個意見。戴胄反駁說:“長孫無忌帶刀入宮,校尉未發覺,同為失誤。按照法律規定:供奉皇帝的湯藥、飲食、舟船,發生任何差錯都要處死罪。陛下如因長孫無忌有功而從寬,這就不是司法機關可以議定的;如果依法處理,罰銅是不合適的。”唐太宗說:“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長孫無忌是皇親國戚,就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審。封德彝堅持己見,太宗默認。戴胄再次辯駁說:“兩者情節嚴重程度相同,而判決卻有生死之別,顯失公平,我斗膽請求寬恕校尉。”太宗覺得有理,免除了校尉死刑。
戴胄就是這樣,凡事秉公而斷。當時朝廷選舉人才,有人為了上進偽造資歷。唐太宗下詔,允許作偽者自首,凡不自首,一經查出,死罪。不久,有作偽者敗露,戴胄受理此案,依法判處此人流放。唐太宗斥責道:“你現在按法律判,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說話不算數嗎?”戴胄回答:“既然走司法程序,為臣不敢違背法律。”太宗質問:“你只顧遵守法律,卻讓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解釋:“法律是國家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語是一時喜怒說出來的。如果曲從個人情緒而違背法律,臣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頓時醒悟,采納了他的意見。
的確,戴胄參與辦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條文為依據,分析周密細致,逐條厘清罪證,言辭如泉涌,極富說服力。為維護公正,戴胄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為從善如流的明君,不僅沒遷怒于他,反而予以提拔重用。繼大理寺少卿后,戴胄升任尚書左丞,貞觀二年,又與魏征一同擔任諫議大夫;貞觀三年,他升任民部尚書,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貞觀四年,戴胄開始以民部尚書之職參與朝政,成為宰相級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官位不斷上升,但戴胄依然嚴守法度,除法定俸祿及皇帝賞賜,沒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他雖貴為宰相級大人物,卻住著簡陋的房子。貞觀七年,當戴胄去世時,他家因房屋簡陋狹小,竟連祭奠的地方也沒有。為了哀悼這位清廉正直的大臣,唐太宗罷朝三日,下令官府特地為他建造一座家廟,并命虞世南為他撰寫碑文。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戴胄如此清廉?
或許有人認為,戴胄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君子操守,不想貪。其實,他并不精通經史,況且,很多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都淪為貪官,可見儒學教化并非為官清廉的先決條件。或許有人認為,是因他循規蹈矩膽小怕事,不敢貪。在帝制時代,帝王擁有生殺大權,惹惱帝王隨時有生命危險,戴胄多次犯顏直言,表明他絕非膽小怕事之人。或許有人認為,是政治生態使然,因為當時政治清明,不能貪。這個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不過,就戴胄而言,其清廉在于內因。《舊唐書》也好,《新唐書》也好,在戴胄本傳中,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記述他的兩則秉公執法故事。透過故事,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極為正直、極度守法的人。古往今來,所有貪腐行為無不是違法亂紀行為。由此可以推斷,大凡講規矩守法度的人,為官必定清廉。
(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