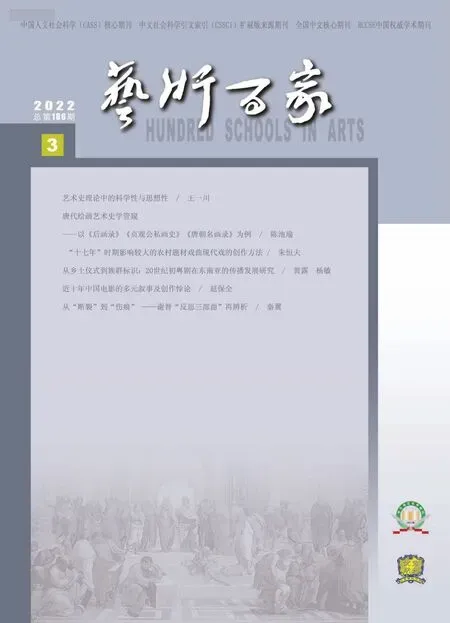家國構想與民族儀式的交合同構
高力 張愛坤
摘要:傳統習慣中,研究者通常將“十七年”時期電影作品當做中國電影發展史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來看待,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故事情節到人物形象再到歷史遭遇總是顯現出了極度相似的特質一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是這一時期一道別樣的文化景觀,顯示出了家國構想與民族儀式的雙向交合特征,文章引入“互動儀式”這一社會學用語,具體從敘述者、敘述文本與敘述接受三個角度考察研究對象的整體敘述活動,最后得出結論:“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敘述活動從總體上也是一場柯林斯筆下的“互動儀式”,“儀式”通過微觀的互動情境和人物的個體際遇塑造了一場家國神話,借助社會情感的力量起到了維系群體內部穩定和團結的社會功能。
關鍵詞:電影藝術;中國電影史;“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互動儀式;敘述活動
一、敘述活動與互動儀式
敘述是人類認知世界并從中獲取經驗的基本活動。“是人類組織個人生存經驗和社會文化經驗的普遍方式”。敘述活動的標的是意義的產生,也正是基于此,敘述活動才能和抒情活動一起成為人類感知外界的兩項基本活動。不止于此,在《后現代知識狀況》一書中,利奧塔更是“提出‘泛敘述論,他認為人類的知識,除了‘科技知識,就是‘敘述知識”。這其中當然存在利奧塔作為后現代主義學者試圖解構一切意義的話語,但至少我們從中可以窺探出敘述活動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意義。按照卡西爾的觀點,人不僅僅是“使用符號的動物”,而且是使用符號來進行敘述的動物。敘述活動可視為是一場發生在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之間動態的雙向交流活動,此間需要的必要中介則是敘述文本,由此,敘述活動的整體過程便應該由“敘述者-敘述文本-敘述接受”這樣三個相對獨立然而相互之間又具有多種聯系的元素組成,敘述活動的本質是一場經由敘述文本的中介作用完成的敘述主體與接受者之間的互動。
“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這一詞匯來自于戈夫曼的闡釋,他認為所謂互動儀式就是一種以表達意義為最終目的的程序化活動。這種活動對于群體內部的團結和穩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涂爾干也曾經提出過宗教儀式具有整合的作用。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儀式活動,不同的儀式類型代表著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傳統社會中的人類活動通常帶有高度儀式化的風格,而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發展進程解構了傳統社會一部分冗雜的儀式活動
無論是涂爾干還是戈夫曼,他們都只是強調了社會儀式的概念以及儀式的社會功能,對于儀式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采取了規避的態度。對互動儀式作用機制真正開始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一書中,柯林斯系統探討了互動儀式的作用機制,他認為,互動儀式是社會學研究的基點。對于微觀社會學來講,情境結構的作用和此結構的動力學成因是社會學者要研究的重要客體群體所有的互動和互動儀式都歸屬于特定的某個情境當中,這當中包括主體通過組合形式而生成的際遇(encounter)關系(至少兩個人),所以“互動儀式與互動儀式鏈理論首先是關于情境的理論”。
二、敘述主體:權力決策與話語干預
敘述主體是文本意義的建構者,是講述活動的源頭,作為文本意義的發出者,敘述者在編排敘述話語的過程之中將個人體驗和生活經歷注入文本的內部,借由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節編排將自己內化入文本的意義進行傳達。
敘述的主觀傾向性決定了敘述者的講述活動很難不受外界影響,書寫活動既顯示出封閉性又流露出一定的開放機動性,書寫和講述是自由與記憶之間相互妥協的產物,講述活動受制于外界政治文化權力話語的干擾而發生偏向的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可由此引發敘事活動的“不可靠”。對于“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電影來講,權力話語的決策和干預成為解讀這一文本不可忽視的重要標示性事件。新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決定了作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少數民族必然要成為國家話語的必要組成部分。
因此,反映在電影的創作過程之中便是創作者傾注在電影文本中的全部意義都演變為試圖建構家國話語的努力嘗試,柯林斯在論述互動儀式的過程中反復強調了互動儀式的發生機制是社會情感力量“什么因素將社會結合在一起——團結的‘黏合劑——以及什么動員了沖突——被動員的群體的能量——是情感”,社會情感的構成源自于個體情感在某種向心力作用下的相互疊加,對于新生中國來講,塑造家國統一、國富民強的鏡像神話便成為“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首要任務。因此,敘述者在建構故事情節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過程之中,首要考慮的便是通過階級二分法來形成類型敘事之中最基本的二元對立結構,進而闡釋源自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基本主題“并在不同題材的不同主題中,形成萬變不離其宗的敘事變形”。
1950年,東北電影制片廠拍攝了干學偉的作品《內蒙春光》,鐘惦榮先生特意撰文《看<內蒙春光>》評價道:“影片充滿了蒙古情調,一開始頓德布在草原上追逐馬匹;烏云碧勒格赤著腳在草原上趕著羊群;……以及像敖包會上的表演等等,都有著濃郁的內蒙風味”。這說明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在于對內蒙風情的視覺展示,而不是政治先行造成的圖解民族政策。隨后,中央電影局對這一影片進行了復審,復審的結果是認為該片對于“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不利,不宜再映出”。隨后,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文化部召開故事片《內蒙春光》的討論會“會議由沈雁冰主持,參加者有統戰部、民委、文委。《人民日報》負責人,以及陸定一、郭沫若、陽翰笙、江青、周揚、蔡楚生、洪深、老舍、田漢、曹禺、夏衍、張致祥、趙樹理、丁玲、鄧拓、袁牧之、陳波兒等”。經過會議討論,周總理做出了如下指示:“第一,同意這部電影在藝術上是好的,但影片的錯誤在于政治原則上有問題;第二,具體指出了《內蒙春光》違反民族政策的內容;第三,特別指出這部影片錯誤的責任不在編劇,應歸于領導”。隨后,影片的編劇和導演對整部電影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僅保留了原片54個場景之中的28個場景,另外重新拍攝了16場,對原來的10個場景進行了局部修改,重新修改的這些場景基本上能夠將新中國的民族政策闡釋清楚,新加入四個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也基本定性。至于此,這部由周總理親自關懷進行修改,而后由毛澤東主席更名為《內蒙人民的勝利》的影片重新上映。
應該說,修改之后的影片很好地對新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了圖解式的說明:新生中國各個民族的共同敵人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而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雖然在某些時候會顯示出其殘酷的一面,但這類矛盾顯示在民族內部,這類人群是我們盡力爭取而不是全力反對的對象,客觀來講,《內蒙春光》的拍攝是作者深入蒙區進行深入調查的結果,劇中引起最大爭議的“王爺”這一形象也是“有生活依據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經過政策導向矯正之后的王爺這一形象雖說符合了當時的民族政策,但畢竟作為一個中途修改的人物而“導致人物思想脈絡不盡合理,圖解政策的痕跡也很明顯”。
由是觀之,對于“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電影敘述主體的講述活動來講,政策導向借由政治話語侵入敘述文本內部,重組之后的話語體系在重新編碼的過程中對于政策法規進行了視像解讀,目的在于詮釋一種新的價值體系,“政治先行”的觀念將民族內部矛盾這一次要矛盾降序排列于主要矛盾之后。對于敘述主體來講,試圖通過影像文本傳達的民族藝術話語不得不重新被解釋為民族政策話語,個體私人情感讓位于家國社會情感,這樣,在互動儀式中具有根本意義的社會情感力量通過政策話語干預之后的藝術客體展演活動將權力觀念按照已經設定的情感模式傳達給受眾,進可能地爭取權力政策欲爭取的對象。
三、敘述文本:類群身份與族裔倫理
敘述文本是一個意義的合成體,同時也是意義的生成體。敘述文本通常按照現時語言系統的規約將敘述話語進行編排,話語的編排過程也就是敘述主體將意義注入文本的過程敘述文本并非實存的物質存在,它的存在意義產生于意義傳達所構成的關系之中,假如沒有解釋與被解釋的發生,文本的意義就不會傳達,文本也就可視為并不存在。文本意義的形成取決于接受者對文本進行解讀的過程中對文本意義所進行的構筑方式。所以,理論上講,單獨的文本自身并不會生產意義,被認為由文本所攜帶的意義在傳達過程中也具有著極大的不穩定性和延展性。
“十七年”時期之所以能夠被學術界認定為中國電影發展史中一個獨特的時期,原因就在于這一時期的敘述文本內涵具有類似性。“十七年”時期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總是傾向于在二元對立之中完成敘事,以階級矛盾替代故事沖突,以家國情感取代個體情感,最后塑造出一場國族同構的盛世景觀。
新生中國在對古舊中國權力體制予以放逐的同時也對古舊中國已然成型的藝術話語進行了放逐和重新編碼。重新編碼之后的藝術符號要在解釋學的功能上發揮具體闡釋新生中國之“新”的特殊作用這樣,少數民族電影的文化功能是第二位的,此時期真正的目的旨在通過民族風情的渲染來烘托意識形態的統一性。
柯林斯將互動儀式的論述焦點聚集在群體內部,互動的發生至少需要兩個人之間影響與被影響關系的存在,中國的多民族統一性決定了各個民族共同構建著一個政治學意味的類似群體,也就是說,文本內部描繪的個體化的某個人或某一民族最終都要歸屬于影片最終所建構的中華民族一體化之中,這樣,敘述文本內部的個性化表征在最初編排的時刻就被認定其最終需要歸附于更高類群之中,隱含在多義性個體之中的表象化差異最終都要統一于國族建構的同一化敘事內部。
群體的形成源自對于文化符號的一致認同,群體之間的界限也在于彼此之間文化符號的差異,類群身份在互動中具有著非常顯著的儀式功能,類群身份得以界定的同時也就標志著個體身份的被歸屬,群體內部在文化符號上的相似相同性將異質符號編入同質符號內部,個體便等于無條件的接受了群體召喚類群身份的形成也是群體內部差異性的喪失,也就是說,主體在歸屬于類群的同時就必然認同了此群體的文化符號,并且在個體的活動之中遵循這些業已形成并且不斷強化的文化符號,而個體通過自身的活動和行為又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文化符號的規約能力和形塑強度。
1959年上映的長影廠作品《金玉姬》很好地表現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區時抗日聯軍的艱苦斗爭朝鮮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很快聯合起來,目的就在于共同“打日本”,為了便于隱藏身份,許多朝鮮族的抗日戰士都將民族服裝換為漢服,不同于其他影片對民族服裝、民族風情的刻意描繪,《金玉姬》恰恰表現的是少數民族兄弟身著漢服秘密斗爭的故事。“電影《金玉姬》在表現民族團結方面也是一個生動的教材。它非常樸實和深刻地描繪了在抗日斗爭年代,無論在抗日聯軍內部朝鮮族戰士和漢族戰士之間親密無間的戰斗友誼和朝鮮族群眾和漢族群眾之間的親如一家人、同生共死的階級感情”。《金玉姬》以現實主義手法生動展示了國家危亡時刻民族之間團結對外的必要意義。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關注到:金玉姬這一人物形象在塑造過程之中編導的有意處理,民族服飾具有著顯著的民族標示性意義,影片中的主人公選擇脫下民族服裝的舉動也交代給我們這樣的事實:面對家國的危亡時刻,民族的意義已經退居次要,無論漢族還是朝鮮族,一致對外才是解救國難的唯一出路。
據此,我們能夠看出,敘述文本之中通過對慣常視覺形象的破壞衍生出新的意義,民族服飾的褪去也就是對民族符號標志意義的拒絕,拒絕的目的是主人公內心深處所認同的家國觀念,或者說是主人公由族群認同走向國家認同的視覺展示,影片所書寫的朝漢人民一致對外可以解釋為中華民族對外來民族入侵的全力反抗。
因此,《金玉姬》這一文本事實上書寫的是在認同中華民族一體化基礎之上對于族裔倫理的敘述性展現。
四、敘述接受:符號匹配與圖像隱喻
敘述活動是一次符號的排列組合過程,排列者與接受者分居文本兩端,意義經由敘述文本的承載進行目的性發送,最終意義能否被解讀以及怎樣被解讀就得益于敘述接受這一環節,接受活動是接受者與隱含作者的一次對話,敘述接受可看做是敘述活動的最終環節。追蹤西方文藝理論的發展,無論柏拉圖還是托爾斯泰對文學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文藝作品的社會功能方面,這種占據文藝理論中心地位的文學觀念著重考察文藝作品對讀者所能夠產生的政治和道德影響直到接受理論和解釋學的出現才啟示性地建立起從讀者理解和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方法論,并由此建立起來一套新的文藝批評方法論,實現了西方文論由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到讀者中心的轉向。
在海德格爾的啟示之下,伽達默爾將人類的理解活動提升到與存在生存以及真理等重大哲學問題等同的地位,按照他的論述,“理解”并非一種所謂的科學的認識方法論,而是真理發生和存在的一種方式。所以,作者的創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怎樣理解,讀者的理解活動使得作品由存在變為現實。之后,姚斯和伊瑟爾這兩位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對于文學接受的研究分別從期待視域和召喚結構兩個方面展開并以此為基礎建構起了影響深遠的接受理論。
電影作為被看的藝術,意義被圖像化和形象化的進行展示,觀眾在看的過程當中將自身置于藝術的升華作用之中,在感受意義的過程當中獲得意義,進而完成對現實的審美超越。對于“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觀看活動來講,民族符碼的展演并非僅存在于藝術和文化層面,更重要的一個環節是敘述主體期許能夠通過敘述文本的展示將家國情感審美化的傳遞給接受者,進而用圖像化的視聽語言達到意識形態規約作用所亟需的政治訴求。
按照符號互動論的觀點,人類的全部所需所感都夠納入符號的概念之下,符號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人類在自然狀態下的活動于此獲得符號意義進而成為研究群體活動的重要依據。如果對符號互動做出進一步延展的話,敘述接受活動之中的符號互動也可以理解為互動基礎上人類的一次符號匹配活動。前文提到過,符號是標示人類歸屬于群體的標志,獲得符號和認同符號的結果就是個體的被歸屬,按照柯林斯的解讀,情境在互動儀式中具有著“場域”的意味,當某一個體因場域召喚力而進入這一特定空間之后就會與場域內部其他個體“不斷接觸而發生延展,從而形成穩定的互動結構”,隨著人們越來越多進入到該場域之中并使得該場域自然空間隨之增長到足以影響社會的時候也就是宏觀社會結構獲得穩定的時刻。群體以符號的形式對自身做出解釋和標示目的是期許群體內部的個體之間產生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從而形成與認知符號相關聯的成員身份感。
“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囿于政治訴求和意識形態干預,總在自身的符號體系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族神話,這場國族神話必然需要通過鏡頭語言來制造出一組服從敘述主題的視像符號。觀眾的收看過程也就是對國族神話視像符號的接受和認同過程,通過觀看者自身與視像符號的匹配來完成個人歸附于集體的目的,通過視覺符號的隱喻功能制造一場又一場政治宣講。
敘述接受的核心是接受者的“解讀”這一動作,解讀并非被動的標的性闡述,解讀過程是接受者能動的發揮空間,解釋不足、過度解釋甚至誤讀都屬于文本接受活動中時有發生的事情。通常情況下,人類通過解釋活動所獲取的文本意義與敘述主體注入文本內部的意義經常會發生偏差,這既是解釋學和接受理論能夠成型的誘因也是造成有些人對接受理論持反對意見的最主要因素——絕對的解釋活動放逐了文本的存在意義。《劉三姐》“是新中國第一部音樂風光故事片”,導演在導演闡釋中特別強調了這部影片的最高任務是“反對封建統治,爭取自由幸福的生活”,“唱歌就是命,寧舍命,不舍歌”,在風格展現上,要求作品“既帶有南方民歌特點,又非常婉轉抒情,也就是要有強烈激昂的調子,又富有抒情風格”。劉三姐雖然屬于傳說人物,但是與現實社會卻有著極大的隱喻關系,她之所以能夠勇敢地和封建統治勢力展開斗爭在于其背后強大的人民群眾,而人們之所愿意為之做后盾也是因為劉三姐和他們一樣飽受著財主的壓迫和剝削,有著一段和他們一樣的血淚史辛酸史。因此,無論她為財主迫害有家難歸還是慘遭監禁,作為個體來講,她都已經成為廣大人民苦難的象征,與人民的悲戚命運緊密相連,也是勞動人民理想的化身,其言行也必然是下層人民集體意志的體現。
這樣的故事安排和人物塑造在當時依然有著深厚的意味,對于觀眾來講,觀看電影既可以感受到壯族活動地區的山美水美,更主要的是劉三姐這個傳說人物身上的文化政治符碼與普通民眾的相通性“現代化”的劉三姐契合了時代主題的宣傳要求,在構建影像奇觀的同時又將傳說敘述降為尋常敘述,觀眾在劉三姐的形象中獲取到日常氣息,進而理解并接受藝術影片的政治功能。
五、結語:“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
——家國構想與民族儀式
“十七年”時期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中一個尤為特殊的時期,少數民族電影之于中國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藝術文本,一直以來它發揮的都是顯著的政治功能和宣傳功能。柯林斯肯定了情感能量在互動儀式的作用機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這樣一個充滿形而上意昧的詞匯強調的不過是人類發乎情而又難以言說的主觀感受,其玄虛的本質決定了此元素發揮作用的過程背離了定量考察的可能性,情感只可在相對意義上說其濃淡,而無法用數據對其精準衡量。如果將“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敘述活動視為一個完整的過程,那么這一過程與柯林斯所稱的“互動儀式”有著極大的類似性,互動儀式形成和建構的目的就是通過身體感情的協調一致造成群體成員的身份歸屬感,而身份歸屬感的形成和不斷加強是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并且不斷趨向穩定的重要前提。
“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敘述活動的整個過程目的全都是指向家國統一、家國強盛的神話內核,之所以要塑造這一神話內核目的無疑就是新生社會能夠獲得長久穩定和不斷繁榮。
(責任編輯:陳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