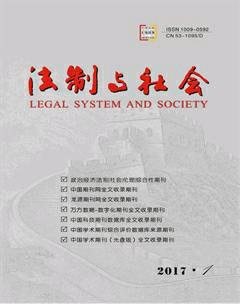警察表明身份程序正當化構造研究
摘 要 本文以“要求警察亮證”這一頻繁發生的熱點事件為視角,闡述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表明身份的程序正當之必要性,并對現行相關法律文件進行梳理同時力求厘清之間的關系,最后聯系實踐對此提出相應立法設計以及司法安排。
關鍵詞 表明身份 正當程序 侵益性 執法
作者簡介:李婕妤,湖北警官學院法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安行政法學和國際私法學。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092
不久前,一段關于警察執法未帶相關證件的視頻在網上熱播。這段長達3分多鐘的視頻顯示:一名私家車主因涉嫌交通違法被交警攔停,車主要求交警出示警官證,交警稱馬上叫人送過來。最后,這名交警選擇轉身離去。無獨有偶,去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位四川女子因用光盤擋住車牌,被成都警方攔下,可該女子不但不配合檢查,反而給了交警叔叔一個耳光。事后這名女子言之鑿鑿地為自己辯稱:“我以為碰上了假警察,因為他們沒有出示證件”。如今,類似這種不配合警察執法的案例,各地時有發生。大家在呼吁各位司機朋友遵章守法文明駕駛的同時,有一個問題同樣值得深思,那就是: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是否需要出示相關證件?身著警服佩戴警徽警號難道還不足以表明警察身份嗎?本文將以“要求警察亮證”這一頻繁發生的熱點事件為視角,闡述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表明身份的程序正當之必要性,并對現行相關法律文件進行梳理同時力求厘清之間的關系,最后聯系實踐對此提出相應立法設計以及司法建議。
一、警察表明身份的程序正當之必要性分析
(一)加強警察執法的公信力
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的表明身份制度屬于行政程序的組成部分,而行政程序作為規范行政權,體現法治在形式上具備合理性的行為過程,無疑是實現法治行政的重要前提。 相反,“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如果執法者連“主動出示證件”這種花費舉手之勞便可做到的程序規定都不愿意或者不屑于遵守的話,又怎么能夠以執法者的身份去要求普通公民自覺遵章守法呢?長此以往的這種行為失范,自然會導致警察執法行為喪失應有的公信力,毀損警方良好的社會形象,也必然會損害法律的權威,影響整個社會遵紀守法的良好風尚。
(二)有利于普通相對人對警察執法工作的制約和監督
應該看到,要求“警察亮證”表明身份,雖然早有規定,但由于長期以來普通民眾權力觀念淡薄,自我保護意識欠缺,很少有人要求警察在執法時出示證件,這就導致為數不少的警察并未形成出示證件表明身份的習慣,面對普通相對人的“亮證”要求甚至不知所措。比如在本文開頭提到的視頻里,面對私家車主理直氣壯的“亮證”要求,交警選擇了轉身離去。為什么?從后續報道可知,這位在成都金沙南路執法的警察的警號是“JF220620”,在成都,以“JF”開頭的警號是協警的標志。所以,視頻中違法司機對警察亮證的要求,無疑起到了制約和監督作用,因為協警并沒有單獨執法的資格。
二、對現行相關法律文件的梳理
通過查詢,筆者發現我國現行的與警察表明身份有關的程序規定不可謂不多。如《行政處罰法》(1996年) ;《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訂) ;等等 。上述法律文件對于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表明身份的程序無一例外作出了規定,在具體條文上幾乎沒有例外的共同表述為“出示執法證件”、“表明執法身份”等類似字樣,但從已經發生的幾起有關案件中,我們發現,對于警察執法表明身份時是否一定要以“出示執法證件”為正當程序,當事人和法院對上述法律文件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對此筆者認為,這里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厘清:
(一)《人民警察法》第9條和第23條的規定是否沖突,應當如何適用
筆者認為,這兩個法條不存在沖突問題。
第一,第9條的要求明確了適用情形,即人民警察在現場執法時,必須出示證件。應該注意到,該第9條是被規定在《人民警察法》第二章“職權”中,而第23條是被規定在《人民警察法》第三章“義務和紀律”中,言下之意,只要是在工作時間,即便不是在執法,該項規定也要被遵守,著警服佩戴警用標識并不足以表明警察執法身份,只是常規紀律和義務的組成部分。可見這兩個條文針對的事項是不同的。
第二,即使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對于行政類法律來講,也應該做嚴格解釋,而不能僅憑個人的理解做擴大解讀,更不能選擇有利于自己的解釋來執法。這是由行政法控制行政權力的立法原理決定的。
(二)《行政處罰法》與《人民警察法》是否存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問題
有人認為,《行政處罰法》要求執法人員執法時出示身份證件,而《人民警察法》規定警察執行公務時可以有兩種表明身份的方式:一是按照規定著裝,佩帶警銜警徽等警用標識;另一種方式則是出示人民警察證件。由此可見,執法人員執法時是否應當出示身份證件,《行政處罰法》與《人民警察法》的規定不一致。于是有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處罰法》為一般法,適用于所有行政執法人員,而《人民警察法》系特別法,僅適用于警察執法。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所以應該適用人民警察法的規定。
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筆者認為,《行政處罰法》和《人民警察法》并非特別法和普通法的關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關系。當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間發生適用上的沖突時,應當適用“上位法優先于下位法”的規則。而“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規則適用于相同位階的法律之間。
三、對警察表明身份正當程序的立法建議
上述法律文件對于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表明身份的程序義務雖有規定,但因為源出多頭,對不同的表明身份的形式沒有做系統的分門別類,從而導致學理上的混亂、執法者的無所適從以及普通民眾的眾說紛紜。對此筆者有如下建議:
(一)嚴格警察表明身份主要程序(即出示證件)的適用情形
從理論上講,警察在任何執法行為中,都應該主動向相對人出示證件,表明身份。但在實踐中要求警察在作出任何一個行政行為之前都去出示證件,不太可能同時也并無意義和必要。筆者在此處重點說到的是嚴格表明身份主要程序(即出示證件)的兩種情形:
1.執法場所具有流動性:
有著固定辦公場所的執法行為先天給予相對人一種信賴利益,比如普通民眾前往派出所辦理戶籍登記,從事窗口服務的警察是否有向每一個相對人表明身份的必要?事實上,既然相對人主動前往派出所辦理相關業務,表明相對人明確知悉警察的身份和權限,同時對這種身份和權限予以承認。相較于這種非流動性執法場所,法律應該對在鬧市或街頭等流動性場所執法的警察有著更為嚴格的表明身份的程序性要求,事實上,流動執法場所的不確定性使得普通相對人對警察的身份表明更為需求,所以立法有必要對在流動場所執法的警察作出嚴格要求其履行“出示證件”這一主要表明身份的程序義務。
2.侵益性執法行為:
所謂侵益性執法行為,是指給相對人帶來不利后果的執法行為,通常表現在執法主體為相對人設定義務或者剝奪、限制其權益。比如行政檢查和行政處罰; 與之相對應的是授益性執法行為,而授益執法行為是指執法主體為相對人設定權益或免除其義務的執法行為。相較于授益性執法行為,侵益性執法行為對警察表明身份的程序要求應該更加嚴格化和制度化。當然,我們也并非認為授益性執法行為就不用表明身份,只是其形式可以更多樣化。
(二)規定警察事先免除表明身份義務的情形
實踐中,警察的執法活動有時會非常急迫,來不及出示證件表明身份,或者不適合出示證件讓對方知悉自己的警察身份,此時就需要事先免除警察的表明身份義務 。現行立法應對下列事先免除表明身份義務的情形進行歸納整合:
1.緊急情形下:
緊急情形往往是指警察面對相對人暴力抗法、持械襲警等突發性事件,來不及出示證件表明身份,必須及時阻止、制伏行為人,否則將帶來生命或財產上的損失。此種情況下,執法民警可以口頭表明身份,先將行為人制伏。當然,在緊急情況解除后的第一時間內警察應當補充履行出示證件表明身份的義務。
2.隱蔽執法時:
警察在進行隱蔽性執法活動時,比如交警查處黑車,如果事先向相對人出示證件表明身份,勢必會影響調查取證的順利進行,所以此時立法應免除警察事先表明身份的義務。當然,在調查取證完畢進入行政處罰環節之前,警察應當履行嚴格的出示證件表明身份的義務。
3.對喪失辨認控制能力者實施強制措施時:
對不能辨認控制自己行為的相對人,如深度醉酒者、失控狀態下的精神病人,在實施強制措施之前出示證件表明身份毫無意義,所以此處也屬事先免除警察表明身份義務的情形。當然,在相對人恢復清醒、情緒穩定時,警察應當在第一時間內,向相對人補充履行表明身份義務。
注釋:
應松年.行政程序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10.
王晨.行政檢查芻議.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10 (2).
張碩.作為一般前置性程序的表明身份制度.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4(9).
《行政處罰法》第34條規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9條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當場盤問、檢查;該法第23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按照規定著裝,佩帶人民警察標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證件,保持警容嚴整,舉止端莊。
如《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證使用管理規定》(2008年);《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2013年);《公安機關適用繼續盤問規定》(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2004年);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2010年);《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治安管理處罰法》(2012年修訂);《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