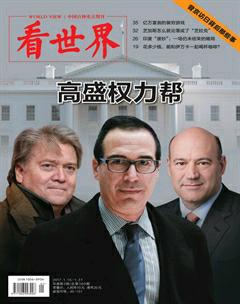1891年,沙俄王儲在日本遇刺刺客是日方安排的隨行警衛
紅色獵隼
沙俄王儲遇刺
1891年5月11日,日本滋賀縣大津附近的街道上,兩位外國來賓的到訪打破了當地日常安寧平靜的生活。在諸多日本警察的護衛下,當時仍是沙俄帝國王儲的尼古拉二世乘坐著富有東方特色的人力車穿行而過。而就在他沉浸于眼前的異國風情之時,尼古拉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被人連續重擊了兩下,一陣頭暈目眩之際,他也顧不得流血的傷口,慌忙跳下人力車拼命向前跑去。而在其身后高舉著利刃的刺客,還想再次揮刀砍殺,卻被從旁趕來的希臘王子喬治(1869—1957)用剛買的日本竹杖打翻在地。此時在旁護衛的日本警察才如夢初醒般地一擁而上,將刺客制服。此即“大津事件”。(大津事件又因為發生在日本風景名勝琵琶湖以南,被稱為“湖南事件”。)事后經調查確認,試圖行刺尼古拉二世的是日本方面安排的隨行警衛之一——隸屬滋賀縣警察局的津田三藏。
尼古拉二世雖然頭部連中兩刀,但所幸有禮帽遮擋,僅為皮肉擦傷。不過身為王儲在他國遇刺,無疑茲事體大。在巨大的外交壓力之下,日本政府隨即對這起事件展開了深入的調查。而坊間以訛傳訛,演化出了多個有趣的版本,比如就有人認為當時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的小說《菊子夫人》(一般認為,《菊子夫人》是皮埃爾·洛蒂根據自己東亞海域服役的真實經歷撰寫的愛情小說,文中的菊子是為男主在日本度假時租的臨時夫人。)風靡亞洲,尼古拉二世也由此產生了對亞洲女性的濃郁興趣。而正是在日本多次出入風月場所的行徑引起了津田三藏的強烈不滿,最終拔刀相向。
另一派觀點則認為尼古拉二世此行的目的是針對日本的武力威懾和刺探軍情,因此言辭傲慢且行蹤可疑,津田三藏眼見于此,最終才鋌而走險。但客觀地分析后不難發現,尼古拉二世在日本的遇刺與其說是一個偶然,不如說是當時日、俄雙方國家戰略層面無可避免的沖撞。
俄羅斯的算盤
出訪日本,已是尼古拉二世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1890年10月,尼古拉二世乘坐沙俄海軍新銳的裝甲巡洋艦“波爾塔瓦”號從圣彼得堡出發,經地中海訪問希臘等國,捎上了自己的遠房表弟——希臘王子喬治之后,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印度洋。在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新加坡等英國殖民地港口停泊之后,“波爾塔瓦”號又遍訪了當時仍處于荷蘭統治之下的爪哇島和亞洲為數不多的獨立王國暹羅,以及中國的香港、上海、廣東等地,最終才抵達日本的長崎。
從這里不難看出,尼古拉二世此次出訪名義上是為了前往海參崴主持西伯利亞鐵道開工儀式,實際上卻是在勘查沙俄海軍從歐洲開赴遠東的航線和沿途的補給港口。畢竟此時的沙俄帝國雖然在太平洋西岸擁有了諸多軍港,但苦無大型造船工業,配屬到這一方向的戰艦均需從歐洲調撥。而一旦在遠東發生戰事,沙俄海軍主力更可能需要萬里馳援。事實上尼古拉二世所走的這條航線恰恰是沙俄海軍進入東亞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日后奔赴戰場的“第二太平洋艦隊”沒有英國政府的綠燈,最終只能取道非洲沿岸,在師老兵疲的情況下全軍覆沒。
日本是尼古拉二世此行的重中之重。從1891年4月27日抵達長崎到5月19日離開,尼古拉二世計劃在日本停駐近一個月的時間。如此漫長的逗留背后,這位年輕的沙俄王儲究竟有怎樣的計劃?后世盡管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可以想見無非基于日俄修好的目的,畢竟在西伯利亞鐵路全線貫通之前,沙俄帝國遠東地區尚無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爭,因此尼古拉二世有意向日本示好,謀求日俄同盟鉗制滿清帝國的可能。
這也就解釋了尼古拉二世在日本期間頻繁參與各種日本民間的風俗、祭祀活動,甚至在自己的右手上紋上東方的龍型圖案。前文中所提到的《菊子夫人》的確也曾影響到尼古拉二世的此次訪問,許多沙俄海軍的將校抵達長崎之后,紛紛想要效仿皮埃爾·洛蒂去租用一個日本的“臨時太太”,但最終被尼古拉二世以“馬上就到復活節了,你們還在想這些下流的事情!”喝止了。
日本政府對尼古拉二世的到訪也是極為重視,不僅派出了曾在英國留學的有棲川宮威仁親王全程陪同,更由迎娶了沙俄太太的公卿萬里小路正秀擔任翻譯。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高規格地接待,也無非是出于全力與滿清爭奪朝鮮,不愿過多樹敵的目的。但就在兩國高層所營造的這種“日俄親善”氛圍之下,日本國內的民族情緒卻正在不斷抬頭。
民族主義情緒引爆危機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武士階層大多為依賴田租生活的“有產者”。而隨著“四民平等”和“版籍奉還”,自藩主以下的武士階層名義上不再擁有土地收入,但是為了安撫這些改稱“士族”的特殊階層,明治政府還是以“家祿支給”的方式維持其基本收入。根據1871年編制的“壬申戶籍”,日本士族約占總人口的5%,盡管比例不是很高,但是近200萬的絕對數量已經使得明治政府每年支出的士族俸祿高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強。
為了擺脫這個沉重的財政包袱,自1872年開始,明治政府連續出臺了“祿制整頓”、“家祿奉還”以及“金祿處分”等一系列政策。應該說當年德川幕府可以維持收支平衡,明治政府沒有理由無法做到,但明治政府此時幾乎同時在進行著新式海、陸軍的擴充,名為“殖產興業”的工業化改革,鐵路、電信、郵政網絡的基礎建設,外加上現代化的教育普及,這些耗資不菲的項目,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財政負擔,而基于日本昔日農業國的身份,這些錢自然只能通過犧牲農民和士族的利益來籌集。
1876年8月5日,明治政府突然宣布發行“金祿公債”,也就是說士族往后本應拿到手的俸祿,被政府全部強制購買了五年期的國債。每年士族只能支取5%到7%不等的利息,而本金在5年之后以抽簽的方式分30年支付。此時日本全國的士族仍超過30萬人,而士族平均每人卻只能拿到500日元,僅相當于德川幕府時代的一百石。
當然明治政府也不想將士族趕盡殺絕,在宣布“金祿公債”改革的同時,明治政府還開展了名為“士族授業”的活動,即號召生活困難的武士移民北海道,加入當地“屯田兵”的行列。日本武士以家族為單位廝殺了上千年,為的就是關西的膏腴之地,誰愿意被趕往苦寒的蝦夷呢?于是在良馴者舉家遷徙的同時,各地對明治政府不滿的士族開始聚集起來,并最終引發了一場名為“西南戰爭”的全面反彈。
試圖在大津刺殺尼古拉二世的日本警員津田三藏也出身于武士階層,其父曾是效忠幕府的藤堂家的藩醫。明治維新后津田三藏加入了新組建的日本陸軍,并參與了“西南戰爭”的平叛之役。但帶著一身傷病結束遠征鹿兒島的軍事行動之后,津田三藏等來的卻不是加官晉爵,而是被趕出現役轉入地方警察的結果。巨大的心理落差令其產生了可怕的心理扭曲。
無獨有偶,“西南戰爭”結束之后,日本陸軍近衛炮兵大隊也曾因為政府未能支付“特別津貼”,而炮擊大藏卿(財政部長)大隈重信的宅邸,釀成了史稱“竹橋兵變”的惡劣事件。津田三藏沒有向自己領導揮刀的勇氣,只能找尼古拉二世的晦氣。事情發生之后,雖然明治天皇睦仁不顧可能被扣留的風險,趕往尼古拉二世的座艦致歉,但對于尼古拉二世的指責,他除了一句“哪個國家都有神經病”之外也實在給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總之尼古拉二世的日本之行,可謂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盡管此后關于津田三藏是否應被處以死刑的問題在日本國內引發了長久的爭論,但這個小人物的生死其實對日俄關系早已沒有任何的影響。所謂尼古拉二世因“大津事件”對日本產生敵意或者恐懼的說法,事實上并不成立,但在尼古拉二世回國后不久,日俄在遠東地區現實的利益沖突還是令兩國演變成了面前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