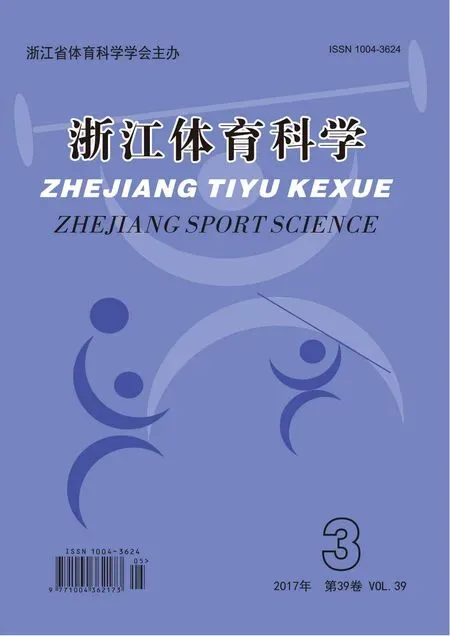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學研究
——基于傈僳族聚居村寨“片馬鎮”的田野調查報告
汪 雄,陳玉林
(玉溪師范學院 體育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
?
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學研究
——基于傈僳族聚居村寨“片馬鎮”的田野調查報告
汪 雄,陳玉林
(玉溪師范學院 體育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從“發生學”的理論研究視角入手,旨在為保護與傳承當下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尋根”和“號脈”。運用田野調查研究方法,以“發生學”為理論支撐,采用質的研究范式,分析了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機制,進一步探尋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發生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不是一種孤立的民俗事項,它的發生與村落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有密切關聯;受特殊地域環境的束縛,傳統體育項目的種類與文化獨具特色,呈現出休閑娛樂性、藝術表演性、競技性等特征;發生機制的影響因素較多,并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體育人類學;發生學;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滇西邊陲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滇西邊陲瀘水縣片馬鎮傈僳族聚居村落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機制為研究對象,主要涉及傈僳族村民、民族傳統體育傳承人、縣文化館和文化站的相關負責人,共計18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利用中國知網、維普、高等教育文獻等數據庫,查閱了地方志、民族史、民族傳統體育等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論著,涉及傈僳族的婚俗觀念、宗教信仰、村寨自然環境、社會制度習俗、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
1.2.2 田野調查法。在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通過課題組成員的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詳細記錄都是體育人類學相關課題研究中獲取第一手資料的方法和途徑。本課題研究共進行實地考察3次,第一次是2013年農歷二月初7—9,研究小組前往瀘水縣片馬鎮考察了傈僳族的“刀桿節”儀式活動,主要了解傈僳族的村落環境、宗教信仰、節慶傳統體育活動,并確定調查訪談對象和聯系方式,為下一步調查研究作好準備;第2次是課題組于2014年10月1—6日自駕車前往調查目的地,對已確定為調查對象的傈僳族村民、家庭以及村落的人文地理和社會制度習俗、神話傳說進行全面考察和深度訪談;第3次是2016年農歷的二月初6—10,課題組對傈僳族傳統節日“刀桿節”儀式活動進行再此考察和回訪。3次考察,歷時共15日,拍攝視頻約300min,錄音約110min,采集照片200余份。
2 研究結果與分析
2.1 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學分析
“發生學”是指在地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生物種系的發生和發展[1]。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視角,在人文科學領域運用日漸頻繁。然而,“發生學”與“起源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強調主觀認識,后者強調客觀現象[2]。因此,發生學是邏輯推理概念,而起源學是歷史時間概念。發生認識論的中心問題是關于新結構的構造機制問題,發生學探究與認識相關的結構生成,不僅研究認識如何發生,也研究認識為何發生[3]。為此,課題組借助上述發生學的相關理論,將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機制歸為兩大系統,一是自然環境系統,二是社會環境系統。本課題的研究也將從這兩方面展開對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進行邏輯推理,深入挖掘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演進在發生學上的存在意義。
2.1.1 自然環境——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的萌發。傈僳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機智、彪悍、聰慧賢能、能歌善舞的云南特有少數民族之一。傈僳族屬古氏羌人,與彝族同屬一個族源,其族別名稱最早見于唐代著述。唐代史籍稱“栗粟兩姓蠻”或“栗蠻”及“施蠻”、“順蠻”,均屬“烏蠻”,分布在今川、滇的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兩岸等廣闊地帶[4]。本研究調查的村落地處世界級資源遺產“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帶。傈僳族人民世代深居大山密林,過著半農半獵的生活,抬頭見山,邁步遇溝,行路攀峭壁,越溝壑,自然環境為他們創造了許多天然的體育鍛煉場所。
特殊的地理因素,造就了云南怒江“四山三江”的獨特地理風貌,高而險峻的山脈阻礙了傈僳族人民的社會交往,耕地面積的稀少或未開發限制了農業生產生活,獲取物質生活資料必須改變現實。水勢迅猛,渡江艱險,江流隔斷,形成獨家散居的居住形式,傈僳族民族主要建居于山腳、半山腰、山頂,長期以來過著與世隔絕的自給自足的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極其鮮明地反映了傈僳族民族的現實生活情景,如采摘果實和捕魚等活動,由此也練就了傈僳族人民獨特的民族個性和特殊的生活技能。
由于農耕生產受限,傈僳族人民必須轉變獲取生活食物的途徑和方法。然而其特殊的自然環境成為各種動物自由生長繁衍的樂園,動物資源豐富而且種類繁多,為傈僳族人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資源。于是傈僳族人民開始以狩獵來維持生計,捕獲動物獲取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形成一種既適應自然又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特殊力量。
傈僳族先民的生產生活技能在這一特殊環境下逐漸顯現出來,人們通過與自然環境的斗爭,衍生出許多身體活動形式,其活動形式主要表現為渡江的“溜索,游泳”,狩獵的“弓弩,投擲”器械,圍獵的“武舞”活動以及模仿動物的“舞蹈”等[5]。這些身體技能既來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逐漸脫離于母體環境演變成傈僳族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形式。
2.1.2 社會環境——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的演進。“宗教”(relig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釋義,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社會屬性。在人類歷史的演變中具有強勁的影響功效,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具有權威性的精神統治力量和核心上層建筑,它為社會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并逐漸形成一套具有評判社會行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體系標準[6]。總而言之,宗教是各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的普遍社會現象,是對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對異己力量所做出的神圣化的、顛倒的反映,并對人類發展歷史及現實生活都產生著重要的影響。由此看來,原始宗教對民族傳統體育的產生與發展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主要處于依賴靠天吃飯和靠神支撐的歷史時代,作為由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始部落氏族中的傈僳族人民也同樣如此。崇拜動物的現象也只有到了對物質生活資料急切需求的時期,才會對社會生活中的人獲得特殊的意義。一方面傈僳族先民為了通過狩獵活動獲取所需食物,必須增強自身意識,不斷積累經驗并努力適應和改造自然,使得人類成為大自然之外的異己力量,越來越對改造自然和戰勝自然充滿自信,探究獵物活動規律,形成一項捕獲動物的生活技能。另一方面傈僳族先民逐漸意識到獵物的兇猛和攻擊性,由于害怕而被迫把某些動物當作圖騰來崇拜,加深了對圖騰崇拜的依賴性。無論是出自獲取物質資料利益或因敬畏而產生的崇拜,可以說都是僳僳族先民當時經濟生活與宗教信仰建立的直觀反映,在人們日常活動中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宗教儀式。
在日趨頻繁的宗教儀式活動過程中,傈僳族先民既要祈神求福、頂禮膜拜,把甜蜜的歌聲和優美的舞姿獻奉給自己心目中的神靈,又要不甘示弱、頑強拼搏于大自然間,用鏗鏘有力的巫術咒語來脅迫神靈。二者既矛盾又統一,在其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此消彼長之勢,不斷左右著傈僳族先民的思想,日常生活如此,民族傳統體育也不例外。宗教儀式活動是傈僳族先民生活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既阻塞了生活又促進了生活,是傈僳族先民認識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異己生產力。
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神靈觀念、巫術、禁忌、宗教節日以及神話傳說等,其表現形式主要涉及舞蹈、競技、娛樂、生存技能展示等。
由于歷史原因,傈僳族人民至今仍遺留有原始部落形態的行為模式,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具風采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沖擊下,傈僳族原生態的民族舞蹈以及體育活動得以完整保留并傳承沿襲至今,對于人類學家、藝術家的研究都顯得尤為彌足珍貴。經歷長期的歷史洗禮和不斷積淀,在原始宗教的影響下,這些古老的祭祀神靈舞蹈,狩獵技能舞蹈,模仿各種圖騰崇拜動物的舞蹈逐步演變成為傈僳族人民強身健體、愉悅身心、富有激情的特色民族傳統體育活動。
2.2 “發生學”視野下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的表現形式和文化特征
2.2.1 表現形式。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在經歷長期歷史的洗禮和發展過程中,必將深深地印染了本民族的意識形態和思維觀念,而原始宗教信仰是其傈僳族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內容,并大多以原始狩獵歌舞的形式為載體逐漸展開。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通過原始狩獵場景的歌舞增加了內容,擴展其影響,并逐漸傳播和傳承,以此推動了傈僳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是對傈僳族先民的發展歷史、生活習俗以及民族心理的最真實、最生動的記錄和描繪。
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內容豐富、演繹著自己獨特的風采,具有鮮明的民族魅力和個性。主要有休閑娛樂性、表演性、競技性三種形式,從表現形式上看主要有歌舞、象形仿生、祭祀娛神等特點;從動作節律上看,有技術要求較強的技藝類、舞樂結合的節奏強烈、屈膝彈跳且動作幅度較大等特點。
2.2.2 文化特征。
2.2.2.1 休閑娛樂性。受傳統文化以及各種歷史條件的影響,環境閉塞,與外界接觸較少,在自然純樸的生態環境中緩慢地發展。但同時又需要文化娛樂活動來滿足人們生活,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正是為了適應人類社會而產生發展的,并逐漸成為人們休閑娛樂、溝通情感、美化生活不可缺少的群眾性娛樂活動內容。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休閑娛樂類項目主要有射弩、秋千、頂杠、陀螺、扭扁擔、拿石頭、跳蘆笙、溜索等形式[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活動是秋千和陀螺。秋千極富娛樂性質,人們經常在茶余飯后閑蕩秋千,參與主體為傈僳族婦女,是一項很普遍、很受歡迎的體育活動,秋千又分為蕩秋、磨秋、車秋三種,現在農村每逢傈僳族自己的盛大節日,蕩秋千是必不可少的傳統體育活動。打陀螺不受場地的限制,隨意在自己院壩就可進行,以抽擊動作為主要形式,制作主要采用樹木枝或根,自己親自削剝而成,大小隨喜好而定。活動時,用一端系有棕樹葉或布條的木鞭抽打,使其旋轉,享受起快感帶來的樂趣。
2.2.2.2 藝術表演性。傈僳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幾乎男女老少都能歌、能舞、能彈,俗有“鹽不能不吃,歌不能不唱”之說。傈僳族的樂器主要有琵琶、口弦、竹笛、葫蘆笙、二胡等;傈僳族的舞蹈有模擬自然的,有表現勞動生產和反映風俗禮儀的,也有模仿動物的和婚喪祭祀的,如“婚禮舞、喪儀舞、祭祀舞、生產舞、狩獵舞、嗄切舞、蘆笙舞”等。最富表演性的活動是“上刀山,下火海”,進行表演時,在刀桿場上豎起兩根20多米長的松樹桿,在樹桿之間順序捆36或72把鋒利的刀刃向上的鋼刀作梯子。表演者赤手光腳,蹬上頂端,做“蜻蜓倒立、飛燕迎春”等高難動作[8]。下了刀桿后,勇士們還要赤裸上身、光著腳跳入熊熊烈火中,甚至用身體滾壓火海,直到碳火熄滅,以圓滿完成“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驚險表演。表演后群眾一起唱歌跳舞,呈現出節日的歡樂氣氛,充分體現了傈僳族人民機智勇敢和知難進取的優良民族品質。
2.2.2.3 競技性。傈僳族是一個長期靠山生活的古老民族,地處懸崖峭壁,山勢險峻,灌木茂密,沒有較為寬敞的平地。傈僳族人民利用現存的自然條件,因地制宜開展適宜于自己本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競技性帶有明顯的山地氣息,衍生出許多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9]。主要表現為“射弩、游泳、砍竹竿、投擲、武術、溜索、泥彈弓”等活動形式。其中最為盛行的是“射弩、溜索”,真實記錄和反映了傈僳族人民的生產生活。射弩,包括射粑粑、射頭頂雞蛋、射刀刃等。傈僳族有“拉不開弓的就不算男子”一句俗話,足見其射弩在生產、生活中的地位。明代《景泰云南圖書志》卷四有“有名傈僳者常帶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傈僳族在歷史上還有“尤善弩,每令其婦負小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傷婦”的稱頌。傈僳族的弩箭是一種利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弓,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其形狀的確定,材料的選擇,箭鏃的安裝,箭尾尾翼的設計等,都體現了的科學原理和技術的含量,是傈僳族人民聰明智慧的歷史結晶[8]。每年農歷正月初一至初三,傈僳族男子都要舉行射弩比賽。正式比賽時,由兩男一女擔任領隊,一男肩上扛弩弓,包頭上斜插一只箭,一男兩手舉著飾有彎弓和箭的標志的紅、白兩色旗子。選手列隊通過彩門進入廣場,圍著旗桿向紅白兩色旗祭酒,跳集體舞,舞罷開始比賽。比賽時用傈僳族民間的特色食品設為靶,如油煎粑粑和肉片,射手按順序比賽,射中“獵物”歸自己所有。溜索,溜索已經從單純的交通工具發展為表現各民族頑強意志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過溜有單人、雙人、男女混雙、人與物、人與畜等多種項目,成為怒江大峽谷一大驚險景觀。繩索有牦牛毛繩、藤編繩及鋼絲繩等多種。過渡者將竹、木制做的溜板或特制座位,吊在繩索上,借助于繩索的傾斜度,溜向彼岸。具有表演性質和競技性的特點,是少數民族運動會上的重要比賽項目之一。
2.3 發生機制對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的催衍作用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宗教信仰都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不斷積淀,民族傳統體育的產生與宗教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形成一對矛盾的綜合體,互為制約和促進,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由于體育和宗教在本質上的對立,宗教在總體上對體育的發展起阻礙作用;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發展階段和歷史條件下,宗教儀式中的某些派生因素,在客觀上又對體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0]。這就使得宗教和體育之間產生了相互滲透的現象。在宗教活動中包括了民族傳統體育的內容,而又在民族傳統體育中殘留有宗教的禮儀和思想觀念。自然環境、社會制度習俗對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產生和發展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2.3.1 傈僳族狩獵技能的形成。一方面,特殊的自然環境對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傈僳族先民捕獵獲取物質資料以滿足生活。另一方面,因動物的兇猛而難以征服,傈僳族先民因害怕而變得對其敬畏,由此而產生對動物的圖騰崇拜,進行心靈美化。既害怕又需要,為了生存人們還得與自然作斗爭,不斷改進方法和手段,形成有效的狩獵技能,并逐漸形成固定的模式,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剝離出來形成本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
2.3.2 傈僳族原始宗教舞蹈的產生。在原始社會時期,傈僳族民族信仰圖騰崇拜、自然崇拜以及神靈崇拜,主要活動為巫術和祭祀神靈。一方面,人們由于害怕不能征服自然,寄希望于自然界之外的異己力量,通常把優美的歌聲以及優雅的舞姿獻奉給自己的神靈,祈福保佑。另一方面,人們又通過口誦默念咒語,起舞造勢以驅逐神靈。這一系列或者包含和孕育了原始體育活動的萌芽和雛形,通常采用幻想和模仿性的動作來影響和控制不能理解的自然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踐行了體育的行為,實現了體育的健身娛樂功能,由此逐漸產生和形成一定模式的宗教舞蹈活動。
2.3.3 原始宗教對云南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促進。原始宗教活動中,人們為了取悅神靈而涉及繁多的宗教儀式,但隨著現代文明的高速發展,宗教因素和色彩逐漸淡化,愉悅身體的元素和價值逐漸加強。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具有強烈的民俗特征,在大多節日慶典和宗教祭祀活動中都伴隨有明顯的身體活動,久而久之,宗教意義逐漸弱化,人文色彩以及體育運動的因素逐漸凸顯,最后脫離原始宗教的束縛而演變成傈僳族彌足珍貴的體育文化財富[10]。傈僳族現在的射弩、秋千、陀螺、溜索、狩獵舞、爬刀桿、下火海、砍竹竿、阿尺木刮等包含了民族傳統體育的內容,都極具增強體質、愉悅身心的體育價值和意義。
3 結 語
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是一種民俗事項。從“發生學”的理論研究視角看,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往往與少數民族聚居的村落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兩大系統存在著十分緊密的內在聯系。縱觀滇西邊陲傈僳族聚居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生機制,深受其傈僳族人民長期遺留的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傳統節慶、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特有的文化事項和民族特性,并對傈僳族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總而言之,也只有從“發生學”的理論意義上探尋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根”,厘清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性,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植根的“土壤”里探尋演進發展的規律,才能對當下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傳承與發展準確“尋根”和“號脈”,并及時輸送“營養液”,實現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長效發展。
[1] J.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M].王憲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 J.Piaget,ThePrinciplesofGeneticEpistemology, Routeledgeand Kegan Paul,London ,1972.
[3] H. E. Gruber and J.J.Voneche (eds), The?Essential Piaget, Basic Books, New York,1977.
[4] 王聲躍.云南地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00-311.
[5] 劉堅.云南民族傳統體育旅游資源與產業化研究[M].昆明:云南科學出版社,2000:9.
[6] 阿.克雷維列夫.宗教史(上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0.
[7] 云南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8] 方征.淺談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J].體育文化導刊,2002(3).
[9] 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傈僳族文化大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10] 盧元鎮.體育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2-239.
Research on Genetic of Minority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Village——the field survey on Lisu areas of Yunnan western frontier
WANG Xiong,CHEN Yu-li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Sports Institute, Yuxi 653100, China)
From the view of "Genesis"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aimed a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inority Traditional Sports Village "roots" and "vein". The use of field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taking "learning"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to the village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pl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llage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is not an isolated folk custo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village of it; bound by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sports project types and unique cultur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entertainment, performing arts, sports and so on; many factors affect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physical anthropology; genesis; Lisu;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Yunnan border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體育類):國家認同視閾下西南跨境民族體育融通與邊疆治理研究(16BTY011);國家社科基金:少數民族武術文化影像志(16CTY018);2016年度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資助項目
2016-12-07
汪 雄(1982-),男,云南玉溪人,副教授,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及其文化研究.
1004-3624(2017)03-0041-04
G812.4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