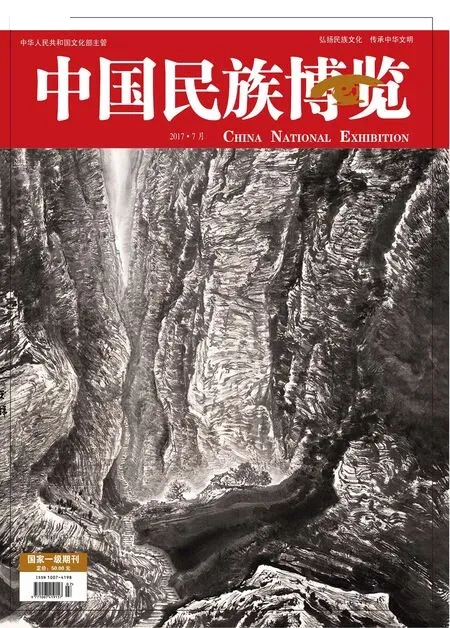《巴拉根倉的故事》的流變與地域習俗
雪 蓮
(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巴拉根倉的故事》的流變與地域習俗
雪 蓮
(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在蒙古族民間文學的范疇里,不僅有著多種主題的民間故事,內容還格外豐富。其中《巴拉根倉的故事》流傳十分廣泛。從內蒙古自治區的科爾沁、錫林郭勒等地到蒙古貞、青海,只要是蒙古民族居住過的地方,幾乎沒人不知道巴拉根倉。主人公巴拉根倉是千伶百俐、幽默風趣的蒙古族草原牧民的代表。《巴拉根倉的故事》是由口頭稱述的形式廣泛流傳下來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細微差別。本文主要運用故事的流變,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歷史等因素的影響。
巴拉根倉;蒙古族;民間故事
一、研究背景
《巴拉根倉的故事》符合了故事學的虛構性、世俗性、娛樂性等文類特征。并且非常短小而簡單,每一個故事的形式都是主人公伶俐機智的才能智勝了對方,是蒙古族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共同塑造出來的智慧的結晶。正如高爾基所說:“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從其勞動和社會經驗中抽取出來的知識總匯”。《巴拉根倉的故事》正是蒙古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的體現,是人們用日常的閑暇時間或集體勞動時間,用講故事的方式來釋放自己內心的不滿。正因為故事符合了所有蒙古族人民內心深處的想法,所以才會流傳到各個不同的地區。
現代文化已經影響到我們年輕一代,并逐漸跟古老的文化脫離了,不僅僅是孩子,連家長都離不開手機和電腦了,更不會在閑暇的時候講故事給孩子聽。或許是因為“退牧還草”政策的原因,放牧時用講故事當作日常樂趣的牧民們也逐漸地城市化了。于是,能講故事的人越來越少,從老人那里聽了故事后絲毫不在意的人也不少。在這種情況下,從古到今一直流傳下來的蒙古民間文學有了被淹沒的危險。所以筆者想通過《巴拉根倉的故事》在不同地方流傳的異文,分析出各個地方的特色文化,呼吁人們去關注民間文學的存在,以及它所表達的真正的含義所在。
二、文本介紹——繞過掉在地上的肉
春暖花開,一天,縣太爺出去打獵帶上了巴拉根倉。因沒來得及吃飯,巴拉根倉便帶上了幾塊兒烤肉。路上饑餓難忍,他拿出來烤肉邊趕路邊吃,突然,從灌木叢中躥出一只兔子。
“快追,抓住它。”縣太爺下令道。
巴拉根倉因一時著急把剩下的幾塊肉揣在懷里,不料把烤肉掉在了地上。他想下馬撿起來,可縣太爺發怒道:“狗奴才,掉在地上的肉是臟的,別撿了。”
聽后,巴拉根倉沒有回答,騎上馬追兔子去了。獵殺完兔子繼續往前走著,碰見幾頭野豬。野豬驚慌逃竄,驚動縣太爺的坐騎,縣太爺從馬背上摔了下去。巴拉根倉追著野豬,就像沒看見似的從正在呻呤的縣太爺身邊策馬而過。縣太爺生氣地吼道:“喂!巴拉根倉,你沒看見我摔倒在地上嗎?為什么不扶我起來,不管不顧呢?”
巴拉根倉對縣太爺說道:“掉在地上的肉是臟的。不能撿起來這塊兒臟肉。”說完,他撇下縣太爺快馬加鞭追野豬進了密林。
三、異文比較分析及其文化背景
筆者根據不同的異文,發現了《巴拉根倉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從而探索出這些變化發生的因素有哪些。
(一)變體文本的共同點
第一,不同異文中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基本一樣,情節結構都是同一個模式:先是由王爺、縣太爺、活佛等地位較高、有權力的人使喚主人公,并向他挑釁。而每一個故事的最后,主人公都會以自己巧妙而風趣的機智手段戰勝其敵手。
第二,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屈于上層階級,善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除了上述故事異文以外的所有《巴拉根倉的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正義的捍衛者。
(二)變體文本的不同點
1.主人公的名字
筆者發現,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對主人公的稱呼有所變化,從巴拉根倉變成了仆人、徒弟等。但筆者認為,雖然他們的地位比較底,被稱呼為仆人、徒弟。但當地人們在講述的時候,前面都加了聰明的、唯一的等形容詞,這能說明主人公在蒙古人的心中有著跟巴拉根倉相同的地位。所以筆者認為,故事在口頭的流傳中,當地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換了對主人公的稱呼,表面上看起來每一個主人公的地位都很低,但在人民的心里都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2.細節方面
筆者發現,故事在不同地方流傳的過程中,很多細節上都增加了地方特色,聽起來好像就是來源于他們家鄉的民間故事一樣。
1)錫林郭勒流傳的異文
錫林郭勒盟有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元上都遺址,元上都是世界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為數不多的幾座都城之一。所以,上述的故事流傳到錫林郭勒時,就演變成了王爺帶仆人進城的開端。并且,由于錫林郭勒盟還是中國草原紅牛的產地之一。因而故事中所提到的,掉在地上的肉變成了牛肉干。
2)青海流傳的異文
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是青海佛教寺院最大叢林之一,也是中國的一大名勝古跡。由于青海地區有著濃郁的佛教文化,故事流傳到青海時,變成了活佛與徒弟之間發生的故事。
柴達木盆地是中國三大內陸盆地之一,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是一片沙漠景象,那里分布的動物主要有駱駝,因此故事中的野豬和兔子,在青海的異文中變成了駱駝,這正是當地的特色之一。
3)蒙古貞流傳的異文
“蒙古貞”一詞在特定的條件和廣義上是“蒙古的”“蒙古們”之意。別名為“蒙郭勒津”,是蒙古族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部落。所以,流傳到蒙古貞的異文中包含了錫林郭勒異文里出現的王爺、吃牛肉干、騎馬等現象,連王爺責備主人公的用詞都基本一樣。
筆者發現,青海的異文跟其他幾個地方的故事有所區別,雖然想表達的想法是一樣的,但在細節、情節方面的共同點很少。所以,筆者認為講述者只運用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在別的情節上都是按自己的意愿講述的。流傳到青海的故事最后提到:“可恨的活佛一時無語,從那以后,活佛一改對徒弟的態度,不再那么辱罵徒弟了”,這才是講述者真正想表達的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他們想要的結果,也是最完美的結局。
四、總結
普羅普認為,故事情節中存在著不變的因素和可變的因素。變換的是角色的名稱以及他們的物品,不變的則是他們的行動或功能。例如:故事里的人物無論多么千姿百態,無論是巴拉根倉、王爺還是活佛都做著同樣的事情,或者在于考驗主人公,或者在于輔佐主人公。同樣,主人公反駁惡勢力的方式雖然有所不同,但最終的目的和結果都是一樣的。由此普羅普提出,功能的實現方法可以變化,因為它是可變的,但功能本身是不變的因素。在不同地方流傳的故事異文的英雄其實只有一個,只不過在流傳的過程中,每個講述人的語言表達水平是不同的。表達能力好的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把故事的情節講得井井有條,同時還受當時的場景、聽眾的反應等因素的影響。當然,能夠即興發揮的人,更能扣人心弦。而言語單調的人只能把故事的主要部分說出來,沒有可以吸引人的情節。故事會由于講述者情緒的變化,或語氣的不同,出現細微差別,但相差無幾。就算是有差別,也不會影響到故事所想表達的本意,以及它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功能。
民間文學是傳播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巴拉根倉的故事》不僅是蒙古族古老生存方式的歷史寫照,同時又是蒙古族民間文化的生動敘述。筆者認為,民間故事不會因為被不同文化的熏染而發生本質的變化,而是會更容易被當地人所了解、接受。《巴拉根倉的故事》也是如此,它是被不同的文化所影響的結果。
[1][俄]弗·雅·普羅普,賈放.故事形態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圖日根白乙拉主編.蒙古民間故事—巴拉根倉[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
[3]芒·牧林編譯.巴拉根倉的故事[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3.
[4]斗改.淺談藏傳佛教寺院的組織機構及其社會功能——以青海塔爾寺為例[J].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2008,17(4):21-24.
[5]王志清.巴拉根倉故事的民俗功能解析[J].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9(3):48-49.
[6]芒·牧林.《巴拉根倉的故事》淵源、發展及其時代初探[J].民族文學研究,1985(1):108-120.
[7]王志清.從日常生活視角談阜新地區巴拉根倉故事中的婚姻情結——兼論民間文學的生活屬性[J].民族文化論壇,2010(2).
[8]納日蘇.論《巴拉根倉的故事》的思想內容[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2):61-67,19.
I207.9
A
雪蓮(1996-),蒙古族,內蒙古阿拉善右旗人,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研究方向:民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