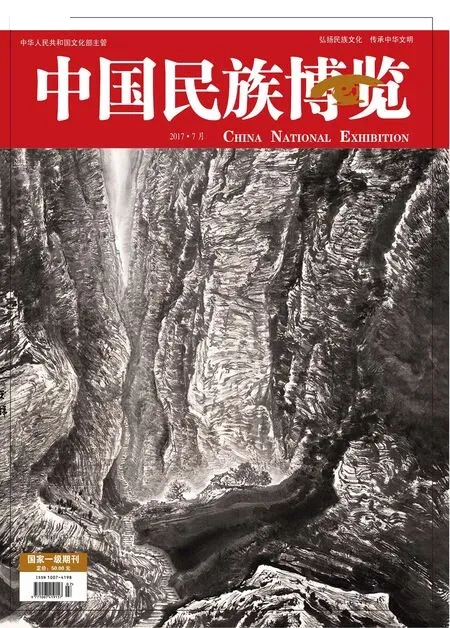從“真”的角度比較中西藝術差異
玄穎雙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1400)
從“真”的角度比較中西藝術差異
玄穎雙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1400)
藝術需要“真”,唯有真情實景,才能引入;唯有真情實感,才能動人。在對“真”進行探索的長途跋涉中,中西方繪畫開始時是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只是腳步邁開后就分道揚鑣了。西方人十分理智地分析解剖每一個局部,“真”在西方畫史即是重比例、重空間、幾何透視等與事物外在形態逼真的寫實內涵。而中國人極富感情地去體會那“天人合一”的境界,“真”是人生的體驗,是生命與自然融合的一種方式,是對宇宙本體精神的感悟,又是自我靈性的抒發。
繪畫;圖真;逼真
長期以來,藝術理論界有一種傾向,認為西方繪畫重“真”和“美”的統一,中國繪畫則重“美”和“善”的統一。誠然,中國的儒家學派確實特別強調“美”和“善”的統一,以致中國美術對一切自然客體大都不以“真實”為創作目標。但能不能根據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中國古典繪畫理念是側重“美”和“善”的統一而忽略“真”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拿先秦來說,老子和莊子都曾強調“真”。如《莊子》中明確地提出了“貴真”的理論:“真者,精誠所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漢代王充在《論衡》中提出:“疾虛妄,求實誠”,即在先秦思想上綜合強調“美”“真”“善”的統一。可見,東西方藝術在表現方法上雖然千差萬別,但思想和感情則可以相互交流和溝通。那么,中國古代繪畫強調的“真”與西方古典繪畫的“真”有什么差異呢?本文試從中西方繪畫對于“真”的不同釋義展開論述。
中國美術特殊的發展道路,使得繪畫造型更多重視的是形象與造型所要表達的觀念,以及繪畫技能所需要的形象準則,因為繪畫造型需要的是標識性作用與 “寸鑒戒”等功能,所以,才會有“古畫皆略”的面貌。繪畫的發展促進了藝術語言的獨立,藝術語言的獨立又增強了繪畫的狀物功能。真正優秀的藝術作品必須包含創作主體真摯的情感。于是,自古以社會道德規范作準則的“美”的審美標準在新的描繪手法與藝術法則面前,很難對藝術本身的評定做出判定,漸漸不能作為唯一的繪畫評定標準了。如此,作為物象本身的形色狀貌與氣態神韻,就成為審美標準的參照 ,“真”自然被作為審美標準提出來。一切得到認可的作品一定需要藝術家基于一種生命的本真從內心里真真實實地創造出來。
一般說來,“真”作為我國古代藝術中的一個重要審美內涵最先體現在唐代。唐人致力于對筆法與墨法的探索,使繪畫從“觀念”與“樣范”中擺脫出來,“尚真”就成了唐人審視社會生活的藝術方式。盛唐匯成的精神氣質為以后的文人或畫家提供智慧表達的延伸和良性變異。等到五代時期,山水畫家荊浩受唐人影響寫出了《筆法記》曰:“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圖真,不可及也。”此句可視為《筆法記》的綱領,他的“畫者,畫也”,就是“真”,就是真實的傳達對象,就是“如萬物其自身存在”,如其真,如其性。只有把“真”放在首要位置,藝術的內在價值才能得以體現。荊浩說“圖真”的基本方法首先是度量物象,這種態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寫實主義的基本方法與立場。可是,他很快就說“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這樣就澄清了“真”不是“似”,“似”就是孤立的描繪客觀物象的外形,而“真”則要求進一步表現自然山水的本體和生命——“氣”。畫家所畫對象是否具有“氣”或者“氣質”就決定了是否屬于“真”,這是獲得“真”的決定性因素。荊浩巧妙地用“真”這個范疇把審美意象和“氣”聯系起來,“真”就是用“氣”來規定審美意象,繪畫藝術的本質和目標就是“圖真”,即創造一個表現自然山水的本體和生命(“氣”)的審美意象。除此之外,荊浩還強調“真”的氣韻,沒有氣韻,畫就沒有生命,即“類同死物”,而這就是“不真”。山水畫的意象達到了“真”的要求,就達到了荊浩稱之的“景”。所謂“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這里特別注意的是“創真”二字,它表明“真”,不是被動的反映,不是照抄某一孤立對象,而是一種能動的表現。當“圖真”的動機得到了盡可能滿足后,畫面就會產生特殊的氣象。
可見,“真”是在把握自然山水的本體和生命的基礎上的一種創造,是畫家創造出來一種“自然”。我們可以總結出在中國古代繪畫美學中,“自然”“真”“氣”這三個范疇是緊密聯系的,而不單純的是只求事物的真實的外形特征,卻是尋求更能體現宇宙的精神內涵。正如美學家宗白華所說:“中國藝術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相互交融,成就一個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
與此相對應的,西方的繪畫藝術在表現原則方面,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影響實在很深重。在《詩學》的第一章里,亞里士多德提到模仿說代,基本上是一種求真寫實的藝術理論,他有力地促進了古代希臘“逼真”藝術的發展。此后,此理論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西方繪畫界。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為反對基督教神學而提出了“返回希臘,”重新復興長期被湮沒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模仿理論的影響下,文藝復興的繪畫大師們基本上是持“以真為美”的態度作畫的,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師法自然”。為了做到對藝術的“逼真”模仿,他們在藝術實踐中運用了歐洲當時先進的數學、比例學、透視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的成果,嚴格地按照科學理論,對物體從比例、透視、解剖乃至線條和色彩的運用,都要求盡可能地符合客觀現實,服務于求真寫實的目標。這種以描摹對象、逼真寫實為基礎的繪畫很快便形成了歐洲畫壇的主流,科學的造型理論和古希臘理想美最終融為一體。
到19世紀上半葉,這種以追求形體的“正確”為唯一目標的素描,在古典主義和寫實主義繪畫中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像安格爾這樣的古典主義大師,即使他其他方面的技能有所不及,但憑借著深厚的素描功底,以絕對的視覺對象作為真實的本質而呈現。在雕塑方面,大師羅丹認為:“美只有一種,即宣示真實的美”,所以說美的本質就是“真”。后來的印象派,旨在表現大自然呈現的光色變化而追求視覺的真實感,其實還是模仿理論精神的繼續。20世紀之后,出現了現代的抽象派藝術,在一片抽象藝術的大軸中仍有鐵桿寫實派夾于其間。即使如馬蒂斯這樣的野獸畫家也崇尚“真實”,他說:“畫家必須具有那種精神上的單純樸素,使他傾向于相信并只是畫他所看見的東西。那些存心想制造風格,自愿離開自然的人是錯過了真理,再到后來西方寫實繪畫更是給人似照相般的真實與震驚,西方藝術家像孜孜不倦的繡花工一樣為我們展現有別于中國繪畫的審美享受。應該說此時的“求真”主義傾向并非僅僅意味著一種寫實的手法,同時更強調一種面對現實的態度和想法。
西方人虔誠地遵循著科學對藝術的指導法則,故“真”在西方繪畫中與科學相聯系即回歸到它的本意——模仿自然,逼真寫實。中國則沿著一種“允執其中”的方向發展,基本上與自然保持著相對距離的平行事態,其轉折表現為相對模糊的蛻變,所以中國畫是對于哲理的探索。從宗白華寫的中西方透視法差異中也可以看出兩方對“真”的不同理解,他認為,“西洋透視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寫實’的空間構造,如鏡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則其真愈幻。而中國畫的透視法是提神太虛,從世外鳥瞰的立場觀照全整的律動的大自然。”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為在對“真”進行探索的長途跋涉中,中西方開始時是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只是由于民族間不同的發展狀況使得后來民族審美趨向就分道揚鑣了。 “真”在西方畫史即是重比例重空間幾何透視等與事物外在形態逼真的寫實內涵。 “真”對于中國人是人生的體驗,是生命與自然融合的一種方式,是對宇宙本體精神的感悟,又是自我性靈的抒發。但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東西方藝術創作實踐不同,然而兩方的經典藝術作品之所以流傳久遠,首先就是因為表現了生活中的“真”,背離生活真實的作品是不會得到肯定性審美判斷的。
藝術需要“真”,唯有真情實景,才能引入;唯有真情實感,才能動人。離開了“真”也就失去了“美”。對不同民族的藝術創造應采取尊重的態度,以寬廣的胸懷汲取、吸納世界的、民族的、時代的藝術成果,從不同的方面補充、啟發、繁榮本族的藝術語言、形式和思想。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葉朗.中國美術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金維諾.中國繪畫斷代史——唐代繪畫[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4]遲軻.西方美術史話[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5]丁寧.西方美術史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6]孔新苗,張萍.中西美術比較[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7]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J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