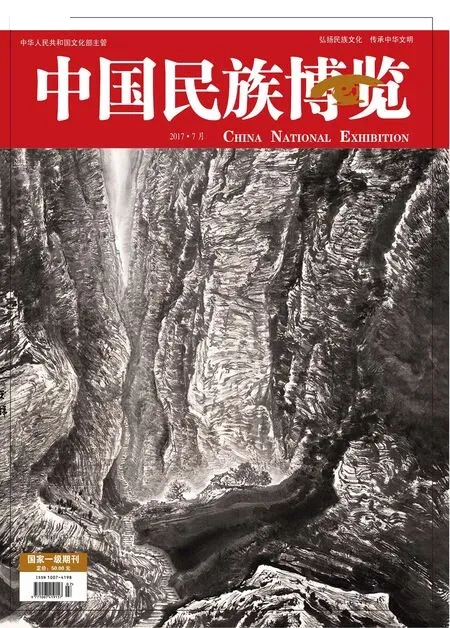淺析晁錯《論貴粟疏》主要經濟思想
——兼談對軍功階層的沖擊
張霖坤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淺析晁錯《論貴粟疏》主要經濟思想
——兼談對軍功階層的沖擊
張霖坤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論貴粟疏》作為西漢早期著名的一篇政論文,其經濟思想可謂是儒法并包,苛緩有度。適應了黃老思想為主導下既休養生息,又富國強兵的雙重現實需求。它的實施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軍功階層對權力的壟斷,緩和了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矛盾,并形成了人們追逐財富的社會風氣。但對于這篇名文后世學者評判不一。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沒有專門單獨為其立章節,而僅僅是在《法家思想之余波》中簡要提及,并以“無創新之見”做出了結論。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有《晃錯的尚法與重農戰思想》一節,對晁錯的經濟思想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說明。本文將根據《論貴粟疏》中的闡述,聯系漢初思想界的發展變化狀況,結合晁錯本人的經歷,對晁錯的經濟思想以及對軍工階層的沖擊加以分析。
論貴粟疏;經濟;法家;晁錯;軍功階層
一、“勸農”是晁錯《論貴粟疏》經濟思想的核心
從《論貴粟疏》中我們不難發現,晁錯的核心主要是圍繞著“勸農、歸農”這個核心。其開篇就論述道:“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勸農、歸農,這是針對當時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斂財物,致使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的社會矛盾和匈奴屢屢違背和親之約,多次侵擾,邊境不寧而發出的聲音。因此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認為最重要的是務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而所提到的舉措,都是為了應對當時民眾主要矛盾和日趨緊張的邊患問題,以求做到讓人們回歸農業、安心生產,“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同時,《論貴粟疏》也有比較明顯的法家“重農抑商思想”。他寫道:“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這有著朝代更替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實際的。
第一、漢初出于安定人心、穩固新政權統治的需要,“過秦”已經成為了當時的社會需求和風尚。從政治架構來說,漢朝時繼承了秦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核心的制度。相應地在對待商業的政策上也有一定的延續性,比如主要是政治上實行賤商,禁止商賈子弟做官,不準商人衣絲乘車等。當然劉邦時代對商人的限制更多還是從當時嚴峻的社會現實出發,《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而當時的富商大賈卻囤積居奇操控物價,以至于一石米一萬錢,一匹馬一百金,物價的飛漲與民生的凋敝使得當時的劉邦認識到商人的出現是不利于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的。因此,劉邦對于商人所采取的態度與政策既是秦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一種自然延續,又是處于解決現實弊病而采取的解決方案。
第二、漢初雖然采用的無為而治,但無為而治并不能不為不治,實際上,在經歷反秦爭斗與楚漢相爭這一所謂的“后戰國時代”后,原本禁錮的思想界已經逐漸開始趨于松弛,漢惠帝四年(前191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后,開放寬容的政策促進思想繁榮,于是儒、道、法諸家競起。陸賈兼取百家、賈誼儒荀并用、晁錯以儒入法,都說明了黃老思想并沒有在此時一家獨大。而無為思想也縱容諸侯驕橫不法,聽任豪強地主兼并不軌,忍受匈奴人不時入寇。面對著當時已經存在的社會危機,要求統治者必須有所作為,只是這種有所作為是在盡量不傷害或者少傷害平民利益的條件下進行的。漢朝皇帝沿襲秦法,大肆削弱功臣的權力,壓制同姓諸侯王勢力,加強統治,大有法家一手遮天的氣氛。
二、晁錯的經濟思想與之前法家經濟思想的區別
第一、最大的不同在于融合了儒家思想。與法家單純的以國家本位,剝削農民壓制商業以保證財政收入與軍隊開銷相比,很明顯要更側重保障人民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引進了儒家“倉凜實而知禮節” 的“仁義”思想,便有儒家先富而后教的意思;
第二、晁錯同時開始將土地兼并問題與商人發財致富聯系起來,尋找農商之間的規律和關系,認為正是由于商人的富裕,占有了農民的資源,使商人有了兼并農民的資本,使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具有儒家的“仁政”色彩;
第三、更為可貴的是晁錯并沒有刻意建議去壓制商人,相反面對商人已富貴、農夫已貧賤的社會現實,晁錯也明白商人之富裕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國家富裕的表現,畢竟如果沒有農業的發展與進步、糧食產量的增長,糧價不可能會降低,如果沒有糧價的下降又何談商人以低價收購糧食?商人手頭上所掌握的巨額財富也是國家鞏固邊防、飼養馬匹抵御匈奴所需要的錢財。
因此面對商人財富與地位不成正比的社會現實,晁錯讓商業資本和農業生產直接掛鉤。商人用部分資金買糧、人粟邊郡,將流通領域中積累的資本投入到簡單再生產過程之中。這種以疏代堵的獨創方案,能夠充分利用商人對社會地位的追求,并將其轉化為對糧食的有效需求,從而實現農民與政府收人均得以提高、商人社會作用明顯的三贏局面。
綜上來看,晁錯的《論貴粟疏》目的是要針對當時存在的階級矛盾激化與日益嚴重的邊境問題所提出來的。其所反映的經濟理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法家,不可避免地帶有法家固有的急功近利、國家本位與農戰思想。晁錯本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標無疑是大一統的強盛國家,這不僅表現在《論貴粟疏》中,也表現在他的《削藩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等著作中。只是由于晁錯本人儒法兼備的從政理念,更有文帝時期趨于恢復的生產力與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漢初“過秦”思想的沖擊,使得晁錯能更多地兼顧到商人和小農的物質利益,表現出對人民明顯的同情心和“人情”味。“晁錯講法制、賞罰與法家有根本區別。法家講法制,是為‘尊主制民’,晁錯講法制,是為‘尊主安民’;法家講賞罰,是為駕馭臣民,晁錯講賞罰,是為勸民忠孝”。
晁錯經濟思想,終究還是反映了當時國家開始動用封建政權的力量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希求社會經濟逐步按照他們所期望的運轉而不脫軌。因此,該思想也可以說是代表統治階級在經濟領域從“無為”到“有為”的轉化。
三、入粟拜爵對軍功階層的沖擊
《論貴粟疏》的意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入粟拜爵對軍功階層的沖擊,在此本文結合秦漢以來軍功爵制度的演變過程、漢朝軍功階層在入粟拜爵之前之后的狀況等方面進行簡要探討。
(一)軍功爵制度的起源和形成
第一、軍功爵制度,嚴格意義上講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悝在魏國的變法。西漢劉向《說苑》中記載“食有勞而祿無功”。就已經表明封賞的標準是功勞而并非血緣,這是對宗法分封制下的世卿世祿制度的否定,已經可以說是具有軍功爵制度的雛形。而軍功爵制度推行最徹底的是秦國,這與秦國本身地處西戎征戰頗多的軍事傳統有關,更與商鞅變法在秦國的徹底性密不可分。商鞅出于幫助秦國富國強兵的目的,定下了二十等爵位,由此確立了以軍功積功受爵的制度。
第二、軍功爵制度形成軍功階層是在漢朝建立后,劉邦大致在高帝六年借韓信申軍法的機會棄楚爵用秦爵利用軍功爵,順利地接收了秦朝政權,這是他第一次對軍功爵所進行的變革,使軍功爵由原先的激勵軍功,轉變成安撫秦民的歸降手段。據《漢書·高帝紀》記載,劉邦曾在西漢初年和高帝十二年兩次就軍功進爵下詔,其中高帝十二年的詔書內容為:“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士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詔書表明,天下乃是劉邦與劉邦集團的所有成員共同打下來,共同所有的,當然應該共同公平地分配。這就是所謂的“共天下”理念。而這種共有天下的理念即表明了軍功階層已經是一個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享有諸多權益的特殊階層。劉邦在去世前與眾臣立下的白馬盟誓更是通過“非有功者不得封侯”,將積功受爵這一制度正式確立下來。
第三、總體上看,軍功階層由于總體出身卑微,飽受民間疾苦,知道民間力量反抗的強大性,因此出于維護穩定的需要,他們在參與政事時能夠比較好地貫徹無為而治的思想并保證其延續性,比較關注百姓生活,注重休養生息。惠帝、文帝、景帝推行的輕徭薄役政策,也是少不了軍功集團成員參與。西漢初年,在新的選官制度沒有完全確立起來前,軍功集團中的優秀人才由于經歷了戰爭的鍛煉,很快就能夠勝任繁雜的國家事務,充實了官僚隊伍,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尤其是在平定諸呂之亂擁立漢文帝并限制劉姓諸侯王的勢力時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軍功階層帶來的弊端
到了漢文帝時期,軍功階層成為瓜分中央財源的一大勢力。“列侯,關內侯及諸侯王女皆能食邑”。漢文帝即位后,爵位已經不能再往上封,因此只能增加食邑。而隨著食邑的增多,中央財政就相應地受到損失,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財政收入雖有所增加,但很大一部分都被諸侯王還有功臣集團所獲得。有學者統計,單食邑城內之稅,中央每年便需減少高達七百零八萬的稅收。而很多軍功地主依仗權勢與財富兼并土地,發展成為一方豪強地主,成為了新的剝削階層。《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杰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可見作為地方豪強的灌夫已經從之前戰功赫赫的軍人變成一個危害一方的人物。而這種現象在當時并不是個案,因此,居功自傲的軍功集團,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然成了皇權的威脅,造成了民怨,導致了社會的不穩定。
(三)入粟拜爵對軍功階層的沖擊
軍功階層對土地的兼并、對財富的掠奪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作為封建統治者的漢文帝,面對著諸侯王與軍功階層兩大勢力的日漸壯大對本來就有限的皇權的沖擊,面對長期以來軍功階層對爵位與官職壟斷造成的階層固化問題,必須在“有為”的思想指導下進行改革。
《論貴粟疏》道:“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這就是晁錯所提倡的入粟拜爵。這個建議的推行,無疑將以前由軍功階層集團所主要把持的爵位面向更廣大的群體,使富商用金錢便可換取第九等至第十八等的高爵。這項政策不僅促使地位低賤的商人,有可能迅速轉成尊榮身份,原先保持尊寵的軍功受益集團,也因社會上突然暴增一群財富充盈高爵者與其平起平坐,而使其原有的尊貴地位急劇滑落。爵位的受封標準不再單純地以軍功為標準而轉為軍功——財富雙重標準;軍功階層不再是獨尊受寵的特殊階層。這種措施既讓富商大賈出錢暫時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也讓軍功集團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而漢文帝和晁錯將商業資本轉化發展生產與投身政治的雙重途徑,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其所希望的“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的目標。
四、總結
通過晁錯提出“拜爵入粟”的前因后果以及最后產生的諸多影響,我們可以發現,整個文景時期的經濟脈絡,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由“自由放任”到“國家干預”過渡、由三分天下之財(漢朝政府、軍功階層以及同姓諸侯王)到盡歸漢朝政府的特點。文景時期的社會發展趨勢,也是從“無為”出發,用“無為”中的“有為”來合理地分配國家財富、合理地切分蛋糕來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政府對經濟掌控能力的增強,從而結束了漢初皇權有限的局面,由共治天下轉為皇帝獨治天下,并最終實現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這也是漢承秦制,承秦之封建制所必然要經歷的過程與必然會達到的結果。在皇權專制主義的排他性逐漸強化的過程中,原有的特權階層軍功集團的消亡也是必然的。而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的狀態下,要維持一個幅員廣闊國家的安全和穩定,沒有這樣相配套的政治和經濟措施,也是難以延續長久的。
[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胡克森.“重農抑商”:一個儒法相融的歷史案例以戰國秦漢作為分析模板[J].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3]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M].北京:三聯書店,1980.
[5]嚴可均.商君書[M].長沙:岳麓書社,1996.
[6]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M].北京:三聯書店,1980.
[7]周美華.晃錯“納粟授爵”與漢文帝軍功爵制度改革[J].歷史文獻研究,2013(32).
[8]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階層受益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2000.
[9]司馬遷.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10]古永繼.“文景之治”非“黃老無為之治”——文景政策與思想剖析[J].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2).
[11]班固.漢書高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2]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K232
A
張霖坤(1995-),男,漢,陜西西安,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4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