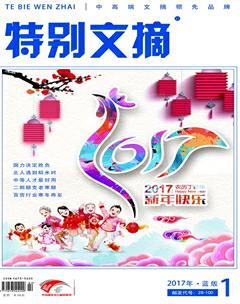工作真相
如果你工作日去公園、咖啡館逛逛,就會發現,很多人的生活并不像傳說的那么蹙迫。同樣在北上廣深,有人很忙,有人很閑。這種差別,選擇起了很大作用。我有個同門,上學時考各種證:證券從業資格、期貨從業資格、注冊會計師、特許金融分析師……后來果然,干了審計,每天十點后才下班。
以為人生的壓力來自工作,這是很大的誤解。毋寧說壓力來自稟賦、三觀和所處環境的沖突。稟賦是不易改變的,三觀是稟賦和環境共同塑造的,環境的改變則相對容易。雖然移民這種大環境的改變挺難,但搬家、改行,以及選擇交往對象這些小環境的調整則不難。一個人在毫無存款的情況下,突然選擇去擁有一套房子,并根據房貸確定每個月的任務量,然后覺得壓力是工作給的,這就糊涂了。
人并不是在逼迫下才可以激發出動力。用智和用力是不同的。用智的工作,壓力逼迫只會令結果更糟糕。人的很多煩惱源自不肯承認自己的平庸,以為有壓力就有動力,在壓力的逼迫下就可以達到期望值。既然期望沒達到,他就以為是逼迫不夠,工作中90%的壓力都是這樣產生的。實際上,給一匹馬再大的壓力也跑不過高鐵。
“認識到自己的平庸”和平庸是兩碼事。前者甚至是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師”,看到別人的長處,其實就是認識自己的平庸。它和“認識自己的天分”也不矛盾。任何人總是兼有所短和所長。當一個人肯正視自身所短的時候,就不會傻呵呵地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逼迫自己,轉而會尋求可能的路徑和調整相應的期望。
總拿夢想刺激自己的人,很可能缺乏自知。夢想和欲望之間的界限過于黯淡,必須經由對自身和萬物的理解才能辨明。夢想是塊遮羞布。很多羞于啟齒的東西,拿夢想裝扮一下再示人就體面多了,但不自欺很難。清醒的人應如是思量:“我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并沒有過人之處,我從事的工作也談不上崇高。哪天我死了,地鐵依然會按時發車,大街上依舊人來人往。我的勞作,對世界沒有重大意義,我重視它,只是為了讓自己保持熱情。”
若不如此提醒,人就會漸漸把自己看得很重,越來越認為自己的工作無比重要。但在別人眼里,你的工作可能只是鬧著玩。我畢業那年,有家煙草局去學校招人,年薪20萬元,招會打籃球、唱歌、演講的。他們并不需要你懂經營管理,只需要你在爬山比賽、足球籃球賽和各種晚會上拿獎。從事那種工作的人,和做資產定價的人,對工作的理解怎么可能一致呢。
正事有時候不是正事。鬧著玩有時候是很大的正事。領導腦子一熱,有個想法,大家轟轟烈烈干了半年,累得吭哧吭哧,發現賺不到錢,就撤了。正事就變成了鬧著玩。平時鬧著玩,偶然賺了錢,領導說這個好,應該認真做,就變成了正事。
用錢去衡量工作的意義,就很容易陷入這種循環。思考力欠缺的人,除了掙錢多少,很難再想出別的尺度評價工作的意義。在庸俗的思路下,只要賺錢,狗屁都是戰略;只要不賺錢,戰略都是狗屁。
錢穆在談到魏晉南北朝的僧侶時,說他們屬于貴族階級。理由是他們吃供養,不工作。吃供養的僧人,哪怕吃得再差,也要當貴族看。這個想法很有見地,它隱含的前提是:人,而不是錢,是萬物的尺度。
收入對工作來講,是十分次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意義,是安排人一生的時間,就像選擇枕頭中的填充物。人通過工作,選擇自己一生有多少光陰在何等環境下以何事為內容來度過,如同打游戲要設定角色和規則,工作設定了常人生命中2/3以上的時間。如果缺乏必要的設定,生活將陷入巨大的混亂。
想象一下小孩為什么需要上輔導班,就能明白大人為什么需要工作。我小時候,根本沒聽說過輔導班。今天上輔導班成了天經地義的事。輔導班的真正意義是什么呢?是安頓好小孩的時間,把大人解放出來。
成人工作的意義與此類似。大蕭條時,政府往往找兩撥人,一撥蓋樓,一撥拆樓,失業率就降低了,避免了社會動蕩。如果不拿工作來限制住盛年人的雄心,不拿挫敗來磨平他的棱角,他無處發泄的血氣就勢必轉移到別的事情上。
常人缺乏自律。一旦可以自由選擇,他一定會把自己引向很糟糕的地方。因此,必須有外在的約束來限制他,才能令社會有序。哪怕早起給一個人帶來很大痛苦,但一想到生活和房貸沒有著落,他就會在第三次鬧鐘響起時努力鉆出被窩。
每月到手的收入只是假象,它遠非工作的根本意義。收入并不值得人將生命傾注其上。到底什么是正事,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沒辦法想清楚。但不要緊,無論能否想清楚,任何工作都有助于將生活導入有序。
一個上班族在綠燈亮起的剎那,搶先沖過馬路只為擠上早一班地鐵的時候,他作為活生生的人的能動性就發揮出來了。在地鐵上覷準要下車的人并搶到座位是十分有成就感的。并不是他的肉體渴望坐五分鐘,而是他的精神渴望適時投入戰斗,然后才能對自身存在的意義有所肯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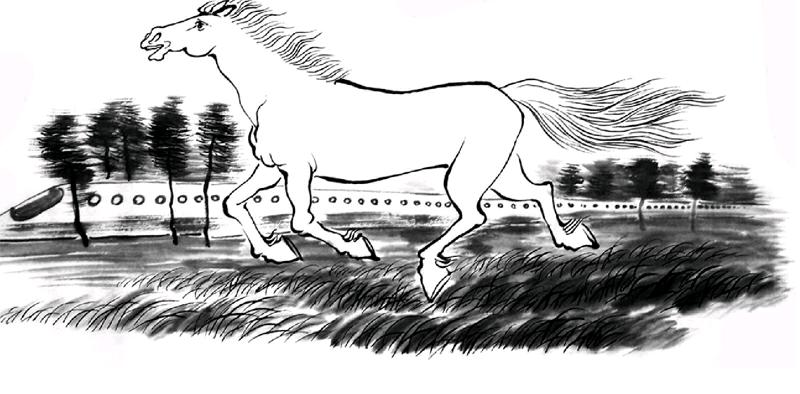
(摘自“王路在隱身微信公眾號” 圖/張文發)
本欄編輯:憨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