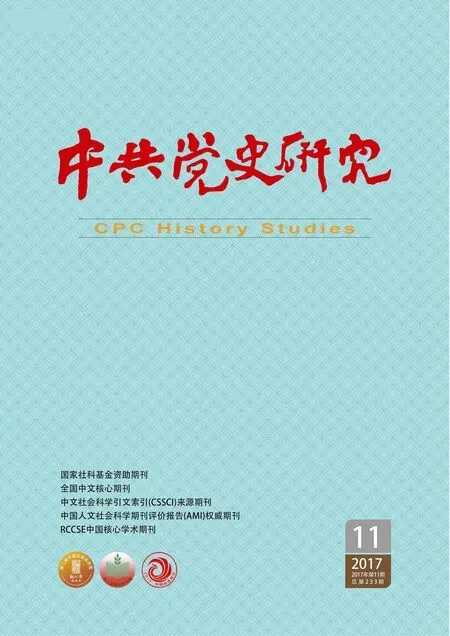中共黨史研究的概念譜系芻議*
李 里 峰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 南京 210023)
·“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筆談·
〔編者按〕進入新世紀以來,概念史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不僅在整個歷史學界得到較為普遍的推廣與運用,而且得到諸多黨史研究者的重視與實踐,有力地推動了黨史研究的學術進步。但概念史的研究范式與中共黨史研究的結合還缺乏較為充分的理論建構,需要黨史學界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探討。鑒于此,我刊擬開設“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筆談欄目,約請相關專家學者從理論概述和實踐路徑等多方面指導概念史研究與黨史研究的有機融合,以更好地推進概念史研究理念的學術實踐,有效地擴展黨史研究的視野和領域。本期先推出幾位學者的筆談文章,以饗讀者。
中共黨史研究的概念譜系芻議*
李 里 峰
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概念提示著歷史的進程。對基本概念進行正本清源,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前提,但這項工作在中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領域才剛剛起步。近十余年來,一批中國學者開始關注西方學界的概念史研究傳統,并嘗試對中國現代政治與社會基本概念進行系統梳理,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福建論壇》2012年第5期。。筆者在黨史、革命史領域研究有年,近來亦涉足與革命相關的概念史研究,深感這一學術工具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義,故撰此文簡要介紹其淵源和特色,并以若干論著為例,就如何進行中共黨史基本概念研究略陳淺見。
概念史是一種發端于德國、盛行于歐美學界的研究手法,其旨趣常被概括為“歷史語義學”,即用歷史的眼光去考察重要概念的形成、演變、運用及其社會文化影響*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于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思考》,馮天瑜等主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頁。。1955年,德國學者羅特哈科爾(Eric Rothacker)創辦學術年刊《概念史叢刊》,通常被視為概念史研究出現的標志。從20世紀70年代起,三部大型辭書陸續編纂出版,為概念史研究帶來了世界性的學術影響,即八卷本《歷史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辭典》(1972—1997)、十三卷本《哲學歷史辭典》(1971—2001)和十五卷本《法國的政治—社會基本概念手冊》(1985—2000)*關于三部辭書內容與特色的簡單介紹,可參見〔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9頁。。
概念史的興起和蓬勃發展,無疑和20世紀中期西方學界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密不可分。受弗雷格(Friedrich Frege)、羅素(Bertrand Russell)、奧斯汀(John Austin)等分析哲學家的影響,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語言并不是“透明的”,人們對事物的描摹、對歷史的敘述并非忠實和完整的“如實”復制,而是一種“再現”或“表象”(representation)。以語言為中介呈現出來的“真實”已不是客觀存在本身,而是人們對自認為客觀真實的主觀表達。這對先前主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主義”話語形成了巨大挑戰,研究者開始更多地關注人們對世界、對歷史的認知和再現,而不再孜孜于追尋“絕對真實”。經過此番“典范轉移”,對語言、概念、話語、修辭的探究便很自然地繞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傳統領域,成為西方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潮流。
研究概念的起源和流變并不是德國學者的專利。同樣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西方學界還發展出不同的研究路徑和學術流派。在英國,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關鍵詞研究”,旨在梳理英文中“文化與社會”關鍵詞的意義轉變、復雜性與不同用法及其創新、延伸、重復、轉移等過程*〔英〕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有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為代表的“劍橋學派”,聚焦于政治語言、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之間復雜的交互作用,尤其注重“對概念在其中發揮功能的語義場進行共時性的探討”*劍橋學派概念史研究之旨趣和特點,可參見〔英〕蒙克:《言語行動,語言或“概念史”》,〔英〕蒙克主編,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2—71頁。。法國則有為學界所熟知的“話語分析”流派,強調知識生產與權力操控之間的密切關聯,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概念無處不在,概念史家關注的則是歷史進程中的所謂“基本概念”,即對特定區域、特定時期的政治與社會變遷產生重要而持續影響的關鍵性概念。在德國概念史領軍人物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來,可以從四個標準來判斷一個概念算不算得上“基本概念”,即時間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些標準又分別對應著特定的方法論訴求。所謂“時間化”是指這些概念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變化,因此需要細致梳理概念生成與變遷的歷史脈絡;所謂“民主化”是指概念的社會邊界日漸拓展,最終成為社會各階層耳熟能詳、日常使用而不自覺的概念,因此需要拓寬研究視野、擴展資料范圍;所謂“政治化”是指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長,對塑造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探討概念形成和傳播的政治后果;所謂“意識形態化”是指概念日益成為權力支配體系的工具和要件,因此需要揭示概念/話語背后的權力操控和角逐。*〔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29—80頁。按照上述標準,《歷史的基本概念》共收錄115個(組)基本概念,系統考察其形成、演變、傳播及影響,從而清晰地勾勒出德國乃至歐洲現代概念體系經由1750年至1850年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而逐漸奠立的過程,為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參照*《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詞條目錄,可參見〔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243—249頁、“附錄1”;“鞍型期”概念及其方法論意義,可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第85—116頁。按照里克特的歸納,這些概念包括政治概念56條、社會概念45條、意識形態概念27條、哲學概念21條、歷史概念20條、經濟概念19條、法律概念15條、國際政治中的概念10條。參見〔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54—55頁。。
從概念史視角觀之,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領域雖已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與之相關的基本概念還遠未得到系統而深入的梳理,致使許多學者還在似是而非地使用各種概念,相關學術討論往往也因概念含混不清而難以深入。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細致的資料耙梳和意義闡釋構筑一個基本的概念譜系,或許對推進中共黨史研究不無裨益。
首先需要探究的當然是那些構成中共歷史底色的核心概念,它們在黨史文獻中隨處可見,對中共歷史進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革命”就是理解中共黨史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既是20世紀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主題,也是近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話語之一,“不僅意味著進步與秩序的徹底變革,還成為社會行動、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根據,甚至被賦予道德和終極關懷的含義”。然而,西文中revolution的原意是天體周期性運動或事物周而復始變更,中國古代典籍中的“革命”往往用作周期性王朝更替的代名詞,背后體現的仍是一種循環史觀。那么,近代中國為何要用“革命”來翻譯revolution,并用它來描述政治與社會的急劇變遷?中國和西方的革命觀念有何異同?中國革命觀念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中共革命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有何延續和差異?*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頁;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57—390頁。為理解中共革命的運行機制,又必須對“階級”概念進行深入探討。按照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將人群區分為不同階級,既是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前提,又是黨組織進行政治動員的有效工具。階級概念怎樣譯介到中國并流傳開來?唯物主義階級觀何以能在與其他思潮、流派的競爭中勝出?階級話語與民族話語之間有何互動關系?階級劃分如何取代傳統的血緣、地緣等人際分野,確立一種新型的政治等級秩序?此外,“國家”“民族”“政黨”“政權”等也都是政治制度及其變遷中的核心概念,中共領導人如何理解和表述這些概念、如何與其他政治勢力爭奪其闡釋權,顯然也是中共黨史研究不應忽視的問題。
許多概念帶有明確的價值判斷,標示著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和自我定位,指引著黨的行動方略和革命實踐,可以稱為價值性概念。1949年中共贏得革命勝利,新政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號,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這一簡單的歷史陳述就包含了若干個價值性概念。“中華民族”是20世紀初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逐漸發展的產物,其內涵從漢族逐漸擴大到其他各族人民,并隨著知識精英的倡導和討論而逐漸傳播,最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成為主導國內政治輿論的符號化概念*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人民”作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公意”(general will)概念的載體,在道德上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從而取代君主成為現代國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來源,然而其整體性、抽象性的特征又使人民主權在實踐中時常面臨困境*沈松僑:《六億神州盡舜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人民”論述,1895—1949》,未刊稿。。“民主”與“共和”是近代國人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實際上“民主”出自中文語境,“共和”出自日文語境,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相互滲透,二者起初是一種“類義關系”,后來才分道揚鑣,分別成為西文democracy和republic的對譯詞*陳力衛:《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響——以“民主”與“共和”為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第149—178頁。。然而,民主作為大眾參與、共和作為均衡政治的實質性差異,無論當時還是如今都很少有人真正弄明白。“平等”“自由”“解放”等也都屬于這樣的價值性概念。
一些作為革命對象或對立面的概念同樣值得深入探究,“封建”即其典型。傳統史籍所謂“封建”是指先秦時期的“封邦建國”,與秦漢以后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相對。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傳入中國后,“封建”就從政治制度轉變為一種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社會形態,毛澤東更將近代中國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遂成為專制、保守、反動等負面意涵的象征和革命要消滅的對象。*馮天瑜:《“封建”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革命”的對立面是“反革命”,這種二元對立是在20世紀20年代建構起來的,當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同時并起,在三大政黨、三種革命的黨際互動中,政治道路的不同選擇遂由“革命”與“改良”之爭演變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圣魔兩立,“反革命”也正式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成為一種令人恐懼的政治污名*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66—121頁。。
中共黨史中的基本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由若干個具有互文、類義、對比、分層等關系的概念共同構成一個“概念群”或“概念鏈”,只有從它們的相互關聯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每一個概念。例如,“人民”概念應該放在和“國民”“臣民”“群眾”相比較的視野中去考察,而“群眾”又和“先鋒隊”“干部”“群眾路線”等密切關聯。“群眾”同時承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勞苦大眾”、西方近代群眾心理學中的“烏合之眾”兩種相反相成的意涵,“先鋒隊”與“群眾”、“干部”與“群眾”、“基本群眾”與“普通群眾”構成了一個既層次分明又邊界模糊的等級體系,為黨在革命實踐中靈活劃分敵友、擴大社會基礎、塑造政治合法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叢日云:《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的“群眾”概念分析》,《政法論壇》2005年第2期;李里峰:《“群眾”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王奇生主編:《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第31—57頁。同樣,“階級”為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動員工具,與之相關的次級概念、三級概念當然也應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如區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依據和標準是什么?“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的定義和邊界何在?底層工農大眾怎樣才能從“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經營地主”等階級身份如何確立、如何演變?從階級話語推衍到革命實踐,“積極分子”“中間分子”“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同路人”等政治標簽意味著什么?這些概念都是為了確定個體和群體在革命中的身份與地位,可以稱為身份性概念。
在中共歷史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黨史學者不僅應該研究這些制度本身,也須關注與之相應的制度性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例如,“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它的思想淵源何在?黨的領導人和黨章在不同時期怎樣表述?民主與集中之關系經歷了何種變化過程?普通黨員和群眾對這一原則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同樣,“人民民主專政”“蘇維埃”“人民法庭”“三三制”“工作隊”“貧農團”“會議”“總結”“匯報”“巡視”“調查統計”等制度或機構,都可以既從制度/實踐又從概念/觀念這兩個不同的視角進行深入考察。
中共領導的革命實踐還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行動策略,深入探究這些策略性概念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功能,無疑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黨史的理解。例如,中共建黨伊始就設有兩個機構——組織部和宣傳部(最初僅有主任),其重要性一直延續至今。黨史學界對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當然有過大量研究,但大多聚焦于機構之沿革、職能之變化或工作重心之轉移,卻很少對“組織”和“宣傳”這兩個概念本身詳加分梳。要知道,中共是與傳統血緣、地緣、業緣團體以及現代西方政黨和利益集團都全然不同的一種新型組織,其特性絕不是不言自明的,革命領導者和參與者對組織的認知也并非毫無歧異和一成不變。“宣傳”(propaganda)一詞則已在西方語境中被污名化,黨為何以及如何使用這一概念同樣需要進行梳理。再如,筆者曾注意到“運動”作為一種動員方式和治理風格的重要性,指出群眾運動是中共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一種非常規政治手段,因其具有常規行政手段難以比擬的優越性,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仍被廣泛使用,基本特征就在于廣大民眾的動員型政治參與、國家力量對基層社會的直接介入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運動式治理”模式*李里峰:《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路線”“方針”“政策”也是這樣,黨史學者不僅要關注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也應該把這些概念本身納入研究視野。“代表”“動員”“作風”“統一戰線”“工農聯盟”“模范”“團結”“斗爭”“改造”“整黨”“整風”等等皆當如此對待。
更適合、更需要作概念史梳理的應該是形形色色的主義概念。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以-ism為后綴的詞匯,往往具有“……至上”的意思,即強調某一種價值或特性超越于其他價值、特性之上,它們構成了通常所說的“意識形態”。這些概念自然也負載了鮮明的價值判斷,和前述價值性概念具有相似性,但數量龐雜、種類繁多,不妨作為一種單獨的概念類型。*在1952年出版的一部學習辭典中,據筆者粗略估計,其所收錄的“主義”詞條至少在100個以上。參見陳北鷗編著:《人民學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2年。其中有些是作為正面價值存在的,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唯物主義”等,過去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研究較多,而對這些概念在整個中共歷史進程中的意義演化及內在張力的探討還遠遠不夠。更多的主義概念則是用來描述黨的對立面或需要克服的錯誤傾向,如作為革命對象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為思想偏差的“唯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個人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作為路線錯誤的“機會主義”“冒險主義”“投降主義”“關門主義”、作為作風問題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等,對這些概念之形成、變遷及影響的剖析,更是以往中共黨史研究所欠缺的內容。
在與黨史、革命史相關的大量概念中,一些看似無關宏旨、實則細致入微地彰顯了中共革命運行機制和獨特性的本土化概念(在其他歷史情境中未曾出現或沒有那么普遍和重要),尤其值得進行深入探究。例如,在研究華北土改運動時,學者們注意到“訴苦”這一獨特的動員和治理手段,指出這種被納入階級話語的特定訴說行為,有效地激發了廣大農民對國民黨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使之在不知不覺間投身于革命洪流。訴苦也有助于農民與國家關系的重構,是一種轉變人們思想觀念的治理技術和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李里峰:《土改中的訴苦: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同樣在土改研究中,又有學者對“翻身”“翻心”“生產”等概念進行“話語—歷史分析”,指出北方土改中“翻身”與“生產”的矛盾構成了中國革命現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態,并預示了未來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構性張力;“翻心”實踐則揭示了精神力量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堪稱共和國革命政治文化之濫觴*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與“生產”——中國革命現代性的一個話語—歷史矛盾溯考》,《中國鄉村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31—292頁;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以上所列都是中共黨史上直接使用過的概念。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黨史文獻中沒有或很少提到但對歷史解釋很有幫助的分析性概念,例如“象征”“記憶”“儀式”“認同”“情感”“傳播”“合法性”等等,也完全可以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有力工具。需要說明的是,上面所作的類型區分完全是為了研究的需要,不同類型的概念是很難截然分開的,上述制度性概念、策略性概念、本土化概念其實都是從中共革命實踐中提取出來的,制度往往具有策略意味,策略也可能凝結為一種制度。
用概念史方法來研究中共黨史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但真正付諸實施卻并非易事。以筆者從事黨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經驗來看,一項好的研究應該具備三種特質:歷史感、層次感和張力感。
所謂歷史感,是指把概念放到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去考察,而不能以今天的知識和眼光去理解歷史上的概念。中共黨史上的大多數概念至今仍在使用,“以今視古”是許多研究者難以抵制的誘惑。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概念史家,無論波考克、斯金納還是柯塞勒克,都一再強調必須時刻注意“歷史化”(historization)或“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重要性,不要犯“非歷史主義”或“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謬誤*〔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181—212頁。。若非“設身處地”地回到歷史現場和歷史語境,研究者的“后見之明”恰恰會遮蔽歷史真相。
所謂層次感,是指從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不同層次去探討特定概念或概念群,而不能停留于詞匯和語義變化的表層。一位學者認為,中國的概念史研究應該包含以下內容:“詞語的歷史;詞語被賦予了怎樣的政治、社會內涵并因此而變成概念的歷史;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詞語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現;文本得以生成的社會政治語境。”*孫江:《近代知識亟需“考古”——我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中華讀書報》2008年9月3日。筆者更愿意將概念史研究歸納為三個層次:作為“能指”(signifier)的概念,即用術語學或關鍵詞的方法去梳理詞匯(概念的載體)的淵源和演變;作為“所指”(signified)的概念,即用歷史語義學的方法去探討概念的意涵及其演化;作為“話語”(discourse)的概念,即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去剖析概念的使用情況和政治功能。
所謂張力感,是指時刻關注概念之名與實以及概念的不同使用者之間的緊張/沖突關系,而不能想當然地把文本呈現出來的面貌當作歷史事實。前面提到判斷“基本概念”的兩個標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正是要提醒人們關注概念背后的權力操控和競爭關系。施米特認為,“國家”“社會”“階級”“主權”等政治概念都是現代發明,最終目的不過是用來區分敵友,如果人們不了解某個詞是為了“打擊誰、輕慢誰或駁斥誰”,就無法真正理解這些概念。斯金納甚至聲稱:“不可能有概念的歷史,只有處于論戰中的概念使用的歷史。”*轉引自〔英〕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第198—201頁。中共黨史上的重要概念也都充滿了張力和斗爭,如果研究者不能將其揭示出來,得出的結論恐怕會過于簡單而難以令人信服。
當然,“史無定法”,以上所述僅為筆者的一家之言,未必確當更不可能完整,中共黨史研究者自然也不必全盤照搬概念史的理論和假設。但對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構筑一個中共黨史研究的概念譜系,顯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筆者期待更多學者加入這一行列,共襄斯舉。
* 本文得到江蘇省“333工程”(BRA2016352)和“六大人才高峰”(JY-029)專項資助。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