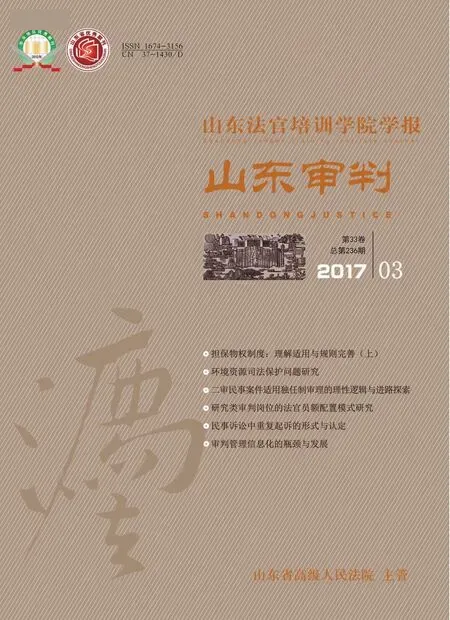證據分類確定路徑分析
——以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為例
●張志彥
證據分類確定路徑分析
——以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為例
●張志彥
確定證據種類和證據分類是證據法學習和實務中的基礎練習和基本技能。將訴訟證明限于審判階段的前提下,進行證據分類應以法官視角進行。堅持證據統一說前提,應按照以下路徑分為三步進行:明確證明對象、固定證據種類、確定證據分類。
訴訟證明 證據種類 證據分類 路徑分析
為了理清不同證據的特點和證明規律,證據法學除了依據法律上按照證據不同表現形式而將證據分為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鑒定意見、當事人陳述、被害人陳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現場筆錄、勘驗筆錄、辨認筆錄、偵查實驗筆錄等筆錄類證據外,還從理論上依據不同的標準對證據進行了類別劃分,較常見的的劃分有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實物證據和言詞證據、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本證和反證等。在證據法學學習和實踐中,經常會有人就某一特定證據屬于哪一種類和證據分類中的哪一類別產生疑惑、爭議。縱觀這些爭議內容,大部分人對每一證據種類的概念和不同證據分類的概念都是比較清楚的,其模糊或迷茫之處在于不清楚按照一個什么路徑或方法來對該特定證據進行分析,各種證據法教材或文獻中,也較少有人對此進行闡述。筆者認為,證據分類確定路徑可以分為以下三步:明確證明對象、固定證據種類、確定證據分類。
一、明確證明對象
訴訟證明作為一個概念,往往有多種說法。筆者傾向于把訴訟證明限定在審判階段,是指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向法庭論證其所主張的事實成立的活動,對方當事人有可能同時就該主張事實的真實性進行證偽活動,法官則作為裁判者,對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是否存在進行權威的驗證和裁斷。①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頁。訴訟證明包括了證明主體、證明對象、證明責任、證明標準、證明手段和證明方法以及證明過程等構成要素,構成要素中的證明手段,即為證據。證明構成要素中,證明對象是指訴訟中需要運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對整個訴訟證明起著統領的作用,為證明主體指明了證明的目標和方向。所以在確認某一特定證據屬于何種證據類別前,應明確以下內容,即某一特定材料②鑒于訴訟法中將證據的定義從“事實說”轉為了“材料說”,故我們把作為證據討論的特定所指范疇稱為特定材料。在被稱為證據時,一定是在某一特定訴訟證明過程中發生的,一定是相對于某一特定證明對象而言的。比如,我們講“沾有被害人鮮血的水果刀”是證據時,一定是針對某個證明過程而言的,通常是在證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實施了持刀傷人的犯罪行為時,所以完整說法應該是:“沾有被害人鮮血的水果刀”是證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行為的證據。又比如,我們講“商場為購買人開具的發票”是證據時,一定也是針對某個證明過程而言的,通常是在證明商場與購買人之間存在交易支付行為時,所以完整說法應該是:“商場為購買人開具的發票”是證明商場收取購買人款項的證據。如果脫離開特定證明過程,沒有特定證明對象的存在,某一特定材料是無所謂證據或非證據的。在某一訴訟證明中,相對于某一證明對象被判定為證據的某一特定材料,在其他訴訟證明中,對于其他證明對象,有可能是無任何證明意義的。所以在提到證據時,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到證明過程中考慮,一定要確定好證明對象是什么。從這個意義上說,證據是一個表征關系的范疇。
將訴訟證明限定在審判階段,也意味著我們在判定某一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種類和證據分類時,必須以庭審作為主背景,以法官視角進行判斷。由于特定證據材料在法庭上展現之前,需要有一個收集過程,收集過程中收集者會根據證據材料的不同特點采取不同的固定證據方法,固定后的證據表現形式可能與被固定證據的原表現形式不同,這將導致站在收集者的視角對證據材料的判斷和站在法庭的視角對證據材料的判斷發生偏差。由于法庭對于自身收集過程中公正性和可靠性的信任,所以對于法庭收集的證據材料,不論其表現形式有無變化,均依據被固定證據的原表現形式進行判斷,而對于當事人收集的證據材料,則應站在法官的視角,以庭審時特定證據材料表現形式的實際情況進行判斷。
二、固定證據種類
與證明的多意一樣,證據的概念也是有多個版本。本文采統一說的觀點,主張證據是由內容和形式共同構成的。證據的內容指證據材料所含有的與案件事實相關聯的信息,證據的形式指證據的種種表現形式,是證據內容得以展現的途徑和方式。訴訟證據可以定義為:在訴訟中具有法定形式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一切材料。③陳光中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頁。在固定證據種類前,應首先確定好證據內容和證據形式。
(一)參照證明對象,確定證據內容
明確了證明對象后,我們需要以證明對象作為參照,分析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內容,即該證據材料所含有的與證明對象相關聯的信息。在分析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內容時,應首先將證明對象具體化,即將證明對象分解為若干事實,④通常是根據實體法規定,先將證明對象限在了特定法律構成要件事實,再將要件事實依據生活經驗分解為若干具體事實。在“以銀行匯款記錄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借款關系時”,證明對象為“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借款關系”,根據傳統民法的規定,借款關系(借款合同關系)為實踐性合同關系,其成立應具備兩個要件,其一為雙方當事人就借款達成意思表示一致,其二為借出方將出借款項交付給借入方。故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借款關系”,就變成了證明前述兩個要件事實。其中,“意思表示一致”的要件事實,可以分解為雙方當事人曾以書面、口頭或行為方式表達了“一方愿意向另一方借錢,而另一方也愿意將錢借給這一方”意思的生活事實;而“借出方將出借款項交付給借入方”的要件事實,則可分解為借出方將款項直接交付或轉賬給借入方的生活事實。其次,完成證明對象的具體化后,我們利用知識來分析證據材料中與證明對象有關聯的信息。比如,銀行匯款記錄在用以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借款關系時,其作為證據包含了以下信息:一定款項從一方當事人賬戶轉至了另一方當事人賬戶,即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收取款項行為(有存在借款關系可能)。又比如,在某人家中發現的被盜物品在用以證明某人實施了盜竊行為時,其作為證據包含了以下信息:該物品與被盜物品具有能表征同一性的特定外部特征或內部屬性(指向該物品即為被盜物品);該物品在某人家中(指向該物品有被某人盜取回家的可能)。
(二)依據證據形式,固定證據種類
證據種類在證據法上是一個內涵確定的概念,指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證據的不同表現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八種證據: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民事訴訟法》第63條第一款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八種民事證據: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意見,勘驗筆錄。《行政訴訟法》第34條規定,行政訴訟證據有以下八種: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意見,勘驗筆錄、現場筆錄。這些規定中,所謂證據的表現形式,是指與證明對象相關聯的證據內容信息的存在方式,也是我們獲取證據內容信息的路徑方式。拋開筆錄類證據(刑事訴訟中的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民事訴訟中的勘驗筆錄,行政訴訟中的勘驗筆錄、現場筆錄)不論,物證的證據內容是以實物或痕跡的外部特征、存在狀態、物質屬性等方式存在和體現的,書證的證據內容是以書面文件或其他物品中的文字、圖形、符號等表達的思想或記載的內容形式存在和體現的,視聽資料的證據內容是以存儲在錄音磁帶、錄像帶和電影膠片中的模擬信號形式存在和體現的,電子數據的證據內容是以存儲在電子計算機、電子磁盤中的電子數據形式存在和體現的。前述四種證據中,物證證據內容主要憑感官感知獲取,書證證據內容主要憑大腦思維獲取,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證據內容須借助特定設備獲取。除前述四種證據外,剩下的證據種類主要包括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當事人陳述、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這些種類證據的證據內容都是在人腦中儲存并須借助外在表達方法形式存在和體現的案件信息,證據內容的獲取主要通過詢問回答獲取。這些證據種類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儲存信息和作出表達的人員主體身份的不同。
在特定證明過程中,我們在明確證明對象、確定證據內容后,便可以根據該特定證據內容的存在和獲取方式,固定下該特定證據的種類。比如針對“在某一犯罪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的身份證”這一證據材料,我們首先需明確該刑事證明的證明對象是“某一犯罪的實施人是張某某”,然后我們便應考慮“在某一犯罪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的身份證”包含的與證明對象有關聯的信息,這種信息應有兩個,第一為“身份證”上的文字內容所包含的信息(該信息指向張某某),第二為“身份證”的位置所包含的信息(該信息指向犯罪現場),在張某某正常情況下到不了犯罪現場和張某某身份證未曾丟失過的前提下,通過前述“身份證”包含的兩個信息,應可以得出“身份證”是張某某實施犯罪時遺留在犯罪現場的結論,即張某某是某一犯罪實施人的結論。確定了“身份證”前述證據內容后,分析證據內容的存在和獲取方式,便很容易得出“身份證”既是書證(第一個信息),也是物證(第二個信息)的結論。
三、確定證據分類
與證據種類相區別,證據分類在證據法中也有特定的含義,是指按照一定的分類標準將證據在理論上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其意義在于區分不同證據的特點和證明規律。所以要準確的進行證據分類,需把握住證據分類的標準和外延范圍。訴訟證明過程中,在確定了某一證據材料所屬的證據種類后,該證據的證據內容和證據形式即已明確,我們便可以根據證據分類的標準將該證據劃分到特定分類的某一類別中。
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分類標準,是證據的來源或出處。原始證據是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且未經復制或轉述的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第一手資料”;傳來證據是間接來源于案件事實,不是從第一來源直接獲取的,而是從第二手以上的來源獲取的證據,即從原始出處以外的來源獲得的證據。⑤前引③,第220頁。一般認為,區分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的來源的“案件事實”,即為證明對象的發生過程。一個特定的“案件事實”發生后,就象信源發出一定的信息,信息依附在一定的載體上,比如為人所感知而進入人腦并得到記憶,或在物上形成能反映案件內容的痕跡、文字等。如前所述,這些信息內容和信息形式的結合,即構成了相對于“案件事實”這一證明對象的證據。此時這些證據均為原始證據。隨著時間向前推移,原始證據的內容信息會因為各種原因在現實世界中傳播,傳播事實的發生,又會象信源發出一定的信息,信息依附在一定的載體上,就會形成包含原信息內容和傳播信息內容共同構成的信息內容與信息形式結合而成的新的證據。這些新的證據相對于“案件事實”這一證明對象而言,其包含原信息內容的信息形式即證據形式并非是“案件事實”發生過程中形成的,而是在傳播事實中形成的。所以說,這些新的證據,在以原信息內容作為證據內容證明“案件事實”時,其并非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而是間接來源于“案件事實”,屬于第二手資料,是傳來證據。但這些新的證據并非永遠是傳來證據,當證明對象不再是“案件事實”,而是傳播事實時,也就是說“當原始證據是否經歷了傳播過程”成為證明對象時,這些新的證據就成為了原始證據。
實務中,容易發生混淆的是證據傳播中的傳來形式和證據收集中的證據固定形式(證據保全中的證據保全形式)。如前所述,證據傳播中的傳來形式是案件事實發生后,隨著時間流逝和空間變化,現實生活自然而然向前發展而形成的,傳來證據中雖然包含了案件事實中的相關信息內容,但其作為證據整體——內容和形式的結合,則是后來的傳播事實中形成的。證據收集中的證據固定形式(證據保全中的證據保全形式)則不同,它是訴訟程序前或訴訟程序過程中,直接出于完成訴訟證明的目的,在某一證據材料被發現后,為了防止證據滅失或以后難以取得,而對證據內容和證據形式進行固定保全而形成的。證據固定形式可能改變了原證據的證據形式,但確定其證據種類時只能根據原證據的證據形式進行確定。
四、實例解析
在南京彭宇一案中,原告曾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證據材料,為一份公安人員對彭宇詢問筆錄的照片(下稱筆錄照片)。筆者試以此為例,對該份證據材料的證據種類和證據分類作出判斷。
首先,該案屬于一起侵權賠償糾紛,原被告雙方主要的事實爭議為:原告主張被告彭宇從公共汽車下車時撞倒了正在候車的原告,而被告彭宇則稱其是在下車后看到原告已經倒在地上的情況下,上前將原告攙扶起來。所以該案訴訟證明中的證明對象應為承擔一般侵權賠償責任的四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即被告彭宇是否實施了對原告的侵權行為,具體說來,就是彭宇是否撞倒了原告。
在明確了證明對象后,我們來分析一下證據內容和證據形式。從筆者掌握情況來看,該份筆錄照片的形成過程為:事情發生后,公安派出所介入了糾紛,由公安人員向彭宇進行了詢問,并制作了詢問筆錄。筆錄內容顯示彭宇承認自己撞倒了原告,筆錄上有彭宇的簽名捺印。公安人員制作完詢問筆錄后,原告之子用自己隨身攜帶的手機對詢問筆錄進行了拍照。從前述內容可以看出,筆錄照片中包含的與證明對象有關聯的信息為:彭宇撞到了原告。這個信息(彭宇撞到了原告)是以彭宇內在記憶進行外在表示——陳述的形式存在和體現后,又被公安人員以記錄在紙張上的文字內容的形式存在和體現出來,最后被原告之子以對詢問筆錄拍照方式儲存手機中,該信息在手機中的儲存形式為電子數據。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照片應為借助相關設備形成的電子數據的替代物。在前述事實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公安人員還是原告之子,其在制作筆錄或拍照時,應均不存在為后來的侵權糾紛訴訟進行收集證據的直接目的。
有了前述分析后,按照法律上關于證據種類的劃分依據,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證明對象為彭宇是否撞倒了原告時,證據材料“一份公安人員對彭宇詢問筆錄的照片”,從法官的視角來看,證據內容“彭宇撞倒了原告”是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和體現的,應認定為電子數據。同樣道理,在法官視角下,如果證據材料為一份公安人員對彭宇的詢問筆錄(不論原件或復印件),則應認定為書證;只有彭宇在訴訟程序中向法庭口頭或書面表示“彭宇撞倒了原告”時,才能將證據種類確定為當事人陳述。
證據種類固定后,按照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的劃分標準,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證明對象為彭宇是否撞倒了原告時,證據材料“一份公安人員對彭宇詢問筆錄的照片”,作為電子數據并非產生于“彭宇撞倒了原告”過程中,不是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應屬于傳來證據。同樣道理,在法官視角下,如果證據材料為一份公安人員對彭宇的詢問筆錄(不論原件或復印件),作為書證也并非產生于“彭宇撞倒了原告”過程中,不是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也應屬于傳來證據;只有彭宇在訴訟程序中向法庭口頭或書面表示“彭宇撞倒了原告”時,將證據種類確定為當事人陳述時,才能將其歸于原始證據。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
責任編校: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