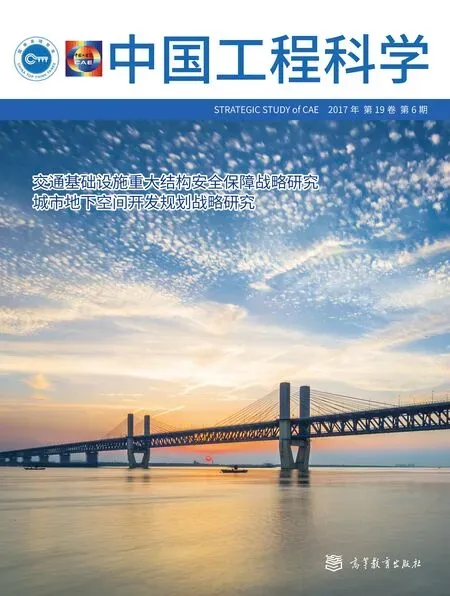城市明挖地下工程開發環境效應研究現狀及趨勢
朱亦弘,徐日慶,龔曉南
(1. 浙江大學濱海和城市巖土工程研究中心,杭州 310058;2. 浙江大學軟弱土與環境土工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杭州 310058)
一、 前言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逐步開始開發城市地下空間,經過30多年的發展,地下空間開發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其中復雜的城市地下綜合體以井噴式的速度發展。以浙江省地下空間開發為例,截至2012年年底,浙江省地下空間開發面積達12 181.9×104m2,且每年地下空間建成面積超過1×106m2[1]。近年來國內也涌現了一波地鐵建設潮,截至2017年7月,我國已經有32個城市開通了城市軌道交通,總里程達4 454 km,其中上海、北京運營里程已超過600 km,運營規模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
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呈現長、大、深的趨勢,隨著開挖深度和面積的不斷增大,地下空間開發引起的周邊環境問題也愈發受到重視。深層地下空間開發會引起周邊地層變動,導致既有建筑物、地下管線、盾構管片的不均勻沉降和開裂,影響各類建(構)筑物的使用功能甚至結構安全。因此地下空間開發過程中需要有科學合理的規劃、設計、施工、監測控制標準確保環境安全,以保證周邊建筑物、道路、地下管線等處于安全可用狀態。
二、 明挖地下工程環境效應研究現狀
我國城市明挖地下工程開發的主要矛盾已由早期的地下工程穩定性問題逐漸轉向地下工程周邊環境變形控制問題。
我國明挖地下工程多處于城市繁華中心地帶,地基開挖往往會影響周圍的重要建筑、市政道路、地下管線、地鐵盾構等設施,改變原有地應力場,引起周圍地層位移,導致周圍建(構)筑物產生不均勻沉降。因此現在亟需探明深基坑開挖引起的周圍地層應力場變化和周圍地層位移場的變化規律,并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控制變形。
(一)統計經驗法
Peck [2]最早對基坑變形開展了系統性研究,他提出了考慮地層差異的地層沉降及分布的經驗估算方法。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將基坑變形區域劃分為主要影響區域和次要影響區域,對兩個區域內地層的變形特征及區域分界展開了討論。學者們通過不斷分析基坑變形監測數據提出了基于各種因素影響的基坑變形經驗公式,并采用包括基坑坑底隆起、基坑擋土墻后地表沉降等參數來評估基坑的穩定性。
Brand等[3]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基坑支護系統變形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①支護類型;②支護體系的剛度;③擋墻的埋設深度;④預加荷載值;⑤施工暴露時間;⑥主體結構的施工方法;⑦地表超載值;⑧開挖形狀和深度;⑨地基土的特性;⑩周圍既有建筑物。
通過監測統計,基坑變形具有顯著的空間效應和時間效應,地基土暴露面積越大、暴露時間越長,其變形增長越大。尤其是在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的軟土地區,土體蠕變可以占到總變形的30% ~60%。因此軟土地區控制土體蠕變對控制基坑總變形量十分重要,基坑開挖后及時支設支護結構可以有效控制地基土蠕變。
統計經驗法基于實際觀測基坑開挖對周圍地層擾動的影響并由此提出地層變動形式和主要影響因素。限于實際工程情況和現場測點布置,一般只能獲得基坑開挖周邊地表沉降、圍護結構變形和坑底隆起等參數作為表征指標,與工程地質條件和支護形式相結合進行分析,并不能獲得完整的地基變形場。
(二)數值模擬法
隨著計算機科學的快速發展,數值模擬法在傳統工程設計中得到廣泛應用。基坑開挖的數值模擬可以更好地考慮巖土體的本構特性、工程地質條件、結構與土的相互作用及接觸面關系和復雜的開挖工況,因此在地下工程變形預測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
Duncan等[4]采用了非線性彈性模型對邊坡開挖的形狀進行了數值模擬,開創了地下工程變形數值模擬研究的先河。
數值模擬法可以考慮地下工程變形中的流固耦合問題,并且可以應用各種復雜的本構模型來模擬土體的應力應變性狀。自Duncan-Chang的非線性彈性模型之后,陸續有Mohr-Coulomb模型、Mises模型、劍橋模型及其修正模型、硬化土模型等應用到地下工程變形研究中。豐富的本構模型可以用于模擬不同應力路徑、各種工況下的巖土體變形性狀。
早期的數值分析方法將三維問題簡化為二維問題求解。二維數值分析可以較好地模擬隧道斷面開挖、長寬比較大的矩形基坑。近年來,隨著計算機計算能力的不斷增強,三維數值模擬方法逐漸成熟。研究發現,二維分析選取重要斷面進行變形預測模擬,其結果比三維模擬結果和實際監測結果偏大[5]。三維數值模擬方法可以更好地分析異形地下工程引起的地基變形。
數值模擬法可以低成本地模擬各類邊界條件、各類工況下地下工程的變形性質。明挖地下工程變形的影響因素繁多,工況的組合形式也較多,數值模擬法可以通過設置不同的變量組合進行研究。Rowe等[6]基于土體各向異性彈性假設,考慮了地層損失及注漿等因素對于隧道開挖時的影響,并引入了間隙參數,使得計算地層沉降時能夠考慮各種施工因素的影響。
數值模擬法可以較好地模擬巖土介質、開挖工況、邊界條件,并可以考慮滲流場、溫度場的影響,因而比傳統計算方法有明顯優勢,但國內數值模擬法應用時間較短,模擬方法和工程參數經驗積累較少,需要進一步的應用和積累以保證數值分析中參數選取的合理性。數值模擬對部分施工工況尚不能很好模擬,包括圍護結構施工和打樁置換等引起的擾動等。
(三)模型試驗法
模型試驗法是研究和驗證巖土工程理論的重要手段,早期的室內模型試驗主要研究基坑開挖的穩定性和變形機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近年來,基坑變形成為主要研究內容,小比尺模型并不能有效地模擬地基土的應力場,大比尺模型的試驗條件和成本較高,因此離心機模型試驗得到了快速發展。
早在1948年,Terzaghi等[7]利用室內模型試驗研究了散粒體填土材料的擋土墻壓力、墻體變形與土壓力關系、滑裂楔體角。
室內小比尺試驗著重研究墻后土體性質變化及墻體與土體接觸條件變化對基坑開挖時的土壓力及墻后地表沉降變化的影響。小比尺試驗的應力場和變形場不能完全模擬實際工況,只能進行基坑變形影響因素的定性研究。
離心機試驗可以較好地模擬應力場,保證模型箱區域范圍內應力條件接近實際工況,適合進行破壞失穩型試驗,可以較好地模擬基坑開挖各工況下地基與墻體應力和變形的變化趨勢。
大比尺試驗可以較好地模擬應力場與變形場,模型不需進行大比例縮尺,其加載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更符合工程和實際情況。我國大型巖土試驗平臺建設已取得長足進展,北京工業大學建成了目前國內最大的地下工程綜合試驗平臺(6 m×6 m×10 m),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大比尺試驗適合進行重要工程的多場多工況模擬論證研究。
模型試驗仍是明挖地下工程變形研究的最直觀手段,需根據研究目標和內容選擇合理的試驗方案。由于小比尺試驗縮尺效應應力場或變形場失真較嚴重;大比尺試驗的試驗成本較高,耗時較長;離心機試驗對基坑開挖的模擬經驗仍有欠缺,需要繼續研究開挖卸載工況等模擬方法。
三、環境保護措施研究現狀
地下空間開發不可避免地會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當產生的影響超過了既有建(構)筑物容許變形值時則需要采取相應的工程措施控制建(構)筑物的變形。根據保護對象不同可以分為以減小影響源的主動加固技術和保護受影響建(構)筑物的被動加固技術。
(一)主動加固技術
主動加固技術多是基坑開挖或隧道掘進過程中通過調整施工工藝和施工流程來達到控制變形的目的。其中盾構法、頂管法等非開挖技術施工系統性較好,一般以調整推進速度、刀盤壓力等施工參數來控制周邊環境變形,在變形敏感區域輔以二次注漿方法加固開挖掘進區域周邊土體。基坑開挖由于開發規模大,開挖卸載引起的周邊環境變形影響范圍大,會采用多種主動加固技術進行基坑自身加固。常用的基坑主動環境控制技術有加固基坑土體、優化基坑圍護體系、地下水降水隔斷和回灌技術等。
基坑土體加固是運用地基改良方法對坑底土體加固以提高被動區抗力,通過高壓噴射注漿法、全斷面注漿法和水泥土攪拌樁等工法改善開挖影響區內的土體強度和性質,為圍護結構提供支撐,控制基坑主要變形區的開展。
基坑周邊大范圍降水會引起周邊大面積沉降,需要采取地下水隔斷或者回灌技術以控制降水影響區域。俞建霖等[8]提出了一種回灌系統的設計方法及程序,可將抽提的地下水回灌到地下,減少地下水位下降從而避免地基因固結導致的沉降。
(二)被動加固技術
被動加固技術是針對受影響的建(構)筑物進行補強加固,以保證在地下空間開發過程中周邊建(構)筑物不會產生明顯開裂損壞。常用的被動加固技術包括隔斷法、基礎托換技術、注漿加固技術等。
隔斷法通過在基坑和受保護建筑之間打設隔離樁來隔斷由于基坑開挖引起的應力場變化,隔斷法常采用鋼板樁、樹根樁、深層攪拌樁等樁體形成具有一定剛度的墻體以承受基坑開挖引起的側向力和摩阻力。
為控制港珠澳大橋海底沉管隧道基礎沉降,竺明星等[9]進行了4組高邊載作用下隔離樁受力室內模型試驗,驗證了隔離樁隔斷變形場的作用。隔離樁在邊載作用下呈被動受力特性,隔離樁鄰近樁基的樁身最大軸力較無隔離樁的樁基減小約10%,樁身最大彎矩減小約20%,隔離樁隔離效果顯著。
基礎托換技術是為了避免既有建筑物基礎在地應力場變化的情況下產生過大差異沉降而將既有建筑物的荷載逐步轉移到新托換基礎上的技術。
注漿加固技術是在既有建筑物基礎周邊土體注漿加固,提高土體的承載力和模量,多適用于加固獨立基礎或條形基礎建筑,常用的注漿方式有壓密注漿和劈裂注漿。對注漿加固效果的機理已經有了較深的研究和認知,但在既有建筑物加固實踐中對注漿方法和注漿壓力的控制仍少有相關的文獻。
四、趨勢與建議
我國城市明挖地下工程開發的主要矛盾已由早期的地下工程穩定性問題逐漸轉向地下工程周邊環境變形控制問題,地下空間開發的環境變形預測與控制技術將越來越重要。
重要建(構)筑物的全生命周期變形沉降監測隨著物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而成為可能,有助于推斷建(構)筑物的容許變形值并提供相應的變形控制標準。
基坑變形監測數據云端存儲與大數據分析技術可以更好地分析同類型基坑的變形特質,使各類經驗公式的擬合數據規模快速擴大。
應效仿歐美大力推進將既有研究成果轉化為工程實踐的指導規范,繼續搜集完善補充各地區的環境控制案例。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應根據自身經驗和條件設定建筑物保護標準。
應進一步完善現有環境影響分析計算理論,建立考慮不同區域水文地質條件差異、復雜的巖土材料性質、周邊環境和荷載差異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環境分析方法。大力發展數值分析方法,結合本地區地下工程開發經驗,編撰數值模擬分析手冊。
隨著地下空間建設逐漸向深層地下空間和我國內陸地區發展,需要緊跟現有工程實踐情況,針對特殊地質條件、地下空間布局和結構形式、施工方法等開展模型試驗和數值模擬研究,以解決由諸如欠固結土區域開挖問題,軟土地區暗挖法的穩定性和沉降控制問題,超近距地下空間開發變形控制問題,超深基坑開挖、降水及回灌等新型工程問題引起的環境效應問題。
五、結語
解決城市明挖地下工程的變形預測與控制問題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筆者通過理論推導、模型試驗和現場實測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了基坑開挖引起的周邊環境影響變形場,對明挖地下工程的變形性狀已有了初步的認知。
變形控制技術還處在經驗指導的實施階段,需要進一步探明變形控制原理。
[1] 李海波, 楊樺. 浙江省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技術和技術標準體系研究 [R]. 杭州∶ 浙江省建筑科學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4.
Li H B, Yang H. Study on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for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in Zhejiang Province [R].Hangzhou∶ Zhejiang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 Design Co.Ltd., 2014.
[2] Peck R B. Deep excavations and tunneling in soft ground [C].Proceeding of the 7th ICSMFE, State-of-the-Art Volume, Mexico,1969.
[3] Brand E W, Benner R P. 軟粘土工程學 [M]. 北京∶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91.Brand E W, Benner R P. Soft clay engineering [M]. Beijing∶ China Railway Press, 1991.
[4] Duncan J M, Clough G W.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port allen lock [J]. Journal of the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s Division,ASCE, 1971, 97∶ 1053–1066.
[5] Chew S H, Yong K Y, Lim A Y K.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 strutted excavation underlain by deep deposits of soft clay [C].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NTU-KUKAIST Tri-lateral Seminar /Workshop on Civil Engineering,Korea, 1996.
[6] Rowe R K, Lo K Y, Kack G J. A method of estimating surface settlement above tunnels constructed in soft ground [J]. Canadial Geotechnical Journal, 1983, 20(8)∶ 11–22.
[7] Terzaghi K, Peck R B. Soil mechanic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M].New York∶ Wiley, 1948.
[8] 俞建霖, 龔曉南. 基坑工程地下水回灌系統的設計與應用技術研究 [J]. 建筑結構學報, 2001, 22(10)∶ 70–74.
Yu J L, Gong X N. Study on the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water recharge system in excavation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01, 22(10)∶ 70–74.
[9] 竺明星, 于汝康, 龔維明. 邊載作用下隔離樁受理特性及隔離效果研究 [J]. 巖土工程學報, 2013, 35(10)∶ 656–661.
Zhu M X, Yu R K, Gong W M.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olation effects of isolated piles due to side loading [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3, 35(10)∶ 656–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