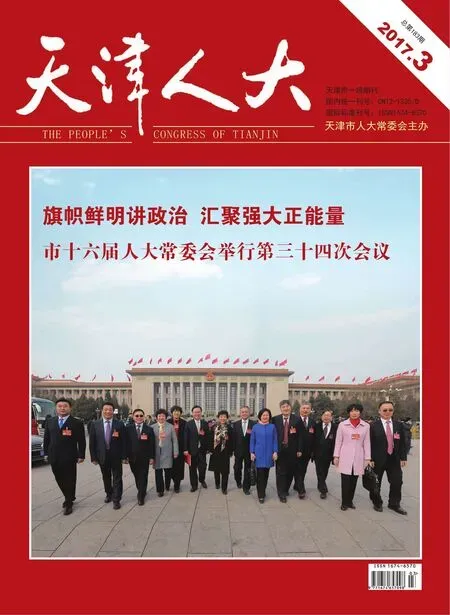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轉化(下)
楊大辛
讀書
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轉化(下)
楊大辛
一躍而為全國第二大城市
天津是在八國聯軍的屠殺中邁入20世紀的。侵略軍在占領了這個城市之后,立即建立臨時政權機構——都統衙門,實行全面的軍事管制。1901年都統衙門強令拆除天津城。這座被視為天津象征的城堡,在當時已有近五百年的歷史,拆毀它是天津人從感情上所無法忍受的。有形的城垣被拆除了,無形的時代樊籬也被打破。在戰爭的廢墟上,天津的城市建設重新起步。
1902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從都統衙門手中把天津接收過來。袁世凱借鑒都統衙門對城市管理的機構設置與制度,設立了工程局、商務局、衛生局、捐務局等市政機關,并組建了中國最早的一支警察隊伍,強化了城市管理體系。袁世凱在津執政期間的另一大舉措是開辟了海河以北的新市區——包括一條新的干道大經路(今中山路)與兩側的街道網絡,以及在大經路北端新建火車站(今北站)。在新市區的規劃地段內,拆遷了大批民房與塋墓,建造商店、工廠、學校、公園與住宅,并將一些政府機關遷到河北新區,建筑格局大多仿照西方模式。為了溝通河北新區與舊城區、租界區之間的交通,跨海河修建了開啟式鐵橋即金鋼橋。1904年經袁世凱批準,由比利時商人開辦電車電燈公司,1906年建成金家窯發電廠,有軌電車同時通車,使天津成為中國最早擁有近代公共交通的城市。
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河北新區形成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舊城廂的環城馬路也逐步繁華,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日臻完善,天津的近代城市風貌初步展現出來。這一期間租界區的發展更為迅速,宏偉華麗的建筑物與高雅別致的小洋樓住宅大批涌現。總的說來,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老城區與租界區的城市建設并肩發展,不過租界區始終領先一步。
天津的近代工業始自19世紀60年代官辦的軍事工業,設備與技術均從國外引進,產品基本上不進入市場,因此不能代表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總體水平。外資企業主要是為出口貿易服務的打包廠、打蛋廠、絨毛加工廠等,規模都不大。民族資本企業也開始出現,最早的為1878年朱其昂創辦的貽來牟機器磨房、1884年羅三佑創辦的德泰機器廠、1886年吳懋鼎創辦的火柴廠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后,官辦的軍事工業被毀,天津早期的工業基礎遭到全面的破壞,留下來的大批技術工匠轉為民族工業發展的基本技術力量,如三條石機械工業區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20世紀以后,天津的近代工業重新起步,大興“辦實業”之風,在1902年至1913年的十年間,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新式工廠有49家,涉及紡織、面粉、火柴、榨油、制皂、卷煙、造紙、機械制造等行業。1914年歐洲大戰爆發,西方國家無暇東顧,為天津的工業發展帶來契機。據1928年天津社會局的調查,當時在天津的中國城區的工廠達2186家,資本總額3300萬元,其中制鹽、制堿、紡織、面粉等17家大型企業的資本額合計為2900萬元,占資本總額的88%。此外,在租界內還有中外資本的工廠3000余家。20世紀20年代可稱之為天津近代工業發展的騰飛時期,從而奠定了天津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工業格局。
天津口岸的對外貿易在進入20世紀以后發展迅速,至30年代初達到高峰。據海關的統計:1902年的進出口貿易凈值為89478 464海關兩,至1911年上升到116536648海關兩,每年平均以300萬海關兩的速度遞增;至1921年上升到224779202海關兩,1931年更上升到350229927海關兩,1921年至1931年間每年平均以1200萬海關兩的速度遞增。若就進出口船只的艘次與噸位統計:1900年為852艘、804292噸;1911年達到2187艘、2720547噸;1931年猛增到3349艘、5000331噸,是1900年艘次的3.9倍、噸位的6.2倍。外貿的興旺促進了港口建設與航運業發展。海河兩岸大型企業的碼頭設施,從20世紀初期的四十余處發展到一百五十余處。早期航運業基本上為外商航運公司所壟斷,自1872年中國官僚資本的輪船招商局的建立,1900年以后民營航運公司也有所發展,從而打破了航運業外商的一統天下。
天津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在20世紀以后出現了一股“銀行熱”,尤其是1928年以后進人繁盛時期。據統計:1928年天津有外資與中外合資的銀行24家,華資銀行(包括官辦與民辦)56家。由于銀行大多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今解放路)及其周邊,故中街亦有“天津華爾街”之稱。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銀號,發展更為活躍,1928年共有二百六十多家。天津金融業發展的一大特點是對華北、西北腹地的輻射面比較廣,因而形成北方地區的金融中心。就金融業的總體規模而言,天津僅遜于上海而居全國第二位。
商業作為城市繁榮的窗口,天津久負盛名,傳統的商業繁華區位于北大關至大胡同一線與宮南宮北大街,以及后來的環城馬路。及至民國以后,由于壬子兵變、軍閥混戰、便衣隊暴亂等一系列政治動亂,商業資本家深受其害,于是從20年代開始逐漸向日、法租界轉移,至1928年勸業場建成后,周邊形成規模商業區,商業資本大批投入,旅館、商店、飯館、影劇院、歌舞廳櫛比鱗次而立,在30年代成為天津的商業娛樂中心地帶,尤其是入夜燈火通明,觥籌交錯,輕歌曼舞,是有錢有閑的人們盡情享樂之鄉,乃有“東方小巴黎”之稱。
天津在向城市近代化轉化的過程中,體現了中西方文化融匯的城市文化結構也逐步形成。天津開埠后,扮演傳播西方文化角色的傳教士,他們在辦學與行醫方面所取得的成績,顯然要比傳教更見實效。教會學校推行西方學制,革新了教育的知識結構,尤其是音樂、美術、體育之類的課程,使學子耳目一新,因而天津成為開展足球、籃球、排球、滑冰、乒乓球等競技運動最早的城市。天津近代教育事業的發達,一直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天津的新聞業起步早,發展快,是傳播西方文化的重要媒體。嚴復在1897年創辦的《國聞報》雖曇花一現,但其譯著《天演論》的發表,風靡全國,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在30年代,天津出版的報紙多達三十余種,其中《大公報》《益世報》享譽全國。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等新興文化設施,在天津出現的時間都比較早。在文化娛樂方面,西方文化的滲透更為明顯,西洋音樂、歌舞、繪畫被視為高雅藝術享受而為知識界所接受;至于電影的傳入與逐步普及,更成為廣大市民群眾文化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帶有賭博色彩的賽馬與賽回力球,也成為某些人熱衷的娛樂活動。與此同時,傳統的京劇、曲藝、評戲以及新式話劇、文明戲等,都占領著很大的文化陣地。在文學活動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興盛一時,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中再現高潮,涌現了許多文學社團與文學刊物。但就文化市場的總體而言,始終不衰的則是通俗文化,包括言情、武俠小說、年畫以及說唱藝術,擁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構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
30年代的天津,從經濟綜合實力、港口吞吐能力、城市基礎設施、交通網絡、文化結構以及人口規模等諸多方面,在國內都居于領先地位,一躍而為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
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重新涌入天津,尤其是日本基于侵略目的的經濟掠奪與兼并活動,致使民族工業的發展受阻。日本在華北走私活動的猖獗,對正常進出口貿易也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并占領天津之后,天津的經濟、文化發展從而受到嚴重挫折。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政權重返天津,又因發動內戰而使天津的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由于這十數年的政局動蕩與戰亂,天津的城市發展逐步走向停滯與衰落,元氣大傷。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才得以復蘇,再度繁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