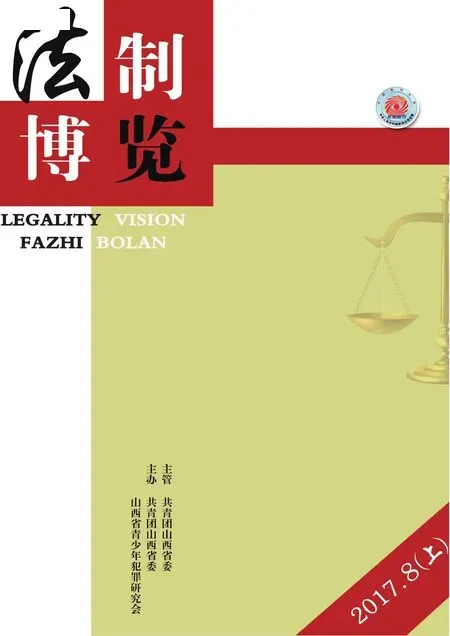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定位及相關的立法建議
葉麗靜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定位及相關的立法建議
葉麗靜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職務犯罪中的強制措施作為一類偵查手段,其制度安排是否規范,直接關乎到犯罪偵查的最終效果。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所作的規定還不詳盡,這不僅深刻影響到對職務犯罪的打壓力度,也妨礙著反腐敗斗爭的進行。為了更加良好地施展強制措施的應有功能,相關單位應關注職務犯罪偵查活動的施行狀況,并積極開展立法制度完善方面的研究。
職務犯罪;強制措施;屬性定位;立法約束
2017年反腐大劇《人民的民義》熱播,讓我們知道,現今社會上的利益誘惑越來越多,許多人憑借自身職權行財務竊取之便,而這種行為,指的就是職務犯罪。我國社會目前處在全面轉型之中,如何采取切合實際的措施來防范和懲罰職務犯罪,是非常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的關鍵問題。
一、職務犯罪偵查與普通犯罪偵查強制措施間的對比
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指的是檢察部門在調查職務犯罪的過程中,為了確保調查活動的順利施行,根據法律規定對職務犯罪嫌疑人所實行的臨時約束其人身自由的手段。從內涵上能夠知道,職務犯罪偵查與普通犯罪偵查強制措施間的關聯有如下三項:
(一)兩類強制措施的相同之處
1.兩者的主體適用都具備合法性。對職務犯罪被告人采用強制手段特別是進行逮捕,顯然關系到此犯罪者的人權權利。而如今法治社會授權哪些國家部門能夠實施強制手段有著審慎且清晰的法律條款。沒有法律承認的部門,一律不可擅自對職務犯罪者使用任何約束或管制其人身自由的強制手段。
2.兩者對權利的限制都具有單一性。不管是檢察部門還是公安部門,使用強制手段都與職務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權密切關聯。“至于在偵查中需要依法對財產權、隱私權進行限制,則需要采用搜查、扣押、監聽等強制性措施,而不能采取偵查強制措施。”①
3.兩者措施的行使都具備強制性。檢察、公安部門實施強制手段的堅實后盾來自國家公權力,采取強制手段無須事前告知職務犯罪者們,它造成的明顯后果是暫時約束與管制犯罪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從字面上講,強制即施加壓力而使之服從。”②即便職務犯罪者可以違背命令,但此種抵抗將為他帶來更可怕的結果,從而該被告人只能依照國家法律作出合法的抉擇。
(二)兩類強制措施之間的不同點
1.兩者部門之間存在不同。檢察部門是職務犯罪類案件強制手段的最后執行者,并依照職務犯罪調查的現實效果進行審判;在普通犯罪案件中,最終是否選擇實施強制手段的權力在于國家公安、海關等部門。
2.兩者對象的適用存在差異。職務犯罪調查部門所使用的強制手段,其對象是職務犯罪者。而公安、海關等偵查部門在調查中采用強制手段針對的是普通犯罪被告人,普通刑事犯罪者不論在人際關系或知識素養等層面都比不上職務犯罪者具備的能力。
3.兩者對程序的規定存在不同。檢察部門在調查職務犯罪案子時選擇運用拘傳、取保候審等手段的,由其審判后交由公安部門實施,這是為了對檢察部門的權力進行有效的約束。而公安部門在調查普通刑事犯罪類案子時使用拘傳、羈押等手段的,既可以不報檢察部門審批,也無須由檢察部門施行。
二、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類別及其主要功能
依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款,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種類,主要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種。在法律本質層面,這五種強制措施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發揮著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開展的功能。其中,拘傳是公安部門、檢察部門、法院對暫未關押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告人等,依法命令其到案進行審訊的一項強制手段,也是力度最輕的一種。取保候審強制方式是上述部門對未被拘捕或者拘捕后需要變更執行的犯罪嫌疑人,為避免其逃脫偵查、起訴和判決,責令其選擇保證人或交納保證金,而作出的對其不予羈押或暫緩羈押的決定,由公安部門執行。這些國家機關責令犯罪嫌疑人在法定時限內不可隨意離開住所,并監視其活動、限制其行為的強制措施被視作監視居住。拘留則是公安部門或者檢察院對現行犯、犯罪嫌疑分子,暫時行使的強制手段。相反,“逮捕指有關國家機關為了遏制被告人進行妨礙刑事訴訟的活動,如逃避偵查、起訴或潛在的社會危險性,而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執行措施。”③
此外,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功能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程序保障功能
規制強制措施的中心立法主旨即是保障職務犯罪偵查、起訴和判決等訴訟行為的有序進行,而使用強制手段的根本目標在于確保以及推進調查任務的成功開展。如果在實施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手段時期限已至抑或有阻礙偵查行為繼續進行的因素浮現,就應及時地改變、推翻或是廢除。
(二)遏制犯罪功能
從暫時制約或剝奪職務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實踐成效上看,對嫌疑人采用強制執行手段,顯然能夠起到積極規避或是有效遏止職務犯罪者施行新的犯罪的功能。另外,也能夠幫助偵查部門制止職務犯罪嫌疑人繼續造禍于社會情形的發生,從而維護好國家、社會、人民群眾的利益。
(三)人權保護功能
在歷史變遷中,近代成熟起來的人權主義,大致是以刑事司法中對強制措施的管制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強制措施在保護人權方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運用立法手段來規制使用標準、步驟,進而防止濫用強制手段情形的發生。因為,“政府運用強制性權力對我們生活的干涉,如果是不可預見的和不可避兔的,就會導致最大的妨礙和侵害。”④
三、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存在的問題
對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研究,我國在上世紀末就應當開展,但是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目前我國在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中顯現出許多矛盾。
(一)機構設置缺乏獨立性
檢察部門是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的主要機構,與此同時,由公安部門所建立的經濟犯罪案件偵查部門,也承擔著調查貪污、賄賂犯罪及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瀆職等的偵查工作。此外,我國檢察院內部設有三個掌握刑事偵查權的部門,即:反貪污賄賂部門、瀆職侵權偵查部門以及監所部門。但因為職務犯罪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在屬性上存在不小的差異,所以必須設立單獨的偵查部門,才能有效發揮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功能。
(二)拘傳措施的適用存在弊端
其一,我國法律未清晰界定傳喚與拘傳適用的部門、對象、領域等。《刑事訴訟法》第50條提到:根據案件情況,可以拘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而所謂的“案件情況”,并不十分明晰。此外,立法沒有嚴格界定拘傳以及傳喚的標準、條件,有關部門常常會對某些能夠使用傳喚手段的職務犯罪嫌疑人進行非法拘留與審訊,甚至出現職務犯罪調查單位濫用傳喚、拘傳手段的狀況。其二,《刑事訴訟法》第92條中明確:拘傳持續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法律對拘傳合法時限不能超出12小時的條款深深脫離了職務犯罪調查工作的現實。在實踐中,要在拘傳犯罪者后的12小時內得到此案突破性進展的可能性極其細微,辦理賄賂案子時則更為艱難。
(三)監視居住措施的適用問題
在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使用范圍、標準并沒有明確界定,而且在踐行環節中,這兩類偵查強制措施的權力行使具有較大的隨機性。甚至,這種行為極易產生偵查機構變相羈押的現象。此外,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實際中,公安部門為了節約人力,將拘留所或是強制隔離所當作法定的監視居所,約束了職務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這也將合法的監視居住措施轉化成違法的羈押。
四、完善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的立法建議
在我國職務犯罪調查中,充分施展強制手段成效的關鍵在于:其一,在偵查中提升強制措施偵查機關的工作獨立性;其二,優化強制措施方式適用中的權力機制。
(一)完善強制措施中機構的權力行使機制
在職務犯罪偵查強制措施中,采用逮捕決定權應從近期、遠期進行全局性考慮。筆者主張,“逮捕決定權”統一歸由人民法院掌握較為合理。這是規避職務犯罪偵查下“自偵自捕自訴”行政程序色彩濃郁、權利行使困境的善策。如若將批捕權交由上一級檢察機關行使,不但在邊遠區域難以操控,而且也未改變自偵自捕的整體定位。對職務犯罪嫌疑人自身而言,在權利救濟的便利性以及可行性上,顯然不如統一交由法院行使來得高效。不過近期,在憲法明確保留檢察院“逮捕決定權”的大條件下,出于維護憲法體制、司法權威以及法院理性工作上的考慮,宜維持“逮捕決定權”的實施現狀,但應當補充職務犯罪被告人與其相關近親屬、辯護人等后續向同級人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的權利,并就此事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法院核查的重心是審查逮捕的合法性,對于背離法律的逮捕應當給予撤銷,對于過失逮捕則應啟動國家賠償程序。
(二)改進拘傳措施的立法建議
立法應當嚴格界定拘傳的適用對象、條件和范圍。傳喚不應該拘捕或羈押的職務犯罪被告人,并指令其到庭承受審訊時,假如犯罪者拒絕到庭,這時就能夠對其采取強制到庭的手段,傳喚的本質繼而產生轉變,變為拘傳。建議從立法上進行界定,對不需要拘留或逮捕的職務犯罪嫌疑人采取拘傳,特殊條件下可直接適用。此外,建議對職務犯罪嫌疑人的拘傳期限由不能超出12小時改變為24至48小時。在現實中,因為職務犯罪屬于一項高智商的違法活動,作案潛伏期較久,且留下的書證、物證極少,假如不能及時制成職務犯罪者的招供筆錄,檢察部門往往畏于立案包括使用強制手段。從世界各國的相關規定看,警察對任一民眾“無證逮捕”后的關押時限一般不能超出24小時,但經擁有更高警銜的領導準許,能夠將這一時段延長12小時。“在上述期間之外如果還要延長對犯罪嫌疑人的羈押期間,須經治安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合法授權,但最長的期限一般不得超過96小時。”⑤換句話說,國外法律中提到的對職務犯罪嫌疑人進行拘傳的時限,大致可分成24、36、96小時等三個層次。
(三)完善監視居住措施的立法建議
其一,明晰監視居住的法律條款。依法指定實際辦案的檢察部門為合法的執行者,細節由檢察部門的司法警察負責進行;明確刑事訴訟法第57條提到的“住處”往往為犯罪被告人的經常居住地。其二,確定監視居住的措施以及方式,保障監視居住的現實成效。應批準實際辦案的檢察部門能夠采取電子監聽技術積極開展監視居住;授予檢察部門暫扣被監視居住人的出入簽證、駕駛證等證件的權力,建議相關機構或其他監管部門撤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職務、從業資格證明等;準確規定實際辦案的檢察部門能夠運用對被監視居住對象同其近親屬、同住者合理的隔離手段,以阻止犯罪者對其他民眾人身、財產等一些法定權利的侵害。假如無法有效分離或間隔的,即可對其運用指定居所的手段推行監視居住。
[ 注 釋 ]
①[德]克勞思·羅科.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②朱孝清.職務犯罪偵查學[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③宋英輝.職務犯罪偵查中強制措施的立法完善[J].中國法學,2007(5).
④[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⑤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D
A
2095-4379-(2017)22-0077-02
葉麗靜(1992-),女,漢族,浙江麗水人,上海政法學院研究生處,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學、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