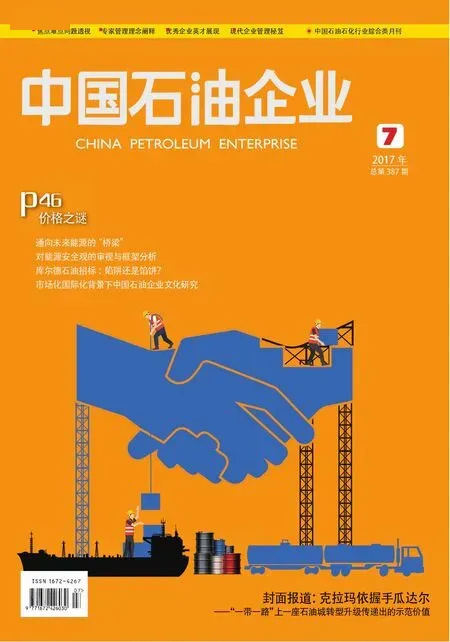對能源安全觀的審視與框架分析
□ 文/林益楷 王亞莘
對能源安全觀的審視與框架分析
□ 文/林益楷 王亞莘
能源是國家經(jīng)濟的重要支柱,在經(jīng)歷一戰(zhàn)、二戰(zhàn)和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后,對能源獲取的“恐懼”,成為所有能源消費國的“心頭之痛”。隨著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的日益攀升,能源安全問題已上升為國家的重要課題。如何看待能源安全領(lǐng)域的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種觀點之爭,如何審視中國的能源安全狀況,如何更好地維護國家能源安全?本文嘗試進行分析與探討。
兩種能源安全觀之辯
國際能源界對實現(xiàn)能源安全的路徑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在《21世紀能源安全挑戰(zhàn)》一書中,蓋爾·勒夫特和安妮·科林梳理了現(xiàn)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
現(xiàn)實主義者認為,油氣作為一種可完全耗竭的能源資源,其戰(zhàn)略價值大于市場價值,能源可能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國與國之間要依靠競爭和戰(zhàn)爭才能獲取資源。因此,石油的爭奪注定將是一場“零和博弈”,國家間的合作雖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緩解這一屬性,但不可能完全回避競爭。理想主義者則認為,沒有世界的能源安全就沒有一國的能源安全。石油和天然氣都屬于全球性的交易商品,完全可以按照市場機制來運行,這依賴于全球不同國家、公司之間的相互依存與合作。追求能源安全可以通過減少需求、擴大國內(nèi)能源供應、能源供應多元化、拓展全球貿(mào)易和投資來實現(xiàn)。著名的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曾說過:“真正的能源安全是不再做能源獨立的白日夢,而是相互依賴支持。”
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能源安全觀背后,實際上是西方國際關(guān)系學界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思潮在能源安全領(lǐng)域的折射。國際關(guān)系學知識譜系的核心內(nèi)容是沖突與合作,或者說是戰(zhàn)爭與和平。政治現(xiàn)實主義此前一直是國際關(guān)系學界公認的理論范式,從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到華爾茲為代表的新現(xiàn)實主義,都將沖突作為國家間關(guān)系的基本事實和根本特征,認為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而達成和維持和平的關(guān)鍵因素是實力,根本機制是大國間的實力分配和力量制衡。
隨著全球能源生產(chǎn)和供應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石油生產(chǎn)貿(mào)易機制已發(fā)生深刻變化。石油的商品屬性和金融屬性日益彰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國際能源署(IEA)等組織先后誕生并相互角力,跨國能源開發(fā)與供應商(賣方)和國際資本(買方)的作用也在加強,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guān)方參與市場博弈。有人認為,石油安全早就已經(jīng)不再是簡單的能源供應充足的范疇,而是一個國家甚至多個國家彼此相互影響的能源系統(tǒng)性風險。全球化時代能源輸出國與能源進口國之間關(guān)系的實質(zhì)是相互依賴,沒有穩(wěn)定的進口就不可能有穩(wěn)定的出口。
幾個關(guān)鍵問題的辨析
一是能源安全是否等同于能源獨立?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幾任總統(tǒng),如尼克松、卡特、小布什和奧巴馬,都曾提出過能源獨立的概念。隨著美國“頁巖油氣革命”的興起,有機構(gòu)預測美國到2030年會實現(xiàn)能源獨立。然而,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美國能源獨立不是指能源供應只靠自己、不靠別人,形成封閉的自我循環(huán)經(jīng)濟圈,能源獨立更多是一種美國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戰(zhàn)略目標和指導思想,它的核心是要充分利用國內(nèi)、國外有利條件,通過增加本土油氣供應、鼓勵節(jié)能增效、大力發(fā)展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等措施,從而建設一個有利于美國的能源安全保障體系。
二是能源供需雙方誰更強勢?對很多國家來說,傳統(tǒng)能源安全的概念就是需求安全。自從石油成為主流能源以來,石油消費國似乎先天處于弱勢。然而,從20世紀后半葉幾次國際油價下跌可以發(fā)現(xiàn),如果石油供應中斷,不僅將威脅到石油消費國的利益,對產(chǎn)油國也將產(chǎn)生重大影響。當烏克蘭危機爆發(fā)之時,國際輿論普遍擔心俄羅斯會切斷輸歐天然氣閥門,但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俄羅斯比歐洲更依賴天然氣出口帶來的收入(目前俄羅斯70%的預算來自油氣出口)。
三是產(chǎn)油國是否希望油價越高越好?石油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價格安全。價格上漲對能源資源供應國來講是否就是大好事呢?恐怕未必。從經(jīng)濟上看,當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短期內(nèi)產(chǎn)油國可能會獲得額外的石油收益,但長期看也會影響全球經(jīng)濟復蘇步伐,而全球經(jīng)濟減速會帶來石油需求減少,導致價格大幅下跌。從能源替代上看,石油價格長期居高不下,必然會引發(fā)能源節(jié)約技術(shù)研發(fā)和尋找替代能源進程的加速,促進資源循環(huán)利用,從而降低能源消費,影響整個石油行業(yè)的發(fā)展。
四是爆發(fā)石油戰(zhàn)爭的可能性?在石油供需穩(wěn)定的形勢下,所有與石油生產(chǎn)相關(guān)的參與者都擁有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一旦打破這種穩(wěn)定局面,對誰都是無益的。能源研究學者費特維斯認為,由于正常購買石油的成本要低于發(fā)動戰(zhàn)爭奪取能源的成本,因此發(fā)動能源戰(zhàn)爭是徒勞的。目前,中國75%的石油通過馬六甲海峽運輸,一些人擔心馬六甲運輸通道是中國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但有些學者并不認為“馬六甲困境”是一個真實的命題,其理由是亞太各國能源、經(jīng)濟對于該航線高度依賴,一旦在馬六甲海峽出現(xiàn)通航困難,受影響的將不單是中國的能源安全,更會影響整個亞太、甚至世界的經(jīng)濟安全。
中國能源是否安全?
從石油對外依存度看,根據(jù)管理學“木桶效應”理論,一個國家的能源是否安全,實際上最終取決于最不安全的那種能源,而不是整體能源。油氣供應安全是中國能源安全的“短板”,根據(jù)中國石油經(jīng)濟技術(shù)研究院發(fā)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62%,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上升至32.2%。目前,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jīng)高于美國,且呈持續(xù)攀升態(tài)勢,業(yè)界預計2020年將超過70%,2030年將超過80%。反觀美國,近年其石油對外依存度在不斷下降,美國目前已是煤炭和天然氣出口國,而石油進口量也在逐年下降,美國石油液體能源(含石油、液化天然氣和乙醇汽油等)對外依賴度從2005年的60%,下降到2014年的26%。中美兩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的反差,勢必影響中美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全球能源安全態(tài)勢。
從能源供應多元化看,2014年中國從中東和非洲地區(qū)的沙特、安哥拉、伊朗、伊拉克、蘇丹、阿曼6個國家進口原油超過總進口量的60%,進口石油90%以上需要從海上船運,其中80%必須經(jīng)過馬六甲海峽,長距離石油運輸存在較高的成本和不確定性。而美國石油進口正逐步從中東轉(zhuǎn)移至自家“后院”。2014年美國從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周邊國家進口石油占比達41%(加上中南美洲占比達58%)。對美國來說,從周邊地區(qū)進口石油,無論從能源運輸成本、運輸安全等方面都有優(yōu)越性,其“舍遠求近”的石油進口多元化策略值得中國學習。
從能源消費結(jié)構(gòu)上看,盡管中國整體能源供應是安全的,但是能源消費結(jié)構(gòu)非常不合理。2013年,煤炭占整個中國能源消費比重是67.5%,石油占比17.8%,天然氣是5.1%,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一次能源消費仍以煤為主,遲遲無法進入油氣時代,不僅導致國內(nèi)整體能源利用效率不高,還帶來了巨大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而在美國2013年的一次能源消費結(jié)構(gòu)中,石油占36.7%,天然氣占29.6%,煤炭占20.1%,相較其2005年的能源結(jié)構(gòu)(石油占40.27%,天然氣占22.5%,煤炭占22.73%)更加合理,盡管依然以化石能源為主,但石油、煤炭等傳統(tǒng)高碳能源所占比重正在減少,天然氣比重得到較大提高。美國從“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的過渡取得比較大的成效,而中國能源發(fā)展“去碳化”進程則面臨很大的挑戰(zhàn)。
從能源利用效率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看,當前中國能源利用效率整體偏低,2000-2011年間能源彈性系數(shù)平均為0.77(其中2003年和2004年竟達1.43和1.6),而發(fā)達國家一般不超過0.5。此外,中國能源消費強度高,2011年我國GDP約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約占世界的19.3%,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國的2.4倍,日本的4.4倍。有專家認為,中國之所以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過去10年來,美國在提高能效方面領(lǐng)先中國。
實現(xiàn)中國能源安全的路徑選擇
下一步,中國應充分借鑒美國實施“全方位能源戰(zhàn)略”的戰(zhàn)略設想(美國白宮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發(fā)布《“全方位”能源戰(zhàn)略——通向經(jīng)濟可持續(xù)增長之路》),大力推進能源生產(chǎn)和消費革命,為實現(xiàn)國家能源安全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
一是堅定推進多元化戰(zhàn)略,強化能源“戰(zhàn)略買家”角色。考慮到國內(nèi)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稟賦的“短板”,油氣供應安全將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議題,也是中國推進能源生產(chǎn)與消費革命需要著力關(guān)注的領(lǐng)域。中國應該統(tǒng)籌好國內(nèi)國際兩個市場,堅定不移地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大力推進石油供應多元化,構(gòu)筑起網(wǎng)狀、鏈式的能源供應體系。在鞏固好非洲、中東等傳統(tǒng)油氣供應地的同時,強化在能源供給新重鎮(zhèn)的“戰(zhàn)略買家”角色:更加關(guān)注中亞和近鄰俄羅斯,以能源合作為紐帶,擴展自身能源供應安全與對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交集;根據(jù)全球“能源生產(chǎn)重心西移”的趨勢——墨西哥國內(nèi)油氣領(lǐng)域開放步伐加快,拉美地區(qū)的巴西等國近年處于油氣大發(fā)現(xiàn)階段,應抓住機遇,在生產(chǎn)過剩的“全球油價再平衡”短暫戰(zhàn)略窗口期,繼續(xù)深化與中南美洲相關(guān)國家的能源合作,使之成為中國能源供應的重要穩(wěn)定來源,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博弈能力。
二是做好油氣行業(yè)“戰(zhàn)略簡法”,釋放制度紅利。美國通過市場機制,推進能源革命,增加了國內(nèi)油氣產(chǎn)量,降低了石油進口依賴度,減少了貿(mào)易赤字,促進了就業(yè),提升了美國國內(nèi)能源安全。我國在推進能源生產(chǎn)和消費革命時明確提出,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構(gòu)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jié)構(gòu)和市場體系。當前,油氣市場發(fā)育不足、市場參與主體較少是我國能源領(lǐng)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因而,要本著“在全產(chǎn)業(yè)鏈引入競爭”的思路,做好油氣行業(yè)“戰(zhàn)略簡法”,簡化不必要的行政規(guī)制,充分發(fā)揮價值規(guī)律與競爭機制在能源生產(chǎn)與消費中的作用,堅持由市場形成能源價格,通過在上下游各領(lǐng)域逐步放寬準入、引入多元投資主體、放開競爭性環(huán)節(jié)價格、探索實施混合所有制等多種途徑,進一步激發(fā)石油市場活力。
三是推進結(jié)構(gòu)能效并舉措施,升級能源安全“戰(zhàn)略匹配”。隨著近年來環(huán)境問題的日益突出,根據(jù)政策目標調(diào)整,中國國家能源安全的重心也開始從追求安全、穩(wěn)定、經(jīng)濟、高效的能源供應戰(zhàn)略匹配,到追求安全、高效和清潔能源供應戰(zhàn)略匹配的重大轉(zhuǎn)變。美國目前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已低于1970年的50%水平,我國政府做出了到2020年單位GDP減排40%-45%的承諾,必須在提高能效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四是激活“亞投行”能源安全“周邊外交”角色,實現(xiàn)能源基建戰(zhàn)略牽引。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取得巨大進展,未來,“亞投行”也勢必承擔其能源角色。中國應積極借力“亞投行”,以跨國能源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為契機,重新戰(zhàn)略性調(diào)整周邊能源安全形勢。首先,借力資本市場、貨幣市場,改造升級既有的中國及周邊區(qū)域的能源基礎設施,確保能源基建“存量”安全可靠。其次,協(xié)調(diào)區(qū)域內(nèi)跨國能源基建規(guī)劃,實現(xiàn)能源基建“增量”有利布局。再次,在能源安全角度,整合“亞投行”機制與“一帶一路”戰(zhàn)略,在更廣的地理范圍內(nèi),拓展中國能源安全戰(zhàn)略縱深空間。
五是積極介入全球能源金融體系,擔當虛擬能源資本市場戰(zhàn)略交易方。當前,伴隨國際金融創(chuàng)新快速發(fā)展,能源金融衍生品成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一環(huán),亦成為影響國際石油供給關(guān)系、造成價格波動的核心因素之一。因而,中國加強能源安全建設,需要更加創(chuàng)造性地介入由于自身起步較晚,還依舊陌生的全球能源金融市場:近期看,函待加強對國際能源金融市場的深度參與,在期貨市場、證券市場、證券投資基金市場等金融市場中,熟悉規(guī)則、對沖風險、配置資源、鍛煉人才,提高資本市場博弈能力;遠期看,需要建設具有一定競爭優(yōu)勢的能源金融交易中心,以期逐步形成可與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等能源金融市場制衡的能力,從而維護全球能源金融市場的多元穩(wěn)定。
(林益楷: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高級經(jīng)濟師;王亞莘: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