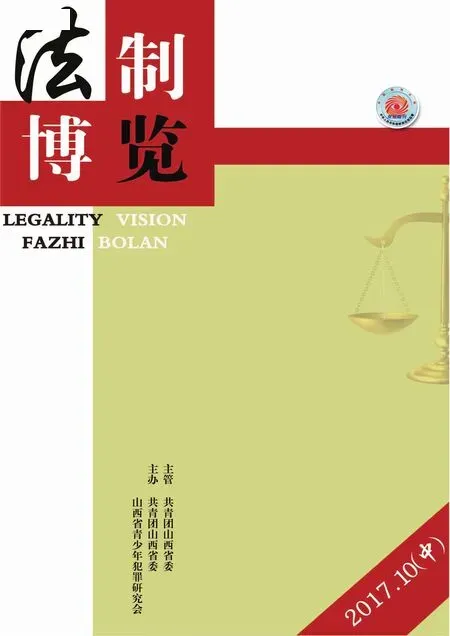淺談誘惑偵查基本問題及可行性分析
王 強
浙江警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淺談誘惑偵查基本問題及可行性分析
王 強
浙江警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3
誘惑偵查是一種偵查手段,是偵查部門針對特定案件而采取的特殊偵查措施。由于誘惑偵查打擊犯罪的有效性,因此在實踐中應用較為普遍,但是我國現行立法卻未對誘惑偵查手段加以明確。關于這種特殊偵查手段的合法性問題,社會普遍存在較大爭議,甚至對誘惑偵查產生質疑,有的觀點認為誘惑偵查不合法,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侵害。本文首先對誘惑偵查的概念進行闡述,然后對我國偵查部門適用誘惑偵查的現實狀況以及誘惑偵查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誘惑偵查;法律規制;可行性;程序控制
一、誘惑偵查的定義
基于抓捕犯罪分子的目的,偵查部門設置“陷阱”,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引誘,在犯罪嫌疑人繼續犯罪過程中對其實施抓捕,這種偵查方式是警察圈套,也是偵查陷阱,被稱為誘惑偵查。法國大革命之前,誘惑偵查被正式確定為偵查手段的一種。統治者基于抓捕革命黨人、鎮壓資產階級運動,維護國家統治的目的,推出了一種特務政策,即誘惑偵查。誘惑偵查在刑事偵查領域的作用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后越來越明顯。
二、我國誘惑偵查的現狀
國內現行立法尚未對誘惑偵查這種特殊的偵查手段予以法律確認,但是在法學界普遍認可的是:基于獲取犯罪線索、抓捕犯罪分子的目的,偵查部門采取一些引誘手段,在犯罪嫌疑人繼續犯罪過程中或犯罪行為發生之后實施抓捕,這種偵查手段就是誘惑偵查。我國現行《刑訴法》規定:偵查過程中,不得采用刑訊逼供和引誘、欺騙、威脅等非法手段采集犯罪證據。該法條并未對“欺騙”的內涵作出合理解釋。從以上條款可以看出,誘惑偵查本質上帶有欺騙性質,這也決定了其非法性,因此依據我國法律的規定禁止使用誘惑偵查手段。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往往對于偵查機關提交的在一定法律限度內的采用誘惑偵查手段采集到的證據予以接受。
境外很多國家采用誘惑偵查手段對一些案情較為復雜的案件進行偵查,如涉及買賣人口、制毒販毒、軍火交易、聚眾賭博案件的偵查,誘惑偵查發揮著重大作用。在國內,誘惑偵查手段尚未獲得法律的認可,即缺乏立法規范,也缺乏配套的法律解釋,因此誘惑偵查合法性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爭議的焦點。如果在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運用誘惑偵查手段不當,有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對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損害,侵害人權,導致我國刑事司法公正性發生偏頗。
三、誘惑偵查的類型
基于分類標準的不同,可將誘惑偵查劃分為以下幾種:
(一)主體的差異
因犯罪行為實施主體的差異,可將誘惑偵查劃分為:偵查人員實施的誘惑偵查和非偵查人員協助實施的誘惑偵查。偵查人員包括偵查機關工作人員,具體是指警察、檢察院以及其他享有偵查權的公職人員。非偵查人員包括受偵查機關領導的偵查人員之外的人,協助偵查人員或在偵查人員授意下實施誘惑偵查。因主體差異作出以上劃分的目的在于明確不同種類的誘惑偵查主體所肩負的義務。在涉毒案件中,偵查人員為了抓捕買賣毒品的犯罪分子,化裝成購買毒品的人,在毒品交易中將犯罪分子拘捕,這就是偵查人員實施誘惑偵查的典型案例。在行賄受賄案件中,檢察員通過對行賄人和索賄人交易地點的安排,對犯罪過程進行全程錄像和錄音,實現現場證據固定的目的,這就是非偵查人員協助誘惑偵查的典型案例。
(二)內容的差異
因為事實內容的差別可將誘惑偵查劃分為: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和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此種分類方式是在誘惑偵查獲得一定實踐經驗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礎上作出的,誘惑偵查手段不能對原本就不存在犯罪意圖的人進行,這也是誘惑偵查啟動程序的必要前提,因此啟動誘惑偵查只能以犯罪意圖的存在為前提,這就是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偵查機關針對已經實施特定犯罪行為或預謀實施特定犯罪行為的人,為其提供實施犯罪的便利條件和機會,引誘犯罪分子繼續實施犯罪,這就是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在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中,偵查機關采取引誘的手段致使受引誘人產生犯罪意圖并實施特定違法行為。啟動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前提是受引誘的人被偵查機關認定為犯罪分子,但是受引誘人并不存在犯罪傾向,犯罪行為的發生是在引誘手段下產生的,是偵查機關積極促成的。依據不同的內容對誘惑偵查進行分類,目的在于依據犯罪意圖的存在與否來判斷誘惑偵查的合法性,這也是定罪量刑的依據。嚴格來講,并不能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納入到誘惑偵查的范疇,它與美國警察圈套相似。依據法律的規定,誘惑偵查的前提是合法,而不合法的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不為法律所認可。
(三)偵查對象的差異
按照偵查對象是否明確的劃分標準,將誘惑偵查分為:對象明確的誘惑偵查和對象不明確的誘惑偵查。其中對象明確的誘惑偵查是指,偵查機關對特定偵查對象采取的誘惑偵查手段,偵查部門事前已經掌握了犯罪分子的部分情況和犯罪情節,如對涉嫌受賄行為的犯罪嫌疑人采取誘惑偵查就是典型的對象明確的誘惑偵查;對象不明確的誘惑偵查是指,偵查機關雖然已經掌握了案件事實和犯罪情節,但不確定犯罪嫌疑人,為了明確犯罪嫌疑人及時將其抓捕歸案而采取的誘惑偵查手段,如在涉嫌強奸犯罪案件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無法確定犯罪行為人,通過化裝引誘犯罪分子繼續實施犯罪,再施行抓捕,這就是典型的對象不明確的誘惑偵查。[1]
四、誘惑偵查的適用條件和范圍
我國現行立法尚未正式明確誘惑偵查的法律地位,所以關于適用誘惑偵查的條件和范圍我國法律同樣付諸闕如,在實踐中偵查機關只能參考其他偵查手段來判斷誘惑偵查的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2]在刑事司法活動中,適用誘惑偵查采集到的犯罪證據與其證明能力之間存在著直接關系,所以,檢察機關對于誘惑偵查的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往往較為謹慎,予以嚴格監督,避免誘惑偵查手段濫用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誘惑偵查的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可概括為:
(一)依據合理
1.4.6 歸一化積雪指數(NDSI) 歸一化積雪指數(NDSI)是提取積雪信息的一種有效方法,其算法較合理,分類精度高,具有普遍的操作意義。NDSI類似于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對大范圍的光照條件不敏感,對大氣作用可使其局地歸一化并且不依賴于單通道的反射,NDSI的計算公式:
依據一定的線索或證據,認定特定區域內或特定人存在發生犯罪案件或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但是證據不充足,因此偵查機關采取誘惑偵查手段對正在實施的特定的犯罪行為進行制止。
(二)案情較大
在自訴案件中,當事人依法享有訴訟權,司法機關機關因自訴人的告知才受理,司法機關直接受理此類案件。自訴案件往往涉及危害性不大,屬于輕微型的犯罪案件,基于偵查成本的考慮,采用誘惑偵查手段勢必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因此在普通行政案件中(包括誘惑執法案件)也采用誘惑方式進行案件偵查顯然是不合理的。
(三)選擇慎重
偵查部門適用誘惑偵查手段的必要前提是在其他刑偵手段已經無法發揮其有效性,選擇使用誘惑偵查要謹慎,避免一切發生危險、侵犯人權、有損社會風氣的可能。
(四)故意犯罪
針對故意犯罪案件的偵查選擇適用誘惑偵查手段,而不適用于過失犯罪。在過失犯罪中,對犯罪結果進行判斷,如果犯罪結果并未發生,即使實施了不當的行為,也不能認定行為人屬于犯罪,因此就沒有偵查的必要;犯罪行為人對過失犯罪行為往往承擔較輕的刑罰,犯罪行為人不會因為害怕承擔過重的刑事責任而逃避處罰,因此較為適宜采用普通的偵查手段。
五、誘惑偵查的程序控制
作為一種特殊的偵查手段,誘惑偵查必須經過合法性授權,這也遵循了我國法治建設的要求。不同的人對于誘惑偵查手段的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的判斷有所差異,因此為了避免誘惑偵查手段的濫用導致冤假錯案,應當建立起一套嚴格的誘惑偵查適用程序。[4]
(一)設立審批程序
誘惑偵查審批程序是指,在使用誘惑偵查手段之前,制作書面請示文件交由主管負責人、領導進行審批,獲得批準才能啟動誘惑偵查程序。書面請示的內容具體包括:適用誘惑偵查手段的條件、依據、理由。
(二)嚴格審查行動
審批的內容包括法律形式要件以及犯罪案件的性質。重視對犯罪案件性質的審查,將所有不具備適用的誘惑偵查行為的不當情節予以排除。
(三)及時終止執行
檢察機關對誘惑偵查手段的使用進行全程監督,包括事前準備階段和實施階段等全部偵查活動。如果發現誘惑偵查程序違法,或者存在引誘無犯意人員實施犯罪的可能,可以提出終止誘惑偵查的建議。
六、誘惑偵查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對于刑事案件而言,傳統的偵查措施往往具有滯后性,犯罪行為發生之后偵查部門依據部分線索對案件進行偵查。而誘惑偵查往往具有積極性,通過引誘存在犯罪意圖的犯罪分子繼續實施犯罪,在犯罪行為發生的同時展開偵查活動,獲取犯罪現場物證,及時抓捕犯罪嫌疑人,達到偵破案件的目的,提高了案件偵查的效率和準確性。另外,公民基于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對誘惑偵查手段形成認可,這也有助于誘惑偵查措施合理性的提高。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缺乏法律限制的誘惑偵查措施,勢必要引發負面作用。[5]
(一)憲法層面
我國憲法和法律基本精神為刑事訴訟行為的合法性提出要求。使用偵查措施偵破案件的前提是偵查手段的合法性,所有偵查行為均應當滿足合法性、正當性的要求。從本質而言,嚴格的訴訟程序是對權利的保護也是對權力的限制,基于強化權利保護和權力限制的目的,對法律作出調整和改革,可以說誘惑偵查的存在不符合法制進步趨勢,反而是法制的倒退,因此誘惑偵查不具有正當性。所有犯罪行為均是在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雙重激勵作用下產生的,對國家刑事政策加以規制,降低外界刺激引發犯罪的可能,通過合理的引導,使消極的犯罪動機歸于消滅,而不應當加強外部環境的刺激。
(二)刑法層面
在刑法領域,偵查人員實施誘惑偵查引誘犯罪分子繼續犯罪,從形式上來看雖然偵查人員也參與了犯罪,但是鑒于偵查人員特殊的身份,不能認定為共犯,這一說法無法獲得實體法共犯理論的認可。在刑法理論中,共犯可分為以下四種:實施行為、教唆行為、幫助行為、組織行為。其中教唆是指,采用引誘、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唆使他人實施犯罪的行為。在使用誘惑偵查手段過程中采用引誘的方式致使他人實施犯罪行為,這是否與教唆行為相同呢?不能以偵查人員的特殊身份而否定其共犯性質。若認定受誘人犯罪成立,則實施引誘行為的偵查人員也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應當受到相應的刑罰處罰。目前,國內司法實踐中還沒有出現偵查人員被認定為共同犯罪承擔相應責任的案例。
(三)刑訴及證據法層面
在我國刑事訴訟領域和證據領域,偵查部門采用誘惑偵查手段采集到的犯罪證據是否可以獲得司法機關的認可成為定罪的依據,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探討。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規定,采集證據的方式必須的合法的,任何采用刑訊逼供、利誘、脅迫、欺詐或其他違法手段獲得的證據都是非法的。在刑偵實踐中,往往允許適當的欺騙措施的運用,這也獲得司法領域和法學研究領域的一致認可,盡管對于證據使用和排除具有指導作用,但是缺乏實踐可操作性。另外,以欺詐、引誘手段獲得的口供不具有合法性,這受到我國刑法理論研究領域的認可,但是以欺詐、引誘手段獲得的物證是否合法的問題,法學界爭議較大。
七、結語
美國、英國、日本等法治發達國家已經構建起完善的誘惑偵查制度,并獲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逐漸發展成為穩定的判例制度,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認可,從而實現了從立法角度對誘惑偵查進行規制的目的,美國先后頒布了《關于秘密偵查的基準》和“索勒斯—謝爾曼準則”等。國內現行立法尚未對誘惑偵查予以明確,誘惑偵查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剛剛起步,尚未得到立法領域和偵查領域的足夠重視。現行法律規范的不足,直接決定著偵查機關在運用誘惑偵查手段中出現多種問題,如缺乏指導、缺乏可操作性等,不利于我國執法環境的構建。所以基于防止犯罪、建設和諧社會的目的,立法機關應當盡快建立起誘惑偵查規制體系。希望國內立法機關能夠積極尋找到恰當的實踐切入點盡快建立起誘惑偵查規制體系,提高偵查機關偵破案件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實現打擊系列性、組織性的犯罪、降低偵查風險的可能,防止誘惑偵查濫用引發冤假錯案,實現誘惑偵查的真正功能。
[1]鄔莉萍.賄賂犯罪適用誘惑偵查的問題研究[D].南昌大學,2012.
[2]王向陽.論誘惑偵查的價值取向及實踐保障[J].理論界,2009(03):100-101.
[3]張超.關于誘惑偵查的思考[J].法制與社會,2009(16):359.
[4]田園.誘惑偵查制度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08.
[5]侯秋哲.試論我國誘惑偵查制度的構建[D].蘭州大學,2008.
D925.2
A
2095-4379-(2017)29-0051-03
王強(1994-),男,漢族,浙江仙居人,浙江警察學院,2014級本科生,研究方向:偵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