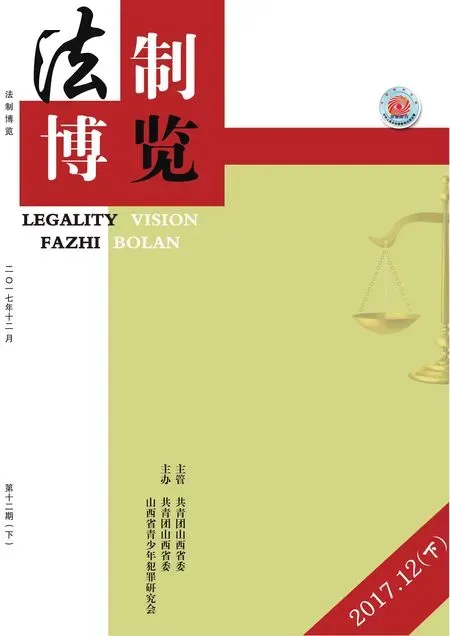《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與中國的選擇
葉雅冰
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與中國的選擇
葉雅冰
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對于保護糧食安全與農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然而,聯合國糧農機構發布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卻讓發達國家躊躇,發展中國家彷徨,包括我國在內的英美日等大國仍持觀望態度。基于條約在農民權益保護、糧農植物遺傳資源流通、分享糧農遺傳資源所生惠益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面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特性和法制現狀,綜合而言,我國加入條約,利大于弊。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農民權;資源流通;中國選擇
在世代農民的農耕實踐和專業育種者的科學培育下,作為眾人勞動與智慧的結晶的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對于保護糧食安全與農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顯然,聯合國糧農組織很早就意識到了糧農植物遺傳資源保護的重要性,歷經七年的修訂,2001年11月3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第31屆大會正式通過了《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一反過去無法律約束力的象征性條約管束,這份新條約是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文件。
截至2016年1月26目,條約的締約方已達137個國家,條約覆蓋的物種已包括水稻、玉米、大麥、谷類、高粱等3508個具有抗性的新品種,16個新社區種子庫建成,1120個作物品種得以保存,受益者達13萬人次,其中農民11.4萬人。[1]
然而,我國仍對《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持觀望態度。基于條約內容和發展前景,結合我國的主要顧慮,綜合而言,我國加入條約利大于弊。
一、農民權益保護問題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第5/89號決議》,農民權是指源自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農民在保存、改良和取得遺傳資源特別是原產地中心和多樣性中心的遺傳資源中所做出的貢獻被保護的權利。[2]
作為一種特殊的權利,農民權既不屬于單一農民個人,也不屬于農民集體。它被聯合國授予國際社會,由國際社會作為當前及未來世代農民的托管人對農民的權利加以保護,并通過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基金加以實施。
誠然,這種由國際社會居高臨下遠距離操作的保護方式,極易導致保護主體模糊化,使保護措施難以具體化,不具針對性。同時,國際社會也很難凌駕于各國主權之上對各國農民的權利加以干涉,使得保護初衷難以實現。
此外,大量發達國家的專業育種者,在發展中國家農民通過世代農耕獲得的良種培育經驗的基礎上,研制培育出轉基因、抗病蟲種子。他們通過知識產權制度,為其研制的新種子獲得專利保護,再將這些升級后的種子高價回銷給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使得農民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專業育種者的知識產權和非專業育種者基于多年勞作的經驗所應享有的權利難以平衡。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恰恰有效解決了農民權保護所面臨的兩大難題。它通過將農民權主體國家化和農民權內容具體化的方式,在肯定知識產權制度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農民的權利。
首先,條約將農民權的實現從國際層面轉入國家層面。條約規定各締約國有保護農民權的義務,要求各締約國切實建立法律框架,在本國法上強調并保護農民權利。同時,條約還通過“根據其需要和重點”、“酌情”、“依其國家法律”等限制性修飾短語,強調締約國的自主選擇權和與他國的協商權[2],使得農民權的保護因國而異,使得各締約國都可以針對自身的實際國情對農民權進行有效的具體的有針對性的保護。因此,在條約的保護下,農民權不再是國際社會手中攥著的虛權,而是真正被寫進各締約國本國法的實權。
其次,條約將農民權具體化為三個層面的權利,分別是:傳統知識的保護,參與分享惠益的權利和參與決策的權利。
在傳統知識保護方面,條約建立了特殊權利制度,即通過控制他人對傳統知識的使用,對農民權加以積極保護和不當利用制度,即通過阻止他人對傳統知識的使用,對農民權進行消極保護。在兩種制度的保護下,條約最大程度地在承認現有知識產權體制的基礎上,實現農民與專業育種者利益的再平衡。
在參與分享惠益的權利和參與決策的權利方面,條約9.2條(b)款和(c)款明確表示要保護農民“公平參與分享因利用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而產生的利益的權利”和“參與在國家一級就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保存及可持續利用有關事項決策的權利”。條約將農民作為實行主體,締約國作為第三方,通過將農民的權利具體化的方式,對農民權進行保護,完美符合各國的保護訴求。
二、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流通問題
與其他遺傳資源相比,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具有顯著的獨特性。首先,它屬于人造的生物多樣性形式,需要通過持續的人工保存和特殊養護才能保留;其次,它的散布具有集中性,多集中于“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緣種的原產地和多樣性中心”,使得針對原生境的保護尤為關鍵[3];其三,國家間對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賴性,不論是擁有豐富專業育種者資源,掌握新基因種存的發達國家,還是在世代農民的辛勤勞作下擁有豐富農地原生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對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無障礙穩定共享,都有極高的需求。
基于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特殊性,能否實現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無障礙穩定流通,一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而《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正有效地解決了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流通問題。
誠然,在條約訂立后,2010年10月30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條約第10屆締約國會議通過的《名古屋議定書》也對生物遺傳資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問題加以約束,我國也于2016年加入成為締約國。《名古屋議定書》確立的雙邊路徑雖然對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流通和保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也存在諸如談判成本過高,談判地位不對等,資源共享無法源源不斷[4],后續轉讓無法實現等問題。建立多邊體制,確立締約國向其他締約國提供獲取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義務,刻不容緩。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作為一份基于各國對農業可持續發展重要性一致高度認同的多邊協議,將保證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穩定與無障礙流通作為各締約國最主要的義務加以強調。
根據條約規定,各締約方有義務采取適當措施,鼓勵在其管轄下持有條約附件一所列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的自然人和法人將這些糧食和農業遺傳資源納入多邊系統;同時,條約的管理機構會在兩年內對未將以上資源納入邊系統的機構采取必要措施。條約強調各締約國“應迅速提供獲取機會,無需跟蹤單份收集品,并應無償提供;如收取費用,則不得超過所涉及的最低成本”。
無疑,條約在尊重知識產權和各國主權的基礎上為各締約國提供了有利于其糧農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副完美圖景,并通過《材料轉讓協定》有效解決后續轉讓的問題。
三、分享糧農遺傳資源所生惠益的問題
雖然條約所建立的惠益體制在實際操作中惠益尚微,但就其構成而言,條約的惠益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已趨完善。
條約的惠益體制主要由四部分組成:信息交流、技術獲取和轉讓、能力建設與分享商業化的貨幣惠益。
在信息交流方面,條約雖然對信息交流的廣度和深度都加以明確的肯定,但也通過“這些信息凡非機密性的均應提供,但須遵循適用的法律并依國家能力而定”,加以限定,使得條約在實踐中更宜被各締約國所接受。在技術獲取和轉讓方面,條約按照承認并符合充分、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的條件進行,提供了建立課題組或建立穩定的商業合作伙伴的方式,推進技術獲取和轉讓的穩定性,切實保護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利益。在能力建設方面,條約提出了制訂或加強科技教育和培訓計劃,開發并加強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保存及可持續利用的設施,與發展中國家及經濟轉型國家的機構合作,在這些國家開展科學研究,并在所需要的領域發展這類研究的能力等切實方案。雖均屬于建議性條款,無強制性和法律約束力,但也可見條約良好的發展預期。
四、中國的選擇
我國作為糧農遺傳資源大國,基于我國對糧農遺傳資源的保護現狀和《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的未來發展趨向,加入《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對我國而言,利大于弊。
首先,從我國對糧農遺傳資源的保護現狀而言,我國目前尚無一部統一的法律對植物遺傳資源的管理加以規制,只是任相關制度散見于各單行法、行政法規和規章中;與分散的立法狀況相應,我國也無單一機構集中行使對于質物遺傳資源的管理職權。此外,我國雖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專利保護制度,但就目前運行現狀而言,授權品種的所有者以公共科研教學單位為主,品種權轉化利用率低,科研人員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單薄,植物新品種流失嚴重。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窄,申請程序復雜,審查速度緩慢,維權困難。
其次,就條約本身而言,條約從根本上肯定了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穩定與無障礙流通的根本目標與農民權益的保護,根據如上三個角度的分析我們對于條約的未來發展與預期前景均可持一個樂觀態度。此外,條約也肯定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幫助,并可以為我國提供一個世界范圍的糧農資源共享庫。更為重要的是,雖然條約尚有些許不足和模糊之處,但加入條約,也是對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進一步確立,更有利于維護我國的權益。綜上,建議我國加入《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
[1]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ITPGRFA)介紹近期工作進展[J].世界農業,2016-03-10:193.
[2]張小勇.糧食安全與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法保障——<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評析[J].法商研究,2009(1):14.
[3]于燕波,王群亮,Shelagh Kell,Nigel Maxted,Brian Ford-Lloyd,魏偉,康定明,馬克平.中國栽培植物野生近緣種及其保護對策[J].生物多樣性,2013,21(6):750.
[4]徐靖,銀森錄,李俊生.<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與<名古屋議定書>比較研究[J].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13,14(6):1099.
D922.6
A
2095-4379-(2017)36-0059-02
葉雅冰(1997-),女,浙江溫州人,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2015級法學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國際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