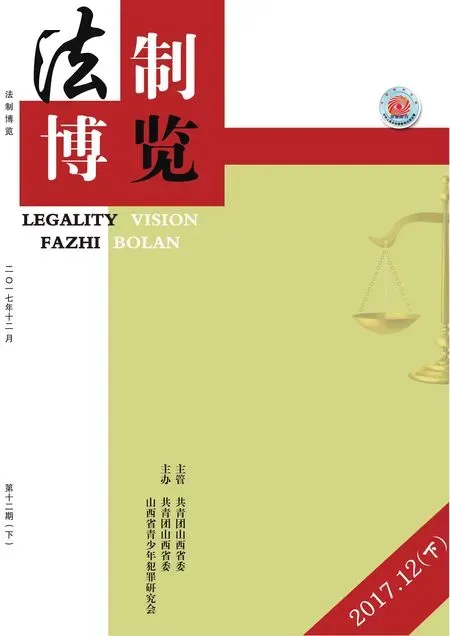淺論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在銜接和協調方面所存在的困境
李湘玄
中共武漢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校,湖北 武漢 430000
淺論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在銜接和協調方面所存在的困境
李湘玄
中共武漢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校,湖北 武漢 430000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政黨法治化取得了許多成果,然而,作為政黨法治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國家法律體系和黨內法規及制度體系在銜接和協調方面還存在規范沖突、調整范圍界限模糊、缺乏全方位細致的違憲查糾機制等困境,要實現兩者有效的銜接和協調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們之間的磨合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這需要一個不斷積累、摸索轉進的過程。
國家法律;黨內法規;銜接;協調
政黨法治化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我國政黨法治體系主要包括國家法律體系和黨內法規及制度體系,前者是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則,后者是管黨治黨建設黨、促進黨內治理法治化的基本依據和制度載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緊密結合,出臺和修訂了一系列黨內法規,這些成果為我黨法治化建設打下很好的基礎,即使如此,黨內法規體系和國家法律體系就并行不悖、彼此協調統一了嗎?
當然,面對“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總書記很早就作過回答,他指出:依法治國和黨的領導是高度統一的,法必須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愿的統一體現,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其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也就是說,黨的主張與憲法法律體現的人民利益是一致的,“黨大還是法大”根本是一個偽命題。然而,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在具體問題上還存在銜接和協調的困境,本文將試圖進行梳理。
第一,國法與黨規存在規范沖突的難題。當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在銜接上遇到規范沖突時,如何執行將成為困境。國法與黨規沖突一般只會發生在黨內,涉及黨員、黨組織和黨務等事項,它面臨一個選擇適用的問題。以黨員為例,具有公民和黨員的雙重身份,必須同時受憲法、法律、黨章和其它黨內法規的約束,而我黨在黨內法規建設上力度很大,標準很高很嚴,“黨紀嚴于國法”,“紀律挺在前面”,因此,在執行時發生規范沖突在所難免。如在審查貪腐黨員案件時,紀委依據的處分規范常常會與公民人身權,特別是人格尊嚴權受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產生沖突,反腐具有現實的合理性,黨員貪腐更應該被嚴懲,不言而喻,這是否就意味著黨員的身份必須就要主動放棄其作為普通公民應享有的一部分權利和自由?而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了我國公民具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基本權利,這是否意味著黨內法規違反了憲法呢?拋開“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黨規和國法沖突既不利于維護黨規的嚴肅性,也不利于維護國法的權威性、統一性。
第二,國法和黨規調整的范圍界限模糊。黨和政府為了強化責任,高效辦事,有時會通過聯合發文的方式來迅速有效地解決國家和社會改革、治理中出現的問題。黨政聯合發文在制定主體、內容形式以及文件名稱等方面并不符合黨規的規范要件,在制定的法定程序上又不符合行政法規和規章,具體歸為其中一類均不合適,只能稱為規范性文件。在具體實踐中,黨政聯合發文經常涉及大量的行政事項,其效力往往等同甚至高于法律法規,這類文件一般由黨委法規工作機構負責審核和審查,容易引起規避行政性文件備案審查的嫌疑,黨委法制工作機構其處理這類文件的備案審查能力往往有所欠缺,這類文件的備案審查已陷入模糊地帶。雖然中辦在《關于建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銜接聯動機制的意見》中提出要建立一系列機制和制度,要求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但是,黨政聯合發文的備案審查主體責任還是不夠明確,仍然需要“進一步明確哪些由黨委進行備案審查,哪些依法由人大常委會實施,哪些由政府負責”[1]。聯合發文是為了更高效解決有關改革方面的問題,卻造成了現實存在的國法和黨規調整范圍的界限及備案審查主體責任的模糊不清,這種重“效率”、重“權威”、輕“法治”的現狀與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要求,與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三,國法和黨規缺乏全方位的、細致的違憲查糾機制。我國現行《憲法》在序言部分就要求,各政黨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這個規定卻是原則的、抽象的、籠統的,沒有與之對應的具體完善的憲法實施的法律機制,也缺乏健全的憲法監督制度和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即使《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作為黨內立法法的基本法,也多為原則性的規定,缺少細節性的制度。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是為了確保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同黨章及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一致,與憲法法律一致而制定的,它的適用范圍卻相對有限,僅適用于中紀委、中央各部門和省委制定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這如何全方位無死角地保障憲法至上原則的落實?又如何維護黨內法規及制度體系的統一性和權威性?
當然,有人會辯解,我國在國家法律體系層面通過立法法建立了立法監督體系,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方面,通過《備案規定》建立了事先審核和事后備案審查相結合的監督體制,這難道不是全方位的違憲審查機制?然而,在現實中,當黨內法規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甚至與憲法相抵觸時,處理起來就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從國法來看,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法定的程序,受理審查要求和建議,依法對其進行審查處理,但受我國目前的政黨關系和法治環境的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徑自審查處理黨內法規有難度,也不現實。二是由人民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也很困難,現實中就存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向法院起訴要求其確認黨內規范性文件違法的情況,法院一開始只能以無管轄權為由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專門作出批復,指出該類案件不屬法院主管的范圍,法院不應受理,告知當事人向其它有關部門申請解決,即便該批復后來被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所代替,但黨委仍然只有在極其少數的情況下才可以比照國家機關,成為民事訴訟主體,可以說,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及違憲違法問題的處理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很難成功。
從黨規來看,《備案規定》對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共涉及六項內容,其中審查處理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是否同黨章等上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相沖突、是否逾越了黨內組織權限等事項屬于黨務工作,有權執行。但是,中紀委、中央各部門和省級黨委是否有權作出相關決定,認定某條黨內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違憲呢?這在理論層面還有待探討。根據我國憲法,認定一個規范性文件違憲,必須要經過相應的憲法規范程序對其進行糾正或撤銷,我國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享有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僅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解釋憲法的職權。盡管我國憲法和法律是在黨的領導下制定的,也盡管處理違憲問題最終必須體現和維護黨和人民的意志,但違憲審查過程“必須恪守法定職權和程序,不能破壞憲法確定的國家權力秩序”[2],因而,“從國家法治建設的角度看,黨內法規審查和備案機構是不能行使此項權力的”[3]。再者,從審查機構自身的專業角度看,“黨內法規備案審查機構對涉及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內容,也明顯存在知識儲備不足,審查經驗欠缺等方面的實際問題。”[4]所以,單從國法或黨規的某一方面考慮違憲違法問題都會在實施過程中遇到困境,因此,《備案規定》提出建立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和國家法律備案審查銜接聯動機制,但是,據有關實踐,這種雙方的備案協作機制在組織形式上,主要是通過開會、發函件等方式進行溝通協調。但是,這種協作銜接形式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多現實性問題,比如單向溝通多,多方互動少;偏重于臨時性的溝通協調,缺少穩定的例行性會議交流;隨意性有余,穩定性不足等等,由于有效的穩定的溝通協調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預期的制度合力也就難以實現。
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同屬治國理政的規范性依據,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個規范體系的銜接和協調是貫徹黨中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保依法執政、科學執政的現實需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然而,實現國法與黨規的銜接和協調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不斷積累、由量變到質變的探索提升過程,需要執政黨、相關國家機關以及其他社會成員共同持續推動,合力織緊扎牢“制度的籠子”,筑實法治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李適時.全面貫徹實施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二十一次全國地方立法研討會上的總結[J].中國人大,2015(21):12-17.
[2]秦前紅,蘇紹龍.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銜接和協調的基準與路徑——兼論備案審查銜接聯動機制[J].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6(5):21-30.
[3]張曉燕.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頂層設計研究[J].理論學刊,2014(1):19-25.
[4]胡勇.建聯合審查機制筑合法合規屏障[J].黨內法規研究,2014(2):57-59;李忠.黨內法規建設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D262.6;D920.0
A
2095-4379-(2017)36-0067-02
李湘玄,武漢大學,碩士,中共武漢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校,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