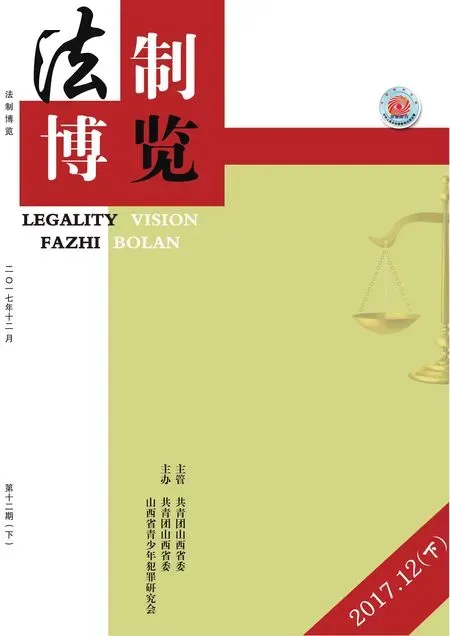論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的舉證責任
王小剛
河北地質大學研究生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論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的舉證責任
王小剛
河北地質大學研究生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環境侵權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在邏輯上存在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被告的舉證責任,以至于在很多侵權案件中,被告方承擔了本不該其承擔的不利后果。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指導意見,規定原告承擔列舉“初步證據”的責任,但對初步證據的認定,證明標準和方法仍缺乏明確規定。
環境侵權;舉證責任;初步證據
一、環境侵權案件中原被告舉證責任的現狀
在曲某和某公司一案中,就原告曲某的舉證責任,最高院認為:曲某提供的勘驗記錄顯示,在該公司的廠房內有黑煙冒出,附近氣味刺鼻,且周圍再無其他鋁制造企業,證明了該公司存在排污行為;曲某種植的櫻桃葉片枯萎,果實普遍猥瑣干癟,產量下降,證明了原告曲某確實受有損害。除此之外,法院認為,在曲某提交的檢測報告中可以看出,距離廠房越近的櫻桃受損害程度越高,且根據原環境保護局規定的關于保護農作物的大氣污染物最高標準,廠房排放的含有氟化物的物質會對櫻桃產生影響。因此法院認為,結合上述表述,原告完成了就櫻桃損失與該公司的排污行為之間具有關聯性的舉證責任。
從法院的裁定中,我們可以看出,原告除了需證明被告存在排污行為和在排污期間自己受到損害,存在損失之外,還需初步證明這種排污行為會造成原告所受損害的可能性。
二、環境侵權案件舉證責任倒置存在的缺陷
(一)邏輯上的缺陷
根據正確的三段論推理邏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大前提是常態關系,比如在一般情況下吃過期的食物會造成腹瀉或者食物中毒,比如攝入一定量的甲基汞化合物會導致水俁病。這是一種常態,以至于通常情況下只要有事實A出現,就可以推定事實B也會出現。而小前提則是具體的案件事實,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就是,被告實施了排污行為,原告受到了損害,小前提可稱之為一種基礎事實。
據此,面對環境侵權案件,若嚴格按照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也就是僅僅根據存在排污行為和損害后果(小前提)就得出結論,是欠缺大前提的,因此是不科學的。與環境侵權中的這種舉證責任倒置的舉證責任分配相似的是“間接反證法”,單純的“間接反證法”也是存在邏輯上的不嚴密性的。事實上,在很多環境侵權司法判例中,法官也意識到這種缺陷的存在,并采用了與之不同的因果關系推斷方法。[1]
在日本,著名的水俁病案和四日市哮喘病案,法官就采用了不同的證明方法。在水俁病案中,法官援用“間接反證法”,認為存在排污行為與村民換水俁病兩種基礎事實,便可證明其兩者間存在因果關系。而在四日市哮喘病案中,法官認為僅僅就被告存在排放粉塵行為與被害人患有哮喘病兩種事實,還不能將敗訴的后果施加給被告。原因就在于,根據當時的醫療技術表明,造成恐怖的水俁病的病因,只有“甲基汞”,而被告排放的污水里就大量含有甲基汞,作為常態關系的“大前提”已經存在,因此法官援用“間接反證法”,如果被告舉不出證據證明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則判決被告敗訴。與水俁病病因明確不相同,哮喘的病因則有很多,除了煙塵,二氧化硫之外,還跟個人習慣以及生活地域等等因素有關系,大前提并不存在,因此法官并未援用“間接反證法”,而是引用了另外一種名為“疫學統計”的方法。[2]
(二)對被告施加了過重的舉證責任
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案件事實不明確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環境侵權訴訟中,采用舉證責任倒置或者間接反證的方法,基本就是將這種不利的風險全部轉由被告承擔。嚴格按照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要求被告承擔證明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責任,對于被告來說是很困難的。被告要證明原告得白血病與自己的行為沒有因果關系,光指出其家族有白血病史或者其受到過核輻射是不足夠的(即使原告方的確是因為這兩種原因患了白血病),被告還需要證明自己的行為在生物學上,醫學上,甚至心理學上都不會在此種情況下導致白血病的發生。事實上怎么可能呢?
三、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提供“初步證據”的理解
(一)“初步證據”的性質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環境資源審判工作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利司法保障的意見》中指出,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除了要對存在排污行為和受有損害承擔舉證責任外,還需提供損害與污染行為存在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據”。次年,最高院發布的關于審理環境侵權案件的司法解釋第六條提出:被侵權人承擔有證明排污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存在“關聯性”的責任。筆者認為,“關聯性”是相比于“因果關系”而言較弱的一種聯系狀態,其說明被侵權人無需嚴格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但負有提供相對較弱證明力,也就是“初步證據”的責任,其存在是為了證明一種“可能性”,而非為了證明“確定性”。如德《水利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原告承擔的證明其為“合格的”污染物的責任,即除了已經造成污染的現狀,還需要證明該污染物具有造成“特定的”損害的可能性。
(二)采用“初步證據”的優勢
首先,原告承擔列舉“初步證據”的舉證責任,對被告來說,有了繼續維權的途徑和可能性。采用“初步證據”以后,被告如果不能阻斷其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就并不一定承擔敗訴后果。其可以通過推翻推定因果關系成立的常態關系以及基礎事實來達到同樣的證明目的[3]。因為采用因果關系推定的前提是原告完成了他的舉證責任,如若原告提供的大前提小前提連“可能性”都證明不了,那理應由原告承擔敗訴后果。
再次,原告對常態關系和基礎事實的舉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確保因果關系推定的可靠性。由原告承擔“初步證據”的舉證責任,即增加了大前提的證明,使因果關系推定在同時存在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情況下行使,這樣的話,除非極個別特殊的情況,否則不會出現推斷錯誤,彌補了原來舉證責任倒置的邏輯漏洞。
四、因果關系“初步證據”的證明
(一)因果關系“初步證據”的證明標準
首先,關于“初步證據”的證明標準,首先我們要明確我們的立場:適當分配給原告可以充當常態關系的證明責任。所以初步證據的要求不宜過高,不需要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高度蓋然性標準,而只需要其證明“可能性”即可。
其次,雖然不需要承擔高度蓋然性標準的舉證責任,但原告對其列舉的“初步證據”起碼要達到證明的效力。稍稍具體的說就是“初步證據”要能證明污染行為具備能夠造成具體的損害的物理或者化學或者醫學上的特性。
(二)因果關系“初步證據”的證明手段
1.官方文件認定
如果官方對某個特定的問題已經有前例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文件得以保存的話,毫無疑問可以作為證明因果關系“可能性”的證據。例如日本水俁病一案中,法院之所以能夠直接適用“間接反證法”,就是因為日本當地政府有科學文件認定甲基汞是致使水俁病的唯一病因。
2.疫學統計方法
疫學統計法,是一種醫學方法,主要研究某種疾病在特定區域,特定人群中患病比例的方法,來尋找病因。并總結群體性疾病與自然因素,群體因素的關聯性。這種方法并不按照嚴格意義上科學推理,而是依賴的經驗法則。
我們以一則經典環境侵權的案例來討論疫學統計方法的應用價值,在曲某訴該公司一案中,曲某提供的證據包括了借以證明距離廠房越近的殷桃葉片含氟量越高的鑒定結論。法院認為,該鑒定結論與勘驗記錄,鋁廠生產過程中會產生氟化物,植物葉片含氟量對大氣中的氟化物反應敏銳等科普資料以及大氣污染物最高允許濃度國家標準相符合印證。因此法院結合其他案件事實,認為原告舉證充分,推定曲某所受損害與該公司排污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1]王社坤.環境侵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檢討[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5,15(06):02-04.
[2]日本律師協會.日本環境訴訟典型案例與評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3]薄曉波.論環境侵權訴訟因果關系證明中的“初步證據”[J].吉首大學學報,2015,38(05):01-04.
D923
A
2095-4379-(2017)36-0172-02
王小剛(1994-),男,漢族,江蘇南通人,河北地質大學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然與資源保護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