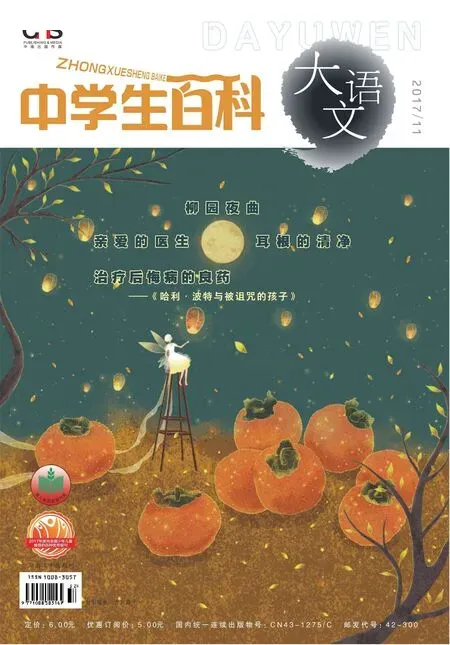高密東北鄉的紅高粱
文丨邱楠
高密東北鄉的紅高粱
文丨邱楠
“八月深秋,高密東北鄉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在那片樸實的黑土地上有瓦藍的天空,有明媚的陽光,有神奇瑰麗的村莊,有對那片地愛得深沉的人們,當然,還有那大片大片的紅高粱……
莫言,就像那大片紅高粱中的一簇,秋風拂過,便隨風搖晃,很快湮沒了身影。的確,他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他是一位世界級的作家。然而褪去光環與盛名,他便是一個凡人,是一個被樸實無華的土地滋養過的凡人。
兒時的他和許許多多人一樣,在中國北方的那片土地上度過了貧窮苦澀的童年。五六歲的他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他的每一天都在饑餓中度過。沒有糧食,他只有吃野草,啃樹皮,甚至還吃過煤塊。那時村里拉來一車裝滿煤塊的煤車,他便和小伙伴們跳上煤車,一人拾起一塊亮晶晶的煤塊,放入嘴中嚼起來。那時的他已分不清味道的好壞,只要能放入嘴中填飽肚子的便是好的。少年時代的饑餓讓他看到了那個年代中國農村的真實現狀——饑餓,貧窮,艱苦。正是那段平凡而又真實的童年,他才能在小說中將舊社會的農村完完全全地反映出來。
除了饑餓,還有孤獨,同樣使他刻骨銘心。“文革”時期,因為“富裕中農”的家庭成分,少年的他便一直遭受排擠,在那個普遍貧窮的年代,富裕的人家便是“剝削者”“地主階級”,是十惡不赦的罪人,是要遭受大家的批斗,要下鄉進行勞動改造的。因此,年少的他便隨家人下鄉放牛去了。在那雜草叢生的荒原上,只有幾頭牛與他做伴,他便只能一個人望著天空自言自語。正是這段平凡卻孤獨的日子,讓他擁有了天馬行空的想象、神奇美妙的念頭。這或許便成了他日后創作的不竭源泉。
或許和那個年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對知識有著熱烈的追求。兒時的他便十分喜愛讀書,那時的農村,書籍是十分罕見的,誰家中能有一本書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時的他為了看書,便一家家去借,有一次為了借鄰居大叔一本帶圖的《封神演義》他磨破了嘴皮,最后幫人家磨了一上午面,才獲得了寶貴的兩個小時的閱讀時間。那時的他站在自家門前借著煤油燈的光亮看書,看到忘我之時連頭發燒著了都不知道。
他就是在農村生長的萬千孩子中的一個,邁過了艱苦的饑荒時代,跨過了殘酷的“文革”時期,終于,他找到了自己的閃光點——寫作。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從《白狗秋千架》到《蛙》,他的高密東北鄉,他的紅高粱家族,他所鐘愛的那片凈土,都在他的筆下被世人所知。在他的作品中,有對時代的反映,有民間習俗歷史文化,有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當他一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文學也從此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然而,褪去了光環他依舊是凡人。是個樸實無華的人,是一個對故鄉有著深厚情感的人,是一個在中國最樸實的土地上成長的凡人。
八月的深秋,高密東北鄉的黑土地上有著大片大片的紅高粱,而莫言,便是那片紅高粱中生長得最熱烈的一株。
點評
莫言在“三農”人物頒獎典禮上娓娓道來:“我在農村長到20來歲入伍,在部隊也是生活在農村的環境里,此后每年花大量時間在農村寫書。我跟農村,尤其是我的故鄉有著密切的、切也切不斷的聯系。”言語間流露著對家鄉濃濃的情感,而從他筆下的故事里,亦能窺見他對鄉情的傾訴與對農村的熱愛。高密的剪紙、泥塑、年畫、茂腔,這些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著農村的一種精神狀態和審美傾向,在他的作品中直觀而生動。他說:“我的藝術風格離不開鄉土。”對他而言,留在農村或許不是因為本分,也不是因為難忘,最多的應該是依靠。他將根深深地扎在農村,茁壯成長,在時光中枝繁葉茂。正如他所言,莫言其實真的是個農民,是個會講故事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