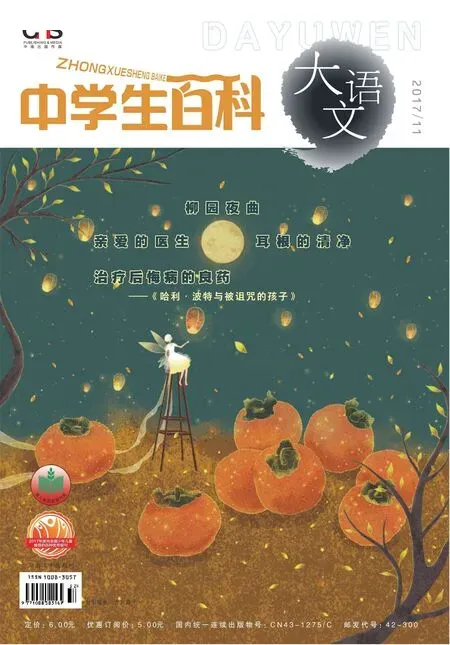回不去的故鄉還是烏托邦?
——對農村發展的一些思考
文丨風泠
回不去的故鄉還是烏托邦?
——對農村發展的一些思考
文丨風泠
■千人一面最是無趣,參差多態乃幸福本源。一個話題,千種聲音,一切有趣想法和鮮明觀點都可以在這個互動平臺上恣意發聲。觀點激蕩、錯落紛雜之態,即我們智慧萌芽之時。
最近,北京一位高考狀元的耿直之語讓“寒門再難出貴子”這一事實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這番討論,讓我想起這幾年的春節期間,一些高學歷的完成蛻變的“寒門貴子”在公眾平臺書寫的故鄉隨筆。這些隨筆的內容大概有以下幾類:第一,對農村落后于城市的生活環境的不適及感嘆;第二,對農村人的日常生活娛樂的現實“鄉村化”與記憶中不同而感嘆;第三,對農村發展的嘗試與對農村建設的艱難的感嘆。無論內容如何,我看此類文章時印象最深的是“回不去的故鄉”。
農村,在諸多從農門跳出的學子貴子眼中已經成為回不去的故鄉了。大體原因有二:一、農村與城市的生活環境差異讓已經適應了城市生活的學子、貴子們難以再長期忍受農村的生活環境。這也許可以調侃地說成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這類差異的形成實際上是因為農村與城市客觀存在的巨大的資源差異,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非物質上的。二、嵌入在農村與城市生活中的社會關系與社會規則的差異讓“寒門貴子”們難以再嵌入農村社會中。“寒門貴子”的工作與日常生活的交往都已經融入城市生活中,他們接受并履行著城市生活的社會關系交往規則。城市的社會規則是現代化的、個體化的、有機的,而農村的社會規則是傳統的、家庭化的、機械的。兩者相互排斥。所以,很多從農村到城市打拼的青年與中年們都在感嘆,農村是回不去的故鄉。當然,這里面不能忽視的另一層現實就是客觀存在的農村衰敗。畢竟,農村人都到城市打工了。
然而,在我國的江南水鄉,潺潺流水環繞著農村社會的烏托邦,它們被稱為中國的新農村。這些村莊我們并不陌生,小學、中學課本上都有它們的身影,最有名的就是“華西村”。每每從新聞報道上看到這些村莊時,我腦中都會浮現出同學和我說起的一個令人“心酸”的玩笑,這種“心酸”來自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兩極差異。她的大學室友說自己家庭條件不好,是農村的。后來才知道這個室友家里住別墅,出門開小車,正是來自“華西村”。她說家里條件不好也是真的,不過這是相對村里其他家庭來說的。然而,誰能夠說家家戶戶住別墅,出門開小車的農村是回不去的故鄉?這種花園式的農村不僅是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理想模式,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烏托邦啊:有田,有錢,有閑。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像華西村這樣的超級村莊并不是中國農村的群像,而存在于人們記憶中的“回不去的故鄉”才能代表中國農村的基本群像。因為,華西村太少,而故鄉太多。
農村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
農村其實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的概念。在現代化或者“發展”的概念中,農村其實最終會走向消亡。法國社會學家有一本經典著作叫《農民的終結》,既然農民都會終結,那么農村如何不會消亡呢?
然而,在這本書出版后的幾十年里,農民不曾終結,農村也依舊存在。與其說農民終結,不如說農民的生活方式終結。如今的農村發展,不論是國家政策上的含義,還是學者的概念中,農村發展的一個指向就是“城市”的模式。因為,在現代概念中發展的最終目標的理想類型也是“城市”模式。所以,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積極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這是其治理績效的有效體現。
說到這里,還是需要一個轉折。雖然有政府積極推動農村發展,推動城鎮化建設;但是,農村建設與發展依舊面臨著不少問題。
第一,農村生計缺乏。中國已經從農業社會邁入工業社會許久,農業生產可以維持農村居民溫飽,但是難以讓農村居民致富。農民通過生活經驗體會了這句話,學者通過理論推斷出了這句話,這已經成為共識。尤其是在社會急速轉型與發展的今天,農村生計缺乏是農村社會發展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致富的概念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先富帶后富”“小康生活”的各種自上而下的宣傳深入人心,致富的現實需求通過各種生活資料的商品化不斷推動著人的致富心理。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在國家因為城市工業發展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下,戶籍管控逐漸放松了。缺乏生計的農村居民渴望致富,渴望邁向小康生活,因而紛紛進入城市工作,由此誕生了中國經濟奇跡的締造者——農民工。
農村生計的缺乏,并不是農村的生產活動不能養育農民,而是農村的生產活動不能滿足不斷“進步”的生活標準。因此,農村居民大量外流,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
第二,農村發展主體的缺位。農民工為中國工業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但是農村的勞動力結構卻發生了質的改變。每年一度的《中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告訴我們,農民工并不是農村被解放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是年輕力壯的盛年勞動力,怎么會是“剩余”,農村留下的勞動力才是“剩余”,因為他們被稱為“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老人,也是我們常說的三留守群體。這類常住農村的群體被學術界稱為“在地主體”。這些主體是目前農村發展的主要群體、主要參與力量。他們為農村發展做出的貢獻體現在不斷提升的農業女性化趨勢,不斷提升的農業老齡化趨勢,事實存在的兒童勞動現象上面。
農村發展主體的缺位,不僅體現在農村建設的主體參與不足上面,更體現在社會層面的留守群體的困境。農村老人的養老、農村婦女的勞動、兒童的失學與安全問題,都是目前存在卻沒有能夠解決的“大”問題。這些問題有如燙手山芋,讓各地政府掩耳盜鈴,不愿正視。不是他們不想解決,而是因為目前條件下難以完全解決。最終,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是落在農村家庭自己身上。因為農村的未來,誰也看不見。
田園式愿景與農村消亡論
目前關于農村發展的討論與思考,學術界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一種觀點認為農村必將消失,一種認為農村未必會消失,還是有諸多可能的發展道路的,得不斷挖掘華西村等“田園式愿景”的存在和推廣可能。認為農村必將消亡的流派積極鼓動政府規劃農村資源以補充城市建設;抱有“田園式愿景”的流派積極動員政府、社會各界力量進行農村社會的重建。
現在的農村建設有很多成功案例,尤以珠三角、長三角為多。這里面有個不得不承認的現實資源界限。縱觀蘇杭地區、東莞地區的農村建設,成功的客觀基礎不外乎有二:第一,農村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或經濟能人。這個經濟能人通俗點說,就是村子里有“有錢人”。第二,農村具有一定的社會聯結基礎。比如家族、風俗習慣等,讓“有錢人”和“村民”有故土難離、回鄉定居、改造鄉村的愿望與需求。而第一點更為重要。因此,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與發展的問題一致,即資源問題。
農村建設的再思考
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農村建設其實是一個治理的問題。那么,農村社會的治理目標是什么呢?
社會學中,關于社會治理這一基本問題討論的核心是“如何解決與民生福祉相關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通俗地講就是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公共資源由誰來提供,以及如何提供。
放到農村社會衰敗的今天,農村社會治理的目標又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不僅僅是為農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而且是如何讓衰敗和渙散的農村重新煥發生機,這包括農村群體的回流,而不是三留守群體的駐守基地;足夠的農村生活的基本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供給,讓農村居民可以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即重建農村社會秩序,農村社會可以支持農村居民的在地家庭再生產。
對于當今農村社會治理的問題,得弄清楚,要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物品供給,做到什么樣的公共服務,讓生存變成生活。因此,農村社會治理的目標在筆者看來,任務艱巨且影響深遠。
其次,現有的農村社會治理路徑和范式是怎么回答農村資源的供給問題的?
現有的農村社會治理路徑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政府主導”模式,主要通過發揮政府的力量,直接由政府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資源提供者。政府是農村社會治理的唯一或主要治理主體。二是“社會主導”模式,主要通過發揮社會力量,在政府力量有限的情況下,由農村社會既有的宗族或外部社會組織的介入,讓社會力量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主要資源提供者。三是“多元治理”模式,主要是政府搭臺,社會唱戲。政府通過政策傾斜,積極號召社會力量在其規劃下為農村社會治理提供資源和力量。
筆者認為現有的農村社會治理范式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從農村社會內部進行“國家—社會”關系的探討,農村內部力量是農村社會治理的主要力量;二是從農村社會外部進行“社會—社會”關系的探討,農村外部力量是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推動力量。
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總結出村莊類型與農村社會治理路徑的匹配模式,即還沒有能夠歸納出如何通過村莊發展狀況水平的差異匹配治理路徑,選擇資源提供的方式。
再次,從歷史和社會變遷的脈絡中看農村社會的發展和衰敗。
在城市社會學研究中,有一個理論是人文生態主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繼替”。該理論認為城市發展類似生物界的繼替規則,從無到有,通過競爭繼替形成現在的城市空間分布形態。這是一個既定的社會規律。在這個概念下,如果將農村看作一個必然衰亡的過程,那么農村社會和其秩序的重建是繼替中另一輪生態循環的建立過程。從歷史的角度去看農村社會的歷史興亡交替,比截面地看待農村社會治理更能發現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社會基因,也更能應對農村發展的挑戰。
最后,農村社會治理的方向可以何為?
費孝通等中國早期社會學家在探索中國社會學發展道路時就提出在中國社會結構下探討中國的發展問題,并形成了一大批的中國社會歷史調查成果,在今天看來仍然有許多建議具有啟發性意義。筆者認為從中國歷史社會的變遷脈絡中,在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農村社會關系變遷的基礎下,去討論農村社會發展,可能會給農村社會治理帶來新的發現和思考。比如,宗族的力量如何嵌入農村社會治理的脈絡中?中國農村社會發展之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到底是何種位置和現狀?
筆者也是農村出身,對農村社會有著極大的感情,因為那里的風土和人情造就了我。對于農村的未來,筆者認為不太樂觀,但仍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