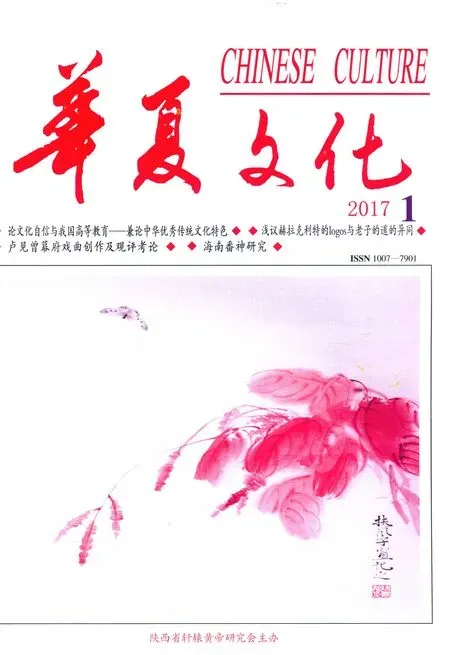《莊子·至樂》篇思想淺析
□ 崔 幸
《莊子·至樂》篇思想淺析
□ 崔 幸
《莊子·至樂》篇屬于述莊派的作品,述莊派是莊子后學中的嫡派。從文章的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來看,述莊派的作品是外雜篇中年代較早的一類。這一類作品的主要特點是繼承和闡發內篇的思想,對莊子的思想也有所改造和發展,然而沒有重要突破,基本上是述而不作的。述莊派作品是研究莊子思想的主要參考資料(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63頁)。
前人對該篇的研究或從美學思想的角度闡發莊子至樂的人生境界(張靜《由“虛室生白”到“至美至樂”——莊子美學思想略論》,武漢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祁志祥《“自適其適”“至樂無樂”莊子美學新探》,《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或探討莊子“逍遙”、“自由”的精神追求與至樂的人生體悟之間的相互聯系(黃克劍《〈莊子·至樂〉髑髏寓言抉微》,《哲學動態》2015年第8期;劉笑敢《莊子之苦樂觀及其現代啟示》,《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趙桂萍、陳引弟《論莊子的快樂觀》,《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或比較莊子與孟子關于“樂”的思想,從思想來源和方法上探討莊子至樂思想(張瑞《淺論莊子的“至樂”思想》,海南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在莊子的研究專著中,如崔大華的《莊學研究》,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以及陳鼓應《老莊新論》(修訂版)等,亦有對《至樂》篇思想的相關探討。本文主要著眼于莊子思想與其生活及所處時代背景的關系,揭示該篇中所體現的“至樂”、“無為”、“無君”思想以及莊子的生死觀。
《至樂》篇以該篇首句二字“至樂”為篇名,篇中主要討論如何對待人生快樂和生死態度的問題。至樂,意為至極的快樂。《至樂》篇分為七章。第一章從開頭“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到“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談人生有沒有至極的快樂。其中連續五句提問,列舉并批判了世人(富者、貴者、壽者、烈士)對苦與樂的看法,并且指出從來就沒有什么真正的快樂。“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所謂至樂也就是無樂。第二章從“莊子妻死”到“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寫莊子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忘卻死亡之憂的故事。篇中借莊子之口,說明人的死生猶如氣的聚合與流散、四時的更替。第三章從“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丘”到“我又何惡焉”,講支離叔與滑介叔“觀化”,天地間無時不在變化中。死生如晝夜,如萬物的變化,人只能順應這一自然變化。第四章從“莊子之楚,見空髑髏”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介紹莊子與空髑髏對話的寓言,借助髑髏之口寫出人生在世的積累與勞苦。第五章從“顏淵東之齊”到“名止于實,義設于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借孔子之口,講述了魯侯養鳥的寓言故事,認為人為的強求只能造出災禍,一切都應當任其自然,“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第六章從“列子行食于道從”到“予果歡乎”,寫列子見髑髏而有所感言。指出人的死生都不值得憂愁和歡樂。第七章從“種有幾”到“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描述物種的演變。萬物從“機”產生,又回到“機”,人也不例外。照應第一章人生在世無所謂至樂,人的死與生也是一種變化而已。
《至樂》篇中議論了莊子生死氣化的理論,有三個要點:一、生命不是本來就有的(“察其始而本無生”),而是逐漸演化形成的。二、氣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形體生命都是氣凝聚的結果。三、有生則有死,生死變化是自然而然的,人死即回歸大自然(“偃然寢于巨室”),因此是不應該悲傷的(第二章)。《至樂》篇中莊子認為死生本身是屬于自然性質的大限,是一種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必然性,他稱之為“命”。“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段(第四章)及“‘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行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第五章)。在莊子看來,命運的安排,如同“容小不能懷大,繩短不可汲深”,都是無法改變的。“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愍愍,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哀樂之情是人與生俱來而不可避免的。“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當人把死生的觀察視角從人本身移到超越人的個體之上的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時,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或者說被超越了,從而對死生的不同情感(界限)也就不再存在。莊子對死亡有一種樂觀放達的態度,這種態度的理論基礎就是認為人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死亡即回歸于大自然。
《至樂》篇第五章孔子與子貢的對話,講魯侯養海鳥的寓言,魯侯“以己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結果把鳥養死了。這則寓言是莊子對當時統治者采取批判態度的一種反映。暗指統治者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人民,從而造成眾人的災難。因而主張為政之道,要使人民“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與此同時,莊子表達了這樣的愿望——無君無臣的自由生活最為快樂。第四章,莊子與空骷髏對話的寓言中:“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的無君思想,雖缺少理論闡述,但作為情感,表現得非常鮮明強烈。莊子社會批判思想是立足于自然主義的,矛頭直指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的主要體現者——君主制和儒家,無君之國最樂。這則閑適超脫中透出凄然重負情調的寓言故事,揭示構成人生困境“生人之累”的政治、經濟、道德和人的自然生理本身等多方面因素。它把死亡當作對人生困境的超脫,對“生人之累”的解除,認為在一個自由的、無任何負累的“至樂”生存環境中,“無君于上”是第一個條件。這則寓言故事實際上包含著、表現著對現實社會的真實洞察和尖銳批判。
莊子認為天地萬物在本性上都是無為的。“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作為萬物之一的人,其存在方式、行為方式也應是無為,即順任萬物之理而不為不作,人的無為來自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源。因而就人性而言,無為才是符合和保持人的本性。“吾以無為誠樂矣”,清靜無為才是真正的快樂。從較高的、哲學本體論的角度來看,莊子順世態度也是得“道”精神境界的一種自由表現。“萬物皆化”,“化”是“道”的存在特征,是順世態度的本質的內涵(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頁)。
《至樂》篇第七章,“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透過廣博的經驗知識和真切的觀察描述,揭示生物的演變過程,說明了萬物雖然有形態上的差異,但在最后的本質上是相通的、相同的。“萬物皆化生”,肯定萬物是密切聯系的,萬物間的界限是相對的、暫時的。在對具體事物相對性的認知方面,則認為萬物存在都是相對的,即“萬物殊性”與“萬物皆一”之間的相對。“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機”是對人生理本質的解釋。“氣”是充盈、彌漫于宇宙間的唯一的、本身無形體卻能構成具體物質形態的一種存在。因而,人的生命、肌體在本質上是“氣”的聚合、變現,是順應自然演化的普遍過程。
莊子的一生是在困苦艱難的逆境中度過的。他對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都是極度不滿和失望的,認為自己是生活在一個“士有道德不能行”(《莊子·山木》)的社會里。他比較清醒地認識到個人在自然和社會中的地位,這種認識具有哲學的理性態度,承認世界的客觀性與非目的性(劉笑敢《莊子之苦樂觀及其現代啟示》,《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但是他只能認識到人被自然和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一方面,而不能理解人同時也能創造自然和歷史的另一方面。他擺脫逆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將其痛苦的實際感受,消解在人是處在無限浩渺的宇宙中和永恒時間長河霎時的哲學體驗中。他對于精神上的超脫,來自他對個人的人格獨立和精神的絕對自由的追求。這種追求就是要人的精神從人與自然的界限中、從社會的世俗觀念中、從自我的情欲中跨越出來,進入一種無任何負累的、無任何對立面的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他站在一種超脫世俗感情的、冷峻的理智立場,用徹底的自然主義觀念來思考,用對人的自然本質的理智推究來抑制人的社會性的行為和情感。莊子對人生哲學的思考發端、立足于個人在社會生存中的“困境”,探討如何從困境中超脫出來,構成其人生哲學的基本方向和內容。
(作者:北京市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郵編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