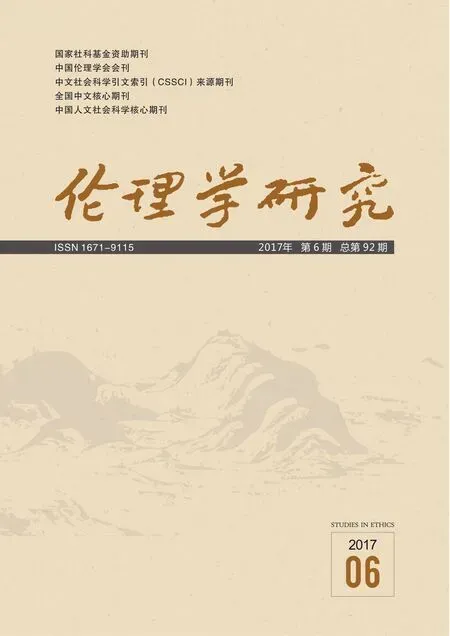家庭倫理、家庭分工與農民家庭的現代化進程
張建雷
家庭倫理、家庭分工與農民家庭的現代化進程
張建雷
在當前農民家庭的經濟生活實踐中,家庭倫理同農民家庭的現代化呈現出了有機的“親和”關系。家庭倫理是傳統儒家倫理在農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現,它提供了農民家庭經濟活動的基本規范,并賦予農民的經濟行動以意義,從而形塑了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在這種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中,農民家庭根據不同成員在家庭中的關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經濟結構。這使得農民家庭能夠充分利用市場機會,合理配置家庭勞動力,以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時,這也奠定了農民家庭現代化的基礎。在家庭繼替的過程中,隨著家庭財富在代際之間的有序傳遞,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實現現代化的財富積累。
家庭倫理;家庭分工;半工半耕;家庭繼替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隨著倫理經濟學的興起,道德倫理觀念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強調和重視。倫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經濟活動中的諸種倫理制度和規則,亦有學者將倫理看作是滲透在經濟活動之中的一種特殊因素,強調經濟活動本身所內涵著的倫理價值[1]。在此方面,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關于文化價值同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經典命題。韋伯認為,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和”關系,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發展[2]。在韋伯分析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基于東亞模式的崛起,探討了儒家文化同經濟發展的關系,強調了儒家倫理對東亞企業精神的重要影響[3-4]。其后,另一些研究進一步關注到了儒家倫理及其具體的倫理規則對華人企業組織的影響[5-6]。不過,整體上看,這些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更多地集中在華人精英群體身上,而缺少對普通人日常經濟生活的關注。
斯科特曾對東南亞農民的日常經濟生活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在以生存作為目的的農民經濟活動中所蘊含的道德含義,即農民的道德經濟,強調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互惠觀念等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對小農經濟生活的基本保障[7](P1-15)。結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以及農耕文化傳統,斯科特的這一觀點似乎更能解釋我國農民經濟的基本現實。但問題在于,斯科特所指出的農民經濟的道德含義,更多的是作為生存保障的“公正”、“平等”觀念等外在的社會規范,而非農民生活中內在的儒家倫理規則。
因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以及至今仍是以農業人口為主體的國家,儒家倫理對農民的日常經濟活動有著何種程度的影響?形成了何種對應機制?尤其是,在當前高度市場化的條件下,其內在的機制是否發生了新的變化?
二、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
家庭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共同體。在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中,通過男系的血脈綿延,每個人都處在“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這一祖先和子孫一體的關系中,這賦予了中國家庭生活中豐富的倫理意義[8](P44)。這種祖孫一體、延續香火的觀念,并由家擴大到家族的無限延續性,也被認為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是維系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沒有中斷的重要力量[9]。因而,家庭倫理構成了傳統儒家倫理在農民日常生活領域最基本的倫理形態。作為維系農民家庭生活的基本倫理規范,家庭倫理既體現了對個體如何做人、處理家庭關系、過好日子等制度性和規范性要求,同時也規定了農民家庭生活的基本任務,并賦予其以意義。
具體而言,家庭倫理主要體現在家庭關系之中。家庭關系又主要包括兩個基本層次:縱向的代際關系和橫向的夫妻關系,即《儀禮》所說的“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其中,代際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核心,構成中國農民家庭縱向延續的基礎。正如許烺光所曾指出的,代際關系是中國社會親屬關系的中心,其他所有的關系都是代際關系的延伸或補充,或是從屬于代際關系的[10](P94)。或言之,夫妻關系作為代際關系無限延續的一環而獲得其價值,由此,也可以說是“妻與夫齊體”,即“妻的人格被夫所吸收、夫的人格由妻所代表”[8](P143)。因而,在此意義上,家庭中的成員并不是僅僅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個體而存在,而是生活在既定的家庭關系之中,是作為父親、母親、子女、丈夫或妻子而獲得其社會身份和自我認知。
不同家庭成員的身份角色被賦予了相應的義務和行為規范。究其根本而言,這是由家庭倫理所決定的。雖然眾多的學者均指出,在我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使得傳統家庭倫理的形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如在一些地方的農村,農民傳宗接代的倫理意識已經極為弱化,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深入人心[11-13]。不過,總體來看,農民家庭中以代際關系為核心的基本倫理精神仍得以延續[14]。為人父母者,仍必須要盡心竭力地為子女著想,勒緊褲腰帶供養子女讀書,操持子女的婚姻大事,為子女的未來積極籌劃,或用農民的話說就是要不斷地“操心”,為子女“操心”,為整個家“操心”。相應的,子女則要為父母盡孝,即尊親、贍養,這是身為子女最基本的倫理義務。正如《孝經》中所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由此,家庭中的每個成員均基于其特定的身份和角色被賦予了相應的責任,即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承擔責任,對家庭整體的延續承擔責任,或如梁漱溟所說“恒只見對方而忘了自己,慈母每為兒女而忘身,孝子亦每為其親而忘身”[15](P87)。這又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繼”的倫理,二是“養”的倫理[16]。“繼”的倫理主要包括家系的繼替和祖先的祭祀,這也包括家庭財產的繼承,這是家庭倫理之根基。“養”的倫理主要包括子女的養育和父母的養老,并以父母的養老為核心,這是家庭倫理的基本要求。“繼”和“養”共同構成為農民家庭倫理的核心要義。
這種以“繼”和“養”為核心的家庭倫理觀,提供了農民家庭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即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禮儀[17](P35)。同時,這也規范了農民家庭的經濟活動,并賦予農民的經濟行動以意義。這主要體現在農民家庭財產的積累和傳遞方式上。家庭財產是農民家庭經濟生活的基礎,在家庭再生產的每一環節都離不開家庭財產的支撐,如撫育子女,并供養其讀書,為兒子蓋房、娶妻,為女兒籌備一份豐厚的嫁妝,贍養年邁的父母,并為故世的父母舉辦體面的葬禮,這均需要花費大量的財物。因而,中國農民家庭的經濟活動并不僅僅是以滿足基本的生存(消費)需求為目的的,而是深受家庭倫理的規約。為完成基本的倫理義務,中國的農民總是積極地爭取每一筆收入,并小心地節約著每一筆開支,以最大程度地積累家庭財產的總量。
此外,在家產的積累過程中,也體現著家產繼承的內容,即家庭財產的積累還是為了讓子代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因而,分家析產也是農民家庭經濟生活的題中之義。在分家析產的過程中,所體現的家庭財產的縱向傳遞也構成為子代家庭經濟生活和家庭財產積累的基礎。惟其如此,方不失其為人父母的本色,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而對于子女而言,子代對家產的繼承,同時體現為子代對父母的義務,即為父母養老送終。由此,在家庭的代際傳遞過程中,就呈現出了“繼中有養,養中有繼”的基本形態。
因而,在家庭倫理的規約下,農民家庭的經濟活動體現出了鮮明的倫理化特質,這也可以稱之為以倫理為本位的家庭經濟組織或家庭經濟組織的倫理化。中國農民家庭的這種獨特的經濟組織邏輯,也根本不同于經典理論對農民家庭經濟組織的解釋。已有的關于小農家庭經濟組織的解釋,主要有兩種視角,一種可以稱之為理性小農視角。此種觀點認為,作為理性的個體,農民的經濟活動同樣體現出了經濟理性的邏輯,即其經濟活動的基本動機在于以有效的要素配置,實現利潤最大化[18](P32-46)。在此意義上,農民家庭就相當于一個高度理性化的現代企業組織。另一種觀點可以稱之為生計小農視角,該觀點認為農民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其經濟活動的基本動機在于滿足家庭(生存)消費需求,并深受勞動辛苦程度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家庭消費需求的滿足程度和勞動辛苦程度之間的基本均衡[19](P41-62)。
在中國農民的家庭經濟組織中,一方面農民參與經濟活動的基本動機在于滿足家庭消費需求,但這些消費需求并不僅僅是生存意義上的生物性需求,而更是家庭倫理的義務。另一方面,中國農民的經濟表現也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精打細算,厲行節約每一筆不必要的開支,積極爭取每一份額外的收入,表現出了高度“理性”的經濟面向。但這種“理性”的經濟表現更是以倫理為本位的,其動機在于最大程度地積攢家庭財富,并為子代家庭的延續打下較好的經濟基礎,為此,他們同樣會不計成本地投入勞動。因此,農民家庭的經濟活動似乎更符合斯科特所說的“道德經濟”的含義。不過,鑒于中國農民家庭生活中的倫理本位特征,筆者認為,“以倫理為本位的家庭經濟組織”的解釋更符合中國農民家庭經濟的現實。
三、家庭倫理與農民家庭的市場分工
在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中,根據不同家庭成員的勞動力稟賦和身份角色的差異,形成了農民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在傳統農業經濟時期,農民家庭分工的最基本形態表現為“男耕女織”,即家庭中的男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婦女則主要從事家庭紡織業以及家務勞動,由此,以實現家庭勞動力最充分的利用和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以及家庭再生產的延續。不過,由于傳統農業時期,這種“男耕女織”的農民家庭經濟往往僅能勉強維持溫飽水平,這通常被視作我國傳統小農經濟封閉、落后的典型形態,并被認為是我國傳統農業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20](P261-265)。但客觀來看,傳統時期農民家庭經濟的貧困,更多的是由于傳統小農農業的有限剩余,工商業市場沒有形成,以及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的剝削等外在原因所導致的,而非這種倫理化家庭經濟組織的內在特征。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穩步推進以及市場經濟的全面興起,這為倫理化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
眾多的學者均指出,當前農民家庭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經濟結構,即農民家庭中一部分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另一部分勞動力留守在農村務農[21]。農民家庭的這一經濟結構出現于1980年代初期,隨著該時期鄉鎮企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年輕的農民進入工廠打工,但他們家庭中年紀較大的父母仍在村里務農。另由于務工地點是在本鄉鎮范圍內,離家較近,因而,這些年輕的農民也可以利用下班或休息的時間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這也被稱之為“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家庭經濟模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制度上對農民流動的限制性條件的逐步放開,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離土離鄉”進入城市務工。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速,更是形成了億萬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進城務工的高潮,并且,他們在進城務工的同時仍保留了小塊土地上的農業生產,這就基本形成了當前農村中較為普遍的農民家庭“半工半耕”結構。
從家庭分工的角度來看,當前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結構首先是一種社會分工,體現出了農民家庭中的倫理關系本質,即農民家庭根據不同成員在家庭中的關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其家庭成員或進入城市務工,或留守在農村務農。具體來看,這又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一是以代際關系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即農民家庭中年輕子女外出打工獲得工資收入,年齡較大的中老年父母則留守在家務農,并照顧孫子孫女的讀書和生活。二是以夫妻關系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即農民家庭中的男勞動力外出務工,已婚的婦女在家務農,照顧小孩和老人。
在第一種類型中,農民家庭的分工主要表現為代際分工,這是農民家庭代際之間倫理關系在經濟上的體現。對于父代而言,子代家庭是父代家庭的延續,幫助子代順利實現家庭再生產及早日實現更好的生活,是父代家庭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是在子代成家以后,父代仍要竭盡所能地為子代家庭的發展提供幫助。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子代家庭成立的初期,尤其是在孫子或孫女出生以后,一方面小孩的成長需要大量的經濟支出,這往往需要父代的直接援助。另一方面帶小孩也需要大量的時間,若由年輕人來帶,這勢必會影響他們外出務工的機會,若是有父母幫忙(帶小孩),則年輕人可以放心地外出務工。并且,此時期父母往往勞力尚可,能夠完全負擔起務農勞動,年輕的子代也無需在農忙季節返鄉幫忙務農,可全年在外務工。在第二個時期,隨著留守在農村務農的父母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勞動能力日減,但他們仍能完成農業生產中相對較為輕松的田間管理任務,并照顧已長大的孫輩們的讀書生活,在外務工的子女僅需在農忙季節返鄉務農即可。
在第二種類型中,農民家庭的分工主要表現為夫妻分工,是農民家庭中夫妻關系在經濟生活上的表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農民家庭的婚姻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婚姻關系的倫理本質并沒有根本改變[22]。生育子女,并撫養其成人、成家,仍是建立婚姻關系的基本目的之一,并構成夫妻關系和夫妻分工的基礎。在這一分工結構下,由于父母年事已高或已經過世,撫育幼代,照顧其讀書,并做好農閑季節的田間管理工作的任務就落在了婦女身上,其丈夫作為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則進入城市務工,以掙取更多的家庭收入。但在農忙季節,丈夫則必須要返回農村務農,以完成該時期較繁重的生產勞動任務。不過,隨著子女逐漸長大成人,結婚生子,這種以夫妻關系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亦開始向以代際關系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轉變。
從經濟的角度看,在農民家庭的上述分工結構中,通過合理地配置家庭中的勞動力資源,有利于農民家庭充分地利用市場機會,實現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并保障家庭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通過家庭分工,農民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男勞力),即有著較強市場競爭能力的家庭成員,進入城市中的務工市場以掙取更多的工資性收入。家庭中的次要勞動力(婦女和老人),即在務工市場中競爭能力較弱或缺乏競爭力的家庭成員,則留守在農村務農,并撫育幼小,完成家庭再生產的任務。由此,不同勞動力稟賦和身份角色的家庭成員均得以充分發揮其勞動能力,實現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價值,同時,這也使得農民家庭可以獲得務工和務農兩份收入。務農收入可以滿足農民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時,農民的家庭農業通常還結合家庭養殖,如飼養雞、鴨、豬等家禽,這主要是為了提供滿足自家消費所需的肉、蛋等食物,以改善家庭生活。外出務工的收入則主要用于家庭積蓄,通過逐年務工收入的積累,農民家庭便可以積少成多,逐步完成蓋新房、籌辦子女婚事、為父母養老送終等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人生任務的財富積累,實現家庭再生產。
這就使得在當前農民家庭的經濟生活中,務工和務農收入,相輔相成,相互補充。一般而言,若一個農民家庭中,主要勞動力因傷殘、疾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外出務工,家庭的收入來源中僅有小塊土地上的務農收入,則該農戶通常就可以歸入最貧困的農戶群體之中。不過,若是農民家庭中,僅有務工收入,而沒有務農收入,這也會對農民家庭的經濟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這意味著該農戶的家庭消費失去了自給的基礎,而完全是市場化的,這就必須從務工收入中預留出家庭消費的市場開支,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外出務工農戶及他們留守在農村的家人的生活成本。在當前農民務工工資水平仍較為有限的情況下,這顯然會構成對外出務工農民的沉重負擔。因而,務工和務農構成支撐農民家庭經濟的穩定的兩柄拐杖,二者缺一不可。
在此意義上,當前農民家庭中以倫理為本位的家庭分工結構,表現出了較高的經濟效能。這既提供了農民參與經濟活動極強的動力和意義,也穩定地支撐了農民家庭收入的增長和家庭財富的積累,并構成農民家庭經濟發展的基礎。
四、家庭繼替與農民家庭的現代化進程
家庭財產的積累也構成農民家庭延續的前提。家庭延續是農民家庭最基本的倫理任務,這主要是通過分家來完成的。分家指的是通過分生計和財產,子家庭從母家庭中分離出來的狀態和過程[23],這也是一個新家庭的產生,即家庭繼替的過程[24](P182-197)。根據農村社會的傳統,只有經過分家,子家庭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家庭。具體而言,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的分離,即子代同父代相分離。二是家產的析分,即“父母將財產傳遞給下一代……年輕一代獲得了對原屬其父親的部分財產的法定權利,對這部分財產開始享有了專有權”[25](P59)。其中,家產的析分是農民分家的核心內容,本質上,這體現了家庭財產從父代向子代流動,子代繼承父代財產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子代也同時繼承了相應的倫理義務,即父母生前的奉養、死亡時的喪葬和死后的祭祀,滋賀秀三稱之為傳統孝道倫理的三樣態[8](P121)。在此意義上,誠如滋賀秀三所指出的,父子是分形同氣的,“父親和兒子既是在現象上的分開的個體,又是在本源上的一個生命的連續,……祖先的積蓄當然由作為其生命之繼續的子孫來享受。在另一方面,伴隨著子孫的發達當然由作為其生命之根源的祖先來享受的這樣的關系。這些享受在老了之后是子的奉養在死了之后是子孫的祭祀。”[8](P122)因而,在家產析分的過程中,所體現的是繼和養的統一,是農民家庭倫理精神的基本體現。
不過,從家庭財產的流動上看,代際之間的資源流動并不是對等的,相較于子代所繼承于父代的財產而言,子代所能反饋給父代的資源是極為有限的。如前所述,父母之于子女,有著近乎無限的責任和義務,即使是在子女成家及分家之后,父母們仍要不斷地辛勤勞作,力所能及地為子代分憂,盡可能地使子女們過上更好的生活。通常是在自己徹底不能勞動的情況下,父母才會真正需要子女贍養,但等到此時,早已年老體衰的父母們也已日薄西山了。這意味著,對于父母而言,其整個一生所創造的財富,都已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子女。正是基于對父代財產的繼承,子代得以有能力獨立開始新的家庭生活。
在傳統農業時期,子代所繼承的家庭財產主要是土地和房屋。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實行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消滅了土地的私有制,家產的范圍縮小,作為生活資料的住房成為子代家產繼承的主要內容。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其父母終其一生所創造的財富仍極為有限,子代家庭所繼承的土地和房屋主要是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用于滿足基本生存需求。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家庭財產的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農民貨幣收入的增加,家產中貨幣財產的份額增大,住房和貨幣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財產。當前,在農民家庭中,子代所繼承的家庭財產更多地是以貨幣化的消費品為體現的,如在兒子結婚時,父母通常要建好一棟高大漂亮的現代樓房,并配備一套完備的現代化家具和家電設備,或直接到城市中買房,一些較為富裕的農民家庭通常還要給兒子和兒媳婦添置一輛小汽車,在兒子結婚后這些自然就成為小家庭自己的財產。此外,父母們通常還要給兒媳婦準備好數萬元不等的彩禮,以作為小家庭生活的基礎。這總計約需要農民家庭花費幾十萬元的貨幣支出。
雖然,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年輕的農民通過進入城市打工,有了獨立積攢財富的機會。但是,從當前農民家庭的現實生活來看,這些財富大多是由父母所創造的,并歷經多年的辛苦勞動和勤儉生活積攢而成。這是由于,當前農村中在外務工的年輕農民,其所掙得的工資收入,很少能積攢下來。在年輕人的生活中,他們更愿意體驗現代城市生活的豐富多彩,結交朋友,消費高端的電子產品,購買光鮮亮麗的衣著,其所得工資多只能維持日常的消費。這只有到了他們結婚生子之后,開始獨立地承擔家庭責任,面臨家庭的日用開支、小孩子的生活和讀書費用,他們才有了積蓄的意識,并開始像此前父輩們一樣,為下一代的生活而更加努力地掙錢,積蓄家財。
由此,在家庭繼替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中國農民家庭獨特的發展模式,即農民家庭代際之間的接力式發展模式。如前所述,在當前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結構下,其家庭收入獲得了穩步的增長,父代家庭所逐步積累并傳遞給子代的財富總量也在不斷增大。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財產在代際之間的每一次傳遞,都伴隨著農民家庭(以子代為主)生活水平的顯著提升。
因此,在家庭繼替的過程中所形成的這種接力式發展模式,形塑了中國農民現代化的獨特路徑。這可歸納如下:農民以家庭為單位,通過代際之間的財富累積和傳遞,父代逐步為子代積累了現代化的資本,從而推動并加速了子代家庭的現代化進程。
五、結 語
在當前農民家庭的經濟生活實踐中,家庭倫理同農民家庭的現代化呈現出了一定的“親和”關系①。家庭倫理是傳統儒家倫理在農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現形態,它提供了農民家庭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規范了農民家庭的經濟活動,并賦予農民的經濟行動以意義,從而形塑了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在這種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中,農民家庭根據不同成員在家庭中的關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其家庭成員或進入城市務工,或留守在農村務農,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經濟結構。這使得農民家庭能夠充分利用市場機會,合理配置家庭勞動力,以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因而,當前農民家庭中以倫理為本位的家庭分工結構,表現出了較高的經濟效能。同時,家庭財富的積累也奠定了家庭延續的基礎。在家庭繼替的過程中,隨著家庭財富在代際之間的穩定傳遞,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實現現代化的財富積累,有序步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
上述討論充分表明,在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現階段,儒家倫理不僅對企業組織和企業精神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在微觀層面上,也構成農民家庭發展的基本動力及價值基礎。在以倫理為本位的農民家庭經濟組織中,儒家倫理的延續與現代化的轉型有機地契合在一起。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農民家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并不一定要拋棄既有的文化傳統,儒家倫理的延續將能夠有力地推動其現代化發展。
[注 釋]
①韋伯曾用“選擇性親和”來表達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韋伯的意圖在于分析新教倫理的世俗禁欲主義是如何促成了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成。不過,在韋伯看來,這種親和性關系并不是一種因果關系,因而不可理解為“新教倫理產生了資本主義精神”,而只能理解為一種耦合關系。韋伯對“親和”用法似乎更符合生物學的表達,即物體之間性質相近,可以相互包容。在此意義上,本文采用韋伯的這一分析策略,將農民家庭同市場的關系理解為性質相近,可以相互包容的“親和”關系。
[1]章海山.略論倫理經濟[J].倫理學研究,2006(1).
[2]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金耀基.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重探[A].中國社會與文化[C].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4]單世聯.韋伯命題與中國現代性[J].開放時代,2004(1).
[5]S.B·雷丁.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與風格[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
[6]楊光飛.家族企業、家族愿景與華人家族企業的內部治理[J].倫理學研究,2010(1).
[7]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M].程立顯,劉建,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8]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M].張建國,李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9]麻國慶.永遠的家——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0]許烺光.祖蔭下[M].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
[11]吳俊,郭志民.家庭倫理傳統的嬗變與當代價值——第4屆海峽兩岸倫理學研討會綜述[J].倫理學研究,2005(1).
[12]李桂梅.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及其啟示[J].哲學研究,2011(4).
[13]賀雪峰,郭俊霞.試論農村代際關系的四個維度[J].社會科學,2012(7).
[14]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人贍養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3).
[1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6]張建雷.分家析產、家庭倫理與農村代際關系變動——一個浙北村莊的社會學詮釋[J].中國鄉村研究,2015(12).
[17]吳飛.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8]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9]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20]黃宗智.明清以來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卷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21]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上)[J].讀書,2006(2).
[22]李桂梅,鄭自立.改革開放30年來婚姻家庭倫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倫理學研究,2008(5).
[23]麻國慶.分家:分中有繼也有合——中國分家制度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1999(1).
[24]費孝通.生育制度[M].上海:三聯書店,2014.
[25]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張建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農村社會研究中心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