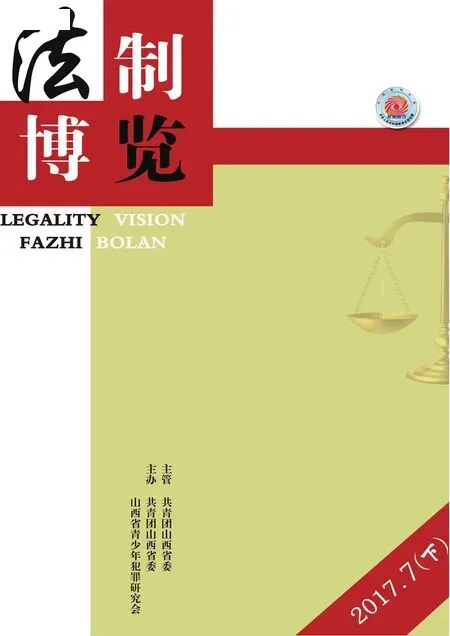我國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研究
吳琳科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北京 100088
?
我國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研究
吳琳科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北京 100088
本文以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為指導思想,以公立高校特別權力關系為例,在對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內部管理關系違法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說明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并對特別權力關系向一般權力關系轉變提出相應的立法建議。為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法律糾紛的解決提供法律依據和有效的解決途徑,完善我國法制體系。
特別權力關系;一般權力關系;法治化
一、引言
眾所周知,圖書館罰款制度是圖書館管理中的重要一環,有44.4%的讀者認為,罰款制度通過否定個別違規讀者財產權的同時,保障了多數人對圖書館資源的占有和享用,對創建規范有序的圖書館文化具有深遠意義。對于我國高校圖書館而言,其罰款權的制定和實施由于缺乏法律依據和監督,常常由我國高校(圖書館)單方面制定并強加于讀者,讀者無權提出異議,只能認罰。近年來,隨著大學生法治觀念的增強,強烈的維權意識促使大學生對高校圖書館某些管理制度開始提出質疑,高校與學生之間矛盾滋生,不利于和諧校園的建設。
二、特別權力關系理論概述
我國近現代意義上的公立大學的創建于19世紀末期。受大陸法系法治觀念的影響,我國公立高校與學生基于內部管理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具有鮮明的特別權力關系色彩。因此,探究我國高校圖書館與學生之內部管理關系的性質,應尋根溯源。
(一)特別權力關系概念
所謂“特別權力關系”,最早是由德國行政公法學者Otto Mayer所構建的,它是與“一般權力關系”相對應的受公法調整的特別法律關系。“特別權力關系”中的“特別”主要是指特別限制的意思,絕非特別優待之意,也就是說特別權力關系中權力與義務相較于一般公民權利義務更加受限制,故又可稱為“特別權利義務關系”。特別權力關系是指特定領域內中,特定主體與特定相對人發生的特別適用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我國的公立高校與其在校就讀的學生的關系、我國的公立醫院與在該院就診的病人的關系。
(二)特別權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一般認為最早出現于德國19世紀時,由Paul Laband所倡導,以此來說明官吏對國家的勤務關系。在Paul Laband之后,Otto Mayer確立了現代行政法意義上關于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主要概念,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確立了特別權力關系在德國的重要地位。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對二戰前的各國,尤其是日本和民國時期的中國臺灣影響深遠。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強調官員服從義務與其軍國主義思想相契合,因此成為日本行政法學重要構成部分。民國時期的臺灣,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由日本傳入,臺灣行政法學者進一步擴大了其適用范圍,對當時臺灣行政法學說和實務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戰后,民主法治思想和人權保障理論廣泛傳播并得到各國認同。戰后西德,針對特別權力關系排除法律保留的范圍和在此范圍內所作的處分是否排除司法審查兩方面問題進行了探討,自Carl Hermann Ule提出司法救濟的適用標準“二分法”之后,1972年德國憲法法院在監獄服刑案中做出判決,否定了先行的特別權力關系范圍內沒有法律根據而限制個人基本人權的行為,引入了法律保留原則。而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又將法律保留延伸到公立高校事項中,即對涉及法律賦予學生的基本權利的“重要事項”,作為權力主體的高校無權加以限制,否則,高校構成違法,應受司法審查。
三、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罰款的合法性
調查顯示,學生讀者主要通過新生入館教育對圖書館的罰款制度做到了基本了解,但是該制度并沒有得到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全體讀者認可。雖然有6.5%的人對圖書館罰款制度非常滿意,20.4%認為基本滿意,但是“不是很滿意”和“不滿意”的比率也占到了74.1%。針對不滿意的原因,有67人認為該制度設定和實施程序不合法,占到了整個調查對象的62.0%,有36.1%的人是由于該制度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因素,說明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已成為讀者不滿意該制度的主要原因。同時,在經過對108位讀者的調查中,發現有82人都有過被罰款的經歷,其中,被罰款1-2次的有72人,占到了66.7%,3-5次的占到了8.3%,表示從未被罰款的僅有26位讀者。
經查閱我國法律法規及我校各項制度規定,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罰款由圖書館和校方自主制定的管理制度。高校圖書館作為高校的常設機構,受高校本身法律地位的影響。由此可見,判斷高校圖書館罰款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首先必須確定我國高校是否具有行政主體地位。根據我國《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有關規定,可以看到我校作為公立普通高校,僅可以在招生、對學生進行處分、頒發畢業證書等特定范圍內成為法律授權的行政主體。圖書館作為普通高校的內設機構,雖然其在開放過程中進行管理,但是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的相關規定,其管理范圍僅限于對館藏實體資源和網絡虛擬資源在內的文獻信息資源,即使在對這些資源進行科學管理維護的過程中,會涉及對讀者借閱書刊行為的管理,這些管理在性質上也僅屬于內部管理,不屬于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因此,雖然高校被授予一定的“行政自主管理權”,但就圖書館罰款而言,并不屬于授權“自主管理”的范圍。
可以看出,盡管高校圖書館罰款制度合理性體現在圖書館管理過程中的方方面面,在現實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我國當前法律制度和理論下,圖書館依然沒有對讀者進行罰款的設定權和實施權。因此,引入修正后的特別權力關系解讀“行政自主管理關系”,為圖書館罰款權的設定和實施提供理論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特別法律關系
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所產生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究竟是什么呢?經調查,有28.7%的同學認為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是具有領導和管理的行政法律關系,有26.8%的同學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特殊的教育關系,由于對“特別權力關系”這一概念的生疏,認為高校與學生之間是特別權力關系的寥寥可數,僅有11.1%。在我國法學理論界,雖然關于高校與學生之間基于內部管理權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尚無一定論,但是不可否認,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存在特別權力關系因素,其具體表現在:
第一,高校與學生實際地位不平等。在實踐中,我國高校依據法律授予的“行政自主管理”權進行內部管理的過程中,具有主導和支配地位,有命令、強制及處罰之權,而學生作為被管理者只有服從遵守的義務。
第二,我國高校學生義務不確定。根據法律授權,為保障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等方面的權利,以及學術教育等相關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國高校往往單方面制定內部管理規章。在肯定內部管理規章合理性的同時,也應看到,由于高校片面強調自身權力,忽視“民主管理”,可以隨時加重學生作為或者不作為的義務,因而,導致我國高校大學生義務具有不確定性。
第三,我國高校具有懲治違紀學生的權力,同時作為被管理者的學生缺乏有效司法救濟。當學生違紀時,高校有權對其進行懲治和教育,對此,廣大學生無異議。但是當學生認為自己并無違紀行為,對懲治行為有爭議時,我國目前只是允許其向有關部門申訴,并無司法救濟的途徑,只有在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時,才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五、我國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的必要性
雖然特別權力關系在二戰后通過不斷完善,其適用范圍日漸縮小,法律保留和司法審查逐漸被引入,其符合民主法治的合理性一面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我國法治社會建設時期法制還不完善的需要,但不可否認,其本質上依然是一種特權理論,與排除“法外特權”的現代法治思想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同。
阿東把骨灰壇輕輕地放入事先留好的水泥穴中,又放了幾樣母親心愛的東西和全家人的照片。然后他摸出一個小布袋,緊貼骨灰壇放下。阿東跪下來,敬了一炷香,然后說:“姆媽,您安心在這里睡。我會照顧好爸爸的。哥哥我也會照顧好的,您放心就是了。這個袋子里是我跟哥哥的頭發,我把它們混在一起了,哥哥現在跟我是一體的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您當是我們一起在陪您。“
立法對高校“自主管理權”的具體范圍模糊,學校制定管理規章片面加重學生的義務是引起高校圖書館罰款制度與學生之間糾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據調查,56.5%的人認為我國高校圖書館罰款制度有需要完善和修改的地方,42.6%的人都認為有必要將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特別權力關系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因此將這種關系納入法治化道路確有必要。具體表現為:
(一)人權保障時代潮流的必然要求
人權,又稱為基本權利或者自然權利,產生于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二戰后,人權理論進一步發展。“戰爭令人警醒”,二戰是對世界人權的嚴重踐踏,在戰后法治重建過程中,各國對人權保障給予了充分重視,再次在憲法中將人權確定為本國公民的基本權利。雖然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關于人權保障的范圍、人權保障方式及其具體定義受到很大的爭議和沖突,但在抽象的理解方面,人權理論有著廣泛的共識。人權保障是現代法治的核心思想,社會文明進步的根本標志和必然要求。
傳統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單方面強調公立高校的特別權力和學生的服從義務,缺乏對學生基本權利的重視,在管理制度設立和實施的過程中難免嚴重侵害了學生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權,隨著現代人權理念的深入人心,學生法治觀念的增強,作為權力相對人的學生對自身基本權利進行爭取。因此,充分保障權力相對人權利,將特別權力關系納入法治軌道,是順應人權保障時代潮流的需要。
(二)順應依法行政實踐不斷深入的必行之路
之所以要堅持依法行政,是由行政主體的性質決定的,堅持依法行政,規范和約束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力求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保護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保障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根本保證。
(三)特別權力關系理論更新的重要內容
時代是向前發展的,隨著社會制度以及國際法治研究的深入,特別權力關系也處于變化之中。如前所述,德國在這方面其限制基本權利、排除法律保留、排斥司法審查等特點,促進了德國行政法的發展,對實現國家行政管理、維持行政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有著重要意義。但其對權力相對人基本權利的漠視與二戰后興起的人權保障時代潮流相違背,因而在各國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批判和修正。將特別權力關系涉及的部分內容納入法治領域,相對于傳統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來說有了很大進步,但由于其依然固守特別權力本位,未能完全以特別權力相對人為中心理解特別權力關系。
具體到我國高校與學生之間,推進特別權力關系向一般權力關系的轉變是明確雙方法律關系,著重保障學生權力,不僅有利于促進高校與學生之間矛盾糾紛合理高效解決,同時也順應了特別權力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更新。
六、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建議
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特別權力關系已不符合我國當代依法治國理念,這并不代表著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廢棄,在當前我國法制發展不完善的今天,特別權力關系的存在依然有著重大意義。筆者認為,我們應在肯定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合理性的前提下,以“修正后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和法制現狀,將特別權力關系納入到我國高校法制范圍,充分發揮其優勢作用。
(一)明確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的立法思想
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的立法思想,是指在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過程中應遵循的指導思想。為保證高校教育管理活動的有序進行,在制定特別權力關系立法的過程中,既不能“一刀切”,對高校特別權力進行全然否定,也不能放任不管,任其發展,應進行合理配置,實現高校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與衡平,促使私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整與融合,推進特別權力關系在我國高校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對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相對人的基本權利進行優先保護
人權是現代法治的核心思想,我國憲法通過最高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對我國高校學生基本權利應優先保護不僅是憲法的要求,更是人權價值的集中體現。公立高校在行使特別權力時,應以學生基本權利的客觀狀況和現實需求為界限,嚴格按照正當程序原則和比例原則。這是因為我國公立高校處于特別權力主體地位,而學生屬于權力相對人,兩者發生糾紛,學生往往處于“弱勢”,根據法律優先保護弱者的原理,其基本權利應當得到優位保護。
(三)對高校與學生特別權力的配置進行法律規制
對學校特別權力的配置進行法律規制,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首先,對特別權力的設定必須依照法律,特別權力關系“特殊”但并不“特別”,不能脫離我國憲法和法律等上位法的規定,因此其設定必須依照法律,特別權力關系主體不可自行設定特別權力。其次,對特別權力的具體配置以應以禁止權力濫用為原則。即特別權力主體行使特別權力不得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應針對特別權力的行使、監督、救濟等方面制定法律法規,完善相關制度,從而有效的防止權力濫用。最后,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要求權力主體在制定內部管理規則時,即便是為了達成公法上的特殊目的,也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否則不能限制權力相對人的基本權利,每一國家的法律制度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只有各安其位,才能使我國法制價值得以最大化。
七、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高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由于引入了基本權利原則、法定保留原則、司法保護原則,已經由傳統特別權力關系開始向法治原則下的一般權力關系演進。隨著特別權力關系法治化進程的加快,高校圖書館與學生基于罰款制度產生的糾紛也可通過立法授權、引進法律保留原則和司法審查機制方式得以規范和有效解決。
[1]周明杰.高等學校圖書館罰款制度的變革與革新[J].蘭臺世界,2013.
[2]文娟.學校與大學生的法律關系分析[J].金卡工程,2008(12):23-35.
[3]郭曰鐸.高校學生權利行政救濟研究[D].山東大學,2007.
[4]周春華.特別權力關系向一般權力關系演進法治化途徑[J].燕山大學學報,2007(2):65-98.
[5]周春華,黃雪賢.我國特別權力關系基本理論問題探討[D].蘇州大學,2007.
D
A
2095-4379-(2017)21-0067-03
吳琳科(1992-),男,漢族,山西長治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