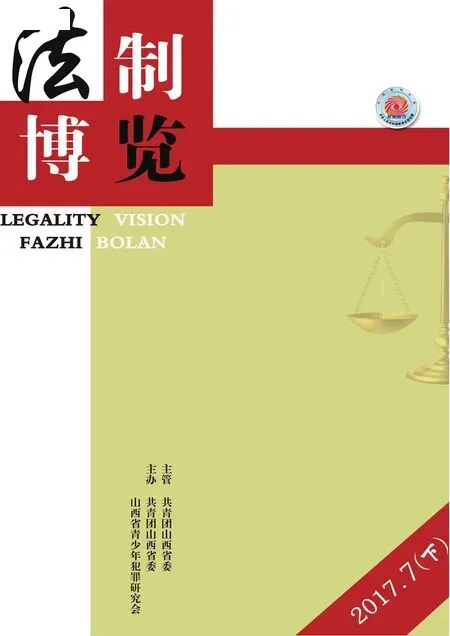行政協議訴訟制度原告主體資格探究
蘇思瑜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
行政協議訴訟制度原告主體資格探究
蘇思瑜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針對新《行政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行政協議訴訟的若干規定,筆者擬從實然層面和應然層面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從文本出發剖析當前我國行政協議訴訟制度對原告主體資格的規定與限制,另一方面針對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提出完善建議。
行政協議;行政協議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一、行政協議訴訟
行政協議是指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管理或者基于公共利益出發同公民和法人等訂立的有行政法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行政協議的訂立目的、主體和協議內容都具有鮮明的行政性特征,具體主要包括“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補償協議”、“政府特許經營協議”以及兜底性的“其它行政協議”。
行政協議訴訟是指行政協議的一方當事人認為另一方當事人在行政協議的訂立或履行過程中,沒有履行協議義務或者沒有按照約定履行協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依法進行審理后作出裁決的活動。提起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是否局限于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所規定的主體,筆者將在下文進行具體分析。
二、實然分析:行政協議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
(一)行政主體的原告資格
從新《行政訴訟法》中可知,如果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或者是沒有按照約定履行或者是違法變更了經營協議以及房屋征收等協議可對其提起行政訴訟。從2015年的《司法解釋》相關條款中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以下相關協議提起的訴訟,我國人民法院需依據法律進行受理: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或房產補償協議;其他行政協議。另外,《司法解釋》相關條款對此規定,如果原告請求解除或者確認協議是無效的,且其理由成立,那么可根據合同法相關條款給予處理。被告若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有其他的法定理由因此變更或者解除協議而導致原告出現損失則應由被告補償。
根據文法構造來分析,行政協議訴訟的原告被限定為協議一方當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被告被限定為協議另一方當事人行政機關。那么行政機關就不能對不愿或怠于履行行政合同的行為提出訴訟,而基于行政協議的行政法特征,在現實司法中行政機關也難以通過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要求對方履行協議,通常行政機關只能憑借其所享有的行政優益權督促行政相對人履行協議。
(二)第三人的原告資格
新《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相關規定提出,行政行為的相對人和其他同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系的公民或者其他組織是有權利提出訴訟的……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前款中提到的行政行為包括了法律、規章授權組織的行政行為。從法條中可以看出原告資格的判定主要是根據利害關系作為標準,這就說明如果同行政行為存在了利害關系,那么就可以提出行政訴訟。此外,2015年的《司法解釋》當中的第11條第2款在文意表述以及文法構造上同新的行政訴訟法是不同的,這就給合同外的第三人針對行政合同提起訴訟釋放了一定的空間。從兩者相結合的情況來看,假如合同簽訂或者履行對第三人利益存在侵害,那么第三人是有權利提出訴訟的,但是問題是應該怎么對第三人同行政合同之間的利害關系問題進行認定。
(三)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法律制度。2015年7月1日,我國的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召開的第15次會議中提出,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生態環境、資源保護以及國有土地轉讓等領域被授予該權利。在北京等十三個省以及直轄市等中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公益訴訟試點。公益訴訟制度已經寫入民事訴訟法中,而新《行政訴訟法》并未對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作出規定。
截止到2016年的12月底,試點地區的檢查機關針對相關訴訟案件已經處理了437件。截止2016年12月30日,筆者在北大法寶的司法案例中尚未發現行政協議方面的公益訴訟案件。雖然尚無典型案例可知,但是依據指導案例可以看出檢察機關是我國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針對行政協議提起的公益訴訟原告資格一般也會限制為檢察機關。
三、完善行政協議訴訟制度原告主體資格的幾項改進措施
(一)賦予行政主體強制執行申請權
在行政訴訟法修訂過程當中還存在這樣的爭議:行政的主體能否作為訴訟原告。修法后,依舊有人主張應當賦予行政主體原告資格,認為不能因為行政主體享有行政優益權而剝奪行政主體的起訴權。筆者認為無需對現行行政主體被告恒定制度作出突破性規定,因為契約的“外衣”無法掩蓋協議的行政性本質屬性,行政主體在行政協議中仍然居于強勢地位。
雖然無需對現行行政主體被告恒定制度作出突破性的規定,然而可以通過對法條的合理解釋賦予行政機關非訴強制執行申請權,根據新《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七條的相關規定提出,公民、法人等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存有異議在法定期間如果未提出訴訟又不履行,行政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其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有學者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法釋[1998]15號),非訴執行僅限于“行政處罰決定、行政處理決定”,但截止2016年上半年,行政機關針對行政協議提起非訴強制執行申請,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有先例可循,福建省最高院2016年7月份發布的典型案例“長灌煤礦公司不履行行政協議,福建省國土廳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一案裁定作出后,雙方對裁定結果均予以認可,裁定已經生效。因此,筆者認為行政協議是可以作為法院非訴執行標準的,具體的可以由最高人院加以解釋和規范。
(二)明確“利害關系”的認定標準
抽象界定“利害關系”這一認定標準并非易事,從實踐中總結具有“利害關系”的情形不失為更好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行政協議糾紛涉及侵害第三人利益主要存在如下情形:第一,侵害第三人實際排他性的權利。具體點來講就是,行政機關如果沒有根據相關法律取消第三人的某一個排他性的權利,又根據行政合同將這權利再一次授予相對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三人就有權利針對該合同提出撤銷之訴來保障自身的權益。第二,針對土地利用以及規劃許可相關的行政合同,侵害了第三人的相鄰權、用益物權等。第三,侵害第三人享有的公平競爭權。從目前的制度上可以看到,不管是政府采購還是特許經營權的授予都是采用招標投標這種方式來進行的。在這個過程當中,任何競標人都會有利益競爭,也應該允許其對競標的結果載體合同提出異議訴訟。
(三)擴大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仍未發展成熟,如何證明以公共管理和服務為主要目的的行政協議存在私人與政府機關共謀侵害公共利益是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大難題,而何許人能夠在案件中提起訴訟也值得研究,如果囿于《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利害關系”標準,定無法滿足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需求,如果突破《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利害關系”標準,但將原告局限為檢察院,那么也不符合放寬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趨勢。
《中國行政審判指導案例》曾在某一案件中指出,如果公民或者法人等合法權益受到了潛在的影響,是有權利根據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出訴訟的。合法權益的侵害不局限于現實的、當下的、明顯的,也包括將來的、可能的、潛在的這一解釋無疑將使得行政相對人與相關人員在面對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自身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更充分切實的保障。確定行政協議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應當立足行政公益訴訟制的構建目的,針對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筆者認為或可采“合法權益受到潛在影響”這一標準,因為行政協議具有行政管理目的,其內容多數體現為政府與私人合作以實現提供行政服務的職能,故筆者認為對公益訴訟的原告標準采取更為寬容的標準并無不妥。
[1]夏文菊.論我國行政合同訴訟制度的完善——以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為視角[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9).
[2]高俊杰.新<行政訴訟法>下的行政合同訴訟[J].財經法學,2016(2).
[3]黃學賢.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若干問題探討[J].法學,2006(8).
[4]蕭輝.新<行政訴訟法>具體適用中的六個問題——專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劉行[J].人民法治,2016(7).
[5]張曉玲.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探討[J].法學評論,2005(6).
[6]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D
A
2095-4379-(2017)21-0181-02
蘇思瑜(1992-),女,福建南安人,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