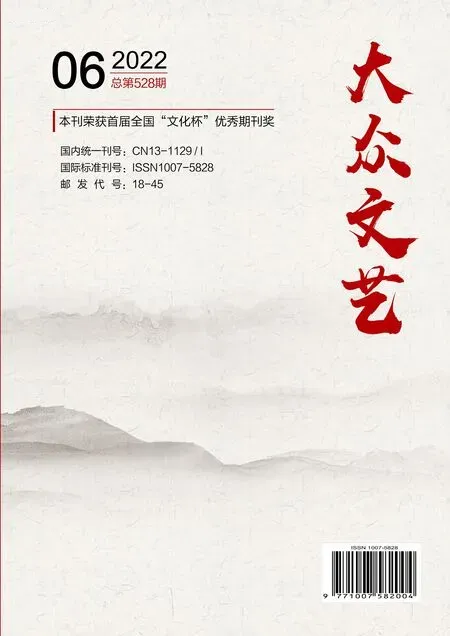集體的緘默
——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人性沉淪
周銘哲 (遼寧大學文學院 110136)
集體的緘默
——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人性沉淪
周銘哲 (遼寧大學文學院 110136)
西方文明對于人的重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西方人對人、神之間的關系從來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20世紀之前的西方傳統文明主要圍繞著兩方面展開:上帝的膜拜與人性的高揚,這兩方面在歷史的長河中具有相對穩定性。可是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尤其是經過一戰之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西方人的傳統價值觀面臨嚴峻危機:資本高度發展帶來的是道德倫理的坍塌,上帝缺席后伴隨的是人們信仰的虛空。這些問題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因此,沿著人性這一主線對此文本進行探討,不僅能夠廓清歷史的蒙塵,還有助于喚醒在當代社會中迷失的自我。
人性;文明;笑;隔膜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思考人性時有一種“雙重視野”:一方面他的小說好像在描寫一場舞會,他是圈子內的人同最漂亮的姑娘在舞廳里跳舞;但同時,他又像是站在舞廳外面,鼻子貼著玻璃窗往里看的一個中西部小男孩,心理盤算著舞票和樂隊的價錢。1這說明菲茨杰拉德在思考人性時陷入了焦慮與迷惑。其實,這種“雙重視野”的背后隱藏著西方文明深刻的文化內涵。這一文化內涵就是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原罪”是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也是西方文化與文學中人的罪惡意識以及善與惡永恒廝斗的根源。2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這件事本身是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它象征著文明的誕生以及文明給人類帶來的福祉;但是偷吃禁果的他們受到了上帝的懲罰,這象征著人類的文明有時候會出現嚴重的問題。一方面人類羨慕自己創造的文明,另一方面也要承擔文明帶來的后果。這樣的對立使作品中的人物成為了崇尚金錢與承擔痛苦的綜合體。在這樣的一種矛盾沖突下,人性必然走向沉淪。人性的沉淪在這部作品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文明與野蠻的換位
整篇小說中,文明人被視成異類,他們的周圍充滿了懷疑的聲音。這種懷疑聲音在小說的開頭就已經出現。“久而久之,我就慣于對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斷,這個習慣既使得有許多怪癖的人肯跟我講心里話,也使我成為了不少愛嘮叨的惹人厭煩的受害者。”“由于這個緣故,我上大學的時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責為小政客,因為我耳聞一些放蕩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傷心事。”3小說中的“我”其實是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大眾對“我”的懷疑說到底是對教育的懷疑,對文明的懷疑。庸常的大眾不自覺地走到了文明的對立面,即野蠻那里去了。當“我”與湯姆初次見面的時候,湯姆對“我”充滿了警惕。“‘噢,我一定會在東部待下來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在提防還有什么別的名堂。”4按照常理,人與人初次見面應該滿懷熱情,可是湯姆的態度卻是冷冰冰的。人與人之間處在一種彼此互不信任的狀態。這種現象用湯姆的話說就是“文明正在崩潰”。湯姆還認為如果白種人不當心,就會被其他人種取代。這種觀點已經超越了個體間相互懷疑的局面,上升到了種族間相互戒備的境況。“‘我們非打倒他們不可。’黛西低聲地講,一邊拼命地對熾熱的太陽眨眼。”5湯姆和黛西的看法代表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觀點。這種觀點肯定了種族主義,玷污了自由平等這一光彩神圣的理想,構成了對傳統文明的挑戰。湯姆的情人威爾遜太太因談到了黛西而與湯姆發生爭執的時候,湯姆表現出的是野蠻的行為。“湯姆?布坎南動作敏捷,伸手一巴掌打破了威爾遜太太的鼻子。”6湯姆并不是由于出于保護黛西的目的教訓了威爾遜太太,而是因為威爾遜太太動搖了湯姆不可置疑的權威。湯姆這一類有權勢的人認為自己的經驗是正確的、合理的,但是他們的行為確實粗魯的、野蠻的。這就把傳統的倫理道德排擠出了文明的界限之外,填充進來的是“弱肉強食”的信條與“互不信任”的法則。他們用野蠻的主張代替了文明的內涵,其結果又經過整個社會的默認,最終形成了新的“文明”。而傳統文明則徹底被邊緣化,它被看成是有問題的,甚至是難以置信的。蓋茨比就是這樣的一個被大眾唾棄的文明人。在蓋茨比的聚會上,露西爾告訴“我”“‘有人告訴我,人家認為他殺過一個人。’”7蓋茨比的客人空穴來風地將蓋茨比為人友善這一美好的品質看成了對罪惡的檢討與懺悔。蓋茨比真誠地告訴貝克自己上的是牛津大學,可是貝克并不相信。整個社會因被猜疑與謠言籠罩著而顯得死氣沉沉。從文化生成的語境來看,聚會狂歡有助于打破人與人之間在心靈上的界限。可是在這里,狂歡并沒有削減人們彼此之間的疏離與防范。整個社會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文明與野蠻互換了位置,人性走向了墮落與沉淪。
二、青春與活力的異變
“笑”尤為頻繁地出現在作品里。通常情況下,“笑”是人們青春活力的彰顯。可是作品中這種青春活力卻遭到了資本的侵蝕,從而發生了變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黛西的“笑”。當黛西知道自己的丈夫湯姆有婚外情時,她強作歡笑。她的“笑”標志的不是她的寬容大度,相反,它體現的是自己對敗壞了的道德的認同。黛西與蓋茨比再次見面時,她興奮異常。她之所以興奮,并不是因為又重新看到了蓋茨比,而是因為她看到了蓋茨優越的生活條件。“‘我很高興,杰伊。’她的聲音哀艷動人,可是她吐露的只是她意外的喜悅。”。8進一步講,她的“笑”、她的喜悅是對金錢與權力的屈從。后來,黛西開著蓋茨比的車撞死了威爾遜太太,她竟和湯姆聯手,把罪責推到了蓋茨比的身上。蓋茨比身亡后,她為了避免受到牽連,拒絕參加蓋茨比的葬禮。黛西“笑”的背后充滿了預謀、虛偽與貪欲。正如作品中所說的那樣“正是這樣,我以前從來沒有領悟過。它是充滿了金錢,這正是她聲音里抑揚起伏無盡的魅力的源泉……”。9而實際上,結婚之前的黛西是富有朝氣的,她能夠理解蓋茨比。用蓋茨比的話說就是“‘可是她不理解,’他說,‘她過去是能夠理解的。我們往往在一起坐上幾個鐘頭……’”10黛西過去是純潔無瑕的,與湯姆剛剛結婚的時候她還在哭泣。可是婚后的黛西喪失掉了自由,這種情況是資本造成的。金錢關系異化了這種活力,使這種純粹的活力變質,使理想屈服于現實。泛濫的物質社會為自由的理想套上了沉重的枷鎖。湯姆的情婦威爾遜太太也是如此。“她看看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接著她蹦蹦跳跳跑到小狗跟前,歡天喜地地親親它,然后又大搖大擺地走進廚房……”11威爾遜太太的“笑”與其說是莫名的,不如說是對金錢與權勢的回報與饋贈。當談到自己貧窮的丈夫威爾遜先生時,她卻收束起了笑容。“‘我嫁給了她,是因為我以為他是個紳士,’她最后說。‘我以為他還有點教養,不料他連舔我的鞋都不配。’”12“‘愛他愛得發瘋!’默特爾不相信地喊道,‘誰說我愛他愛得發瘋啦?我從來沒愛過他,他就像我沒愛過那個人一樣。’”13威爾遜太太因丈夫的貧窮,故而對自己的婚姻感到無奈。這種無奈實則是對金錢的崇拜。威爾遜太太“笑”與“哭”這一前后對比,折射出了在當時金錢操控下社會的流變與人性的無常。“笑”在作品中不僅是具體的個別人發出的動作或表現出的狀貌,它還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意象。“笑聲每時每刻都變得越來越容易,毫無節制地傾瀉出來,只要一句笑話就會引起哄然大笑。”14“笑”在資本的面前變得極為廉價。“笑”已經褪去了青春活力的本色,留下的只是無聊的寂寞與空虛。
三、他者與自我的隔膜
小說的敘事主體“我”與他者之間有著巨大的隔膜。這種隔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是“我”與蓋茨比的隔膜。這種隔膜首先集中表現在兩個人的居住環境上。“我”居住的房子與蓋茨比的房子比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那天夜里當我回到西艾格的時候,有一會兒我疑心我的房子著了火。半夜兩點鐘了,而半島的那整個一角照的亮堂堂的。”“轉彎以后,我才看出原來是蓋茨比的別墅,從塔樓道地窖都燈火通明。”15房子在整部小說里顯然具有象征意義,它象征著人格力量。在這種對比下,蓋茨比高尚的精神凸顯出來,進而從側面反映出了“我”與蓋茨比之間的代溝。蓋茨比真心向“我”推薦工作,卻被心存偏見的“我”直言拒絕。蓋茨比大難臨頭,“我”勸蓋茨比離開別墅,他卻不肯考慮。這些都反映出“我”與蓋茨比這一他者有著不同的追求與目標。這些因素造成了彼此之間的隔膜。另一方面是“我”與家族的隔膜。小說中交代了“我”的伯祖父為整個家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離奇的是“我”卻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從未見過這為伯祖父,但是據說我長得像他,特別是有掛在父親辦公室里的那副鐵板面孔的畫像為證。”16伯祖父鐵板的面孔就像將親情割裂的鐵幕,造成了“我”與整個家族的距離。因此,“我”感到的是一種凄涼。“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溫暖的中心,倒像是荒涼的宇宙邊緣。”。17第三個方面是“我”與社會的隔膜。在蓋茨比的要求下,“我”促成了蓋茨比與黛西的會面,卻造成了蓋茨比的悲劇。這是因為深受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的“我”并沒有看清楚都市社會的人情世態。“我”成為了導致蓋茨比內心痛苦并走向死亡的直接推動力量。他者與自我的隔膜必然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可以說,這也是人性沉淪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小結
作者面對人性的問題,在作品中表現出了糾結與困惑。這種困惑是對時代的困惑,更是對整個西方文明該何去何從的困惑。相關人性問題的思考與解讀還沒有到達終點,也不應該有其終點。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探索,至今仍然具有重要而且深遠的意義。
注釋:
1.[美]亞賽?麥塞納.天堂的彼岸[M].侯頓出版社,1966:2.
2.蔣承勇.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8.
3.4.5.6.7.8.9.10.11.12.13.14.15.16.17.[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李夢嫻,譯.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1、15、20、62、173、53、62、129、173、159、45、49、50、57、117、4、4.
[1][美]亞賽?麥塞納. 天堂的彼岸[M].侯頓出版社,1966.
[2]吳元邁.20世紀外國文學史[M].譯林出版社,2004.
[3]蔣承勇.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4][美]菲茨杰拉德.李夢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周銘哲(1993.10-),男,遼寧省沈陽市,男,漢族,現就讀于遼寧大學文學院、16級在讀碩士,專業:文藝學 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