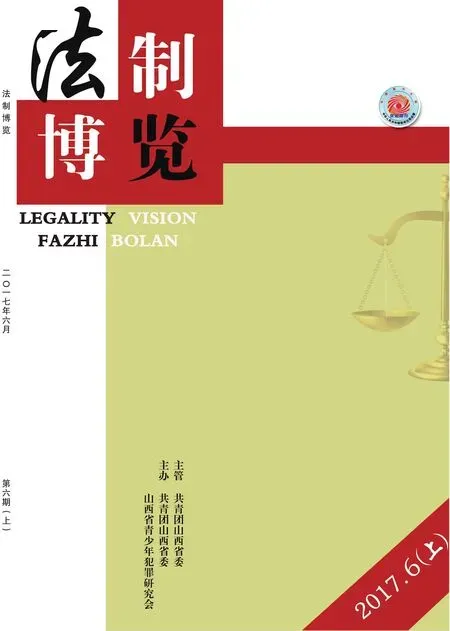民間借貸案件中刑民交叉問題研究*
徐亞蘭
浙江工業(yè)大學(xué),浙江 杭州 310014
?
民間借貸案件中刑民交叉問題研究*
徐亞蘭
浙江工業(yè)大學(xué),浙江 杭州 310014
刑民交叉問題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而隨著民間融資的蓬勃興起,民間借貸案件也越來越多的涉及刑民交叉問題。例如在案件審理中發(fā)現(xiàn)借貸行為或借貸主體涉嫌犯罪或者當事人主張涉嫌犯罪時,是先民后刑、先刑后民還是刑民并行,以及涉案合同效力如何認定等,各地法院有不同認識和做法。最高院2015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對這些問題有所涉及,但實踐中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從民間借貸異化為刑事犯罪的原因、刑民交叉的程序選擇,合同效力認定等幾個方面進行闡述,以期對此類案件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程序選擇;合同效力
一、民間借貸活動易轉(zhuǎn)化為刑事犯罪的原因
(一)法律規(guī)范的固有缺陷
2015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以及2016年的刑民交叉裁判意見都對民間借貸相關(guān)問題做了規(guī)定,對實踐中處理這類案件都具有很好地指導(dǎo)與借鑒意義。但由于法律存在的滯后性、空白、不確定等特點,實踐中出現(xiàn)的案件不可能都有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因此仍然會出現(xiàn)司法工作人員對于同一案件產(chǎn)生不同的認識。
例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關(guān)于“存款”的概念,文義解釋應(yīng)當理解為零風(fēng)險的還本付息的固定收益,但若嚴格按照該解釋,實際生活中大量的非法集資行為則無法被納入刑法規(guī)制的范圍,這也不符合立法最初的維護國家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fēng)險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臺的《關(guān)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第一條對非法吸收存款罪的“存款”①這一概念作了較之前更為寬泛的規(guī)定,同時列舉了11種典型的吸收公眾存款的表現(xiàn)形式,這些都對打擊非法集資活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這種擴張性解釋是否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仍有待探討。
(二)利益誘惑
借貸行為在我國古代民事法律關(guān)系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應(yīng)該與其能夠滿足出借人、借款人雙方不同需求密切相關(guān)。但我們也都知道,一旦涉及利益問題,就很容易出現(xiàn)糾紛。宋朝對民間借貸活動采取不干涉原則,但對于有息借貸(出舉),從法律上作了諸多限制。②比如《宋刑統(tǒng)》中明確對借貸利率作了限制規(guī)定:“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③。以此防范高利貸者對貧民百姓的盤剝,對于現(xiàn)在也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
近幾年大量出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投資跑路事件,給出借人帶來巨大損失,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但經(jīng)過分析,在大部分刑民交叉的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對自己的行為都有一定的責任。部分借款人受利益驅(qū)動,以非法占有的心理大量集資,然后肆意揮霍導(dǎo)致資金鏈斷裂,最后事情敗露,理應(yīng)承擔責任。為什么說出借人也有責任呢?部分出借人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一味追求高利率,而我們應(yīng)該意識到高利潤通常也伴隨著高風(fēng)險。高利潤并不違法,但不一定受法律保護。當然,這里的出借人的責任是指他所付出的代價,在參與的金融活動涉嫌違法犯罪的案件中,出借人的大部分資金很難收回。
(三)征信體制缺失
民間借貸最初只是熟人社會中的產(chǎn)物,大多也都是私人之間的小額借貸,所以更多的還是基于彼此之間的信任。在民國時期,人們這樣講到:“吾國通俗,尚信用、講體面,非萬不得已時,不愿實行抵押貸款,雖抵押品豐足者,亦不愿履行此項名義,以為有礙體面。錢莊因熟習(xí)商家之心理,復(fù)諒情度勢,可推知商家之底蘊。”④可以看出當時錢莊借錢給商人都是基于對他們的信任度。但現(xiàn)如今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科技的發(fā)達,民間借貸活動也日趨復(fù)雜。現(xiàn)在社會流動性增大,人們的生活圈子也不像古時那么狹小與固定。一個人的社會評價可能并不為周圍人所熟知,也就為一些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實施不法行為的機會。部分受害人謹慎出資,在投資前通過各種途徑進行了解,但最后被這些假象所蒙蔽。
例如在很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集資人可能打著開工廠、辦企業(yè)的幌子,向受害人集資并承諾給予高額回報。在此過程中除了將一部分吸取的資金用于還本付息外,相當一部分被用于個人揮霍、維持公司的巨額運行成本、投資不良債權(quán)以及廣告炒作等,從而營造聲大勢大的假象。2011年的吳英案中,非法集資的對象不僅包括林衛(wèi)平等11名直接被害人,也包括向林衛(wèi)平等人提供資金的100多名“下線”。這些人大多并不認識吳英,只是大家口口相傳,最終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而最近剛開庭審理的e租寶案件中,也存在類似問題。這值得我們反思與慎重對待。這些都體現(xiàn)現(xiàn)階段的征信制度不夠健全,需要加以完善。國務(wù)院印發(fā)《國務(wù)院關(guān)于建立完善守信聯(lián)合激勵和失信聯(lián)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shè)的指導(dǎo)意見》,希望能減少此類案件的發(fā)生。
二、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問題的程序選擇
民間借貸糾紛可能涉及刑事問題的處理方式選擇:一是法院在立案后,發(fā)現(xiàn)民間借貸行為本身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應(yīng)當裁定駁回起訴;立案后,發(fā)現(xiàn)與民間借貸糾紛雖有關(guān)聯(lián)但不是同一事實的涉嫌非法集資等犯罪的線索、材料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繼續(xù)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二是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過程中,相關(guān)行為人被公安機關(guān)立案偵查,致使案件既涉及刑事犯罪同時又涉及民事責任認定和承擔。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行程序選擇是一個重要問題,理論與實務(wù)界都進行長期的研究探討。
(一)“先刑后民”處理方式及其弊端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施行的《關(guān)于在審理經(jīng)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jīng)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1998年規(guī)定》)中確定了在經(jīng)濟糾紛案件中先刑后民的原則。“先刑后民”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應(yīng)用的較為廣泛,其在提高審判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減輕被害人訟累等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但隨著新型刑民交叉案件的出現(xiàn),這種處理模式的弊端也逐漸顯現(xiàn)。
在“刑民交叉”的民間借貸案件中適用先刑后民處理很容易產(chǎn)生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沖突。首先,先刑后民側(cè)重于對公權(quán)的優(yōu)先保護。以陳興良教授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刑事優(yōu)先原則剝奪了當事人對程序的選擇權(quán),使公權(quán)私權(quán)處于一種極不平衡的狀態(tài)。其次,先刑后民程序模式容易被濫用。“先刑觀念”的本質(zhì)在于“有罪思維”,以至于在處理刑民交叉類的疑難案件過程中,經(jīng)常性地發(fā)生曲解刑法規(guī)范的事例,比如在涉及到“訴訟欺詐”案件中,就有人提出應(yīng)當按照詐騙罪論處的觀點,指出詐騙不需要有被害人上當受騙自愿交付財物的特征。而隨著我國法治進步,這種有罪推定的思想也逐漸予以矯正。先刑后民還易被部分當事人惡意利用,拖延訴訟時間,逃避責任承擔或者希望借司法權(quán)力挽回財產(chǎn)損失。最后,先刑后民不利于權(quán)益保障。在復(fù)雜的經(jīng)濟類案件中,保障當事人的債權(quán)實現(xiàn)是終極目標。但在先刑后民的模式下,很多債權(quán)人只能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實現(xiàn)權(quán)利。但這種訴訟模式對民事權(quán)益的保護遠低于直接通過民事訴訟所能得到的。
(二)“先民后刑”模式的設(shè)想
近代世界各國對私權(quán)和公權(quán)的保護均有所側(cè)重,這些均與一國的社會現(xiàn)實及國情密切相關(guān)。當我國處于計劃經(jīng)濟時代,強調(diào)公有制經(jīng)濟,自然側(cè)重于社會保障。而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開始重新認識并重視私權(quán)價值。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轉(zhuǎn)型階段,政府鼓勵民眾利用剩余資金進行投資,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蓬勃興起。確定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優(yōu)先,是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平衡社會權(quán)利紛爭的重要步驟。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是對財產(chǎn)的獲取、占有和享有的一種法律上的平等,也即是一種機遇平等。⑤因此,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先民后刑”也得到越來越多學(xué)者的贊同和支持。
從另一方面來看,先民后刑也意味著人權(quán)保障與打擊犯罪的博弈。盡管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把保障人權(quán)作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任務(wù)而與打擊犯罪并重,但問題是,掌握著“生殺大權(quán)”的司法機關(guān)能不能中立地處理刑民交叉類案件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然,“先民后刑”并不是排除對公權(quán)的保護,而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能夠尊重案件的實際進度,使民事部分得到及時的解決。不容置疑的是,不論哪種模式都不會是完美無瑕的,都會有一定的弊端。比如民事審理中認定的證據(jù)并不能當然的應(yīng)用于刑事程序中,因為民事刑事的證據(jù)認定要求不同。那么在刑事部分審理中可能對于證據(jù)問題等需要重新認定,降低訴訟效率。還有“先民后刑”模式承認民事賠償折抵刑事處罰的合理性,有效地促成了被告方與被害方的和解,解決了被害人的民事賠償問題,但在理論正當性上面臨爭議。
(三)以“刑民并行”為原則
最高院發(fā)布的《最新民刑交叉案件裁判意見16條》第六條規(guī)定“被告涉嫌刑事犯罪,并不能否定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的民事關(guān)系,法院一并駁回原告對被告的起訴不當,至于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后,是否應(yīng)該裁定中止審理,應(yīng)由受理法院視情形決定。”例如趙學(xué)軍與趙明伍、劉克勝民間借貸糾紛案⑥中便是如此處理,體現(xiàn)司法部門對刑民并行的認可。
當然,對于一些特殊情形下的案件就要采用“先刑后民”及“先民后刑”來處理。《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五)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jié)果為依據(jù),而另一案尚未審結(jié)的……。”2015年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七條對此加以明確。這是處理刑民程序沖突時的重要法律依據(jù)。表明在一案需以另一案的審理結(jié)果為依據(jù)或者另一案的審理對本案審理結(jié)果將產(chǎn)生重要影響時,才可“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三、合同效力認定
民間借貸案件中合同有效與否與當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guān),同時合同效力認定也是民間借貸案件審理的重要部分。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凡是涉及刑事犯罪的民間借貸活動,其中的民事行為當然無效。原因是借貸行為涉嫌刑事犯罪,而刑事犯罪的違法性又高于民事行為,那么民事上也應(yīng)當是無效的。個人認為這種看法過于片面化。刑法民法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而民間借貸合同屬于民事法范圍自然應(yīng)當嚴格按照民事法律規(guī)范,同時結(jié)合最高院關(guān)于合同無效的司法政策精神加以認定。
(一)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發(fā)生交叉的民間借貸合同效力
借款人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吸收存款構(gòu)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就單個借款行為而言,僅僅是引起民間借貸這一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法律事實,并不必然構(gòu)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實。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實是數(shù)個“向不特定人借款”行為的綜合,從而引發(fā)了從量變到質(zhì)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行為與單個民間借貸行為并不等價。
如果僅僅是出借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貨幣,借款人自愿借入貨幣,雙方自主決定交易對象與內(nèi)容,既沒有主觀要去損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過錯,客觀上也沒有對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到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除存在《合同法》第52條、本規(guī)定第14條規(guī)定的情形外,應(yīng)當認定該民間借貸合同為有效。在約定借款利率的合同中,也不能因為約定利率過高而認定借貸合同無效。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二十六條可知,現(xiàn)階段只是對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的部分認定無效,并不影響合同效力。
(二)與集資詐騙發(fā)生交叉的民間借貸合同效力
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不同,在集資詐騙案中,行為人采取隱瞞真相或者虛構(gòu)事實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可依照《合同法》54條的規(guī)定行使撤銷權(quán),當然受害人有選擇權(quán),因此合同效力是待定的。如果出借人事后明確表示追認合同效力,相關(guān)當事人仍然要承擔合同中的相關(guān)義務(wù)。也即是說,不論合同有效或無效,并不影響集資詐騙事實及犯罪數(shù)額的認定。因為任何人不得從其非法行為中獲利,這是刑法、民法的共同準則。
集資詐騙案中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導(dǎo)致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如果直接認定借貸合同無效,則意味著犯罪人可以免除支付約定利息的合同義務(wù)。甚至擔保合同也會因此無效,受害人的債權(quán)更是難以實現(xiàn)。在這些情況下,合同效力認定還是應(yīng)嚴格按照民事法的規(guī)定。刑事犯罪并不必然導(dǎo)致民事合同歸于無效,刑事處罰與追究民事責任可以并行不悖。⑦
四、結(jié)論
刑民交叉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已有大量研究,很多學(xué)者也都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而民間借貸活動中出現(xiàn)刑事犯罪問題該如何解決也是司法實踐中的疑難問題。不論是程序選擇還是合同效力認定,與其他刑民交叉案件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同時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在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之后發(fā)現(xiàn),在處理這類案件中還是應(yīng)當注意刑法的謙抑性,把握刑法介入民間借貸活動的度,應(yīng)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此外,現(xiàn)階段民間借貸形式更加多樣化,涉及經(jīng)濟類犯罪的頻率也越來越高,說明相關(guān)規(guī)定的滯后,現(xiàn)有的管理手段已不能勝任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國家權(quán)力機關(guān)應(yīng)加強對相關(guān)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的保護民眾的合法權(quán)益。
[ 注 釋 ]
①“承諾在一定期限內(nèi)以貨幣、實物、股權(quán)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②郭成偉.中國證據(jù)制度的傳統(tǒng)與近代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324.
③<宋刑統(tǒng)>卷26<雜律>“受寄財物輒費用”.
④戴恩波.錢莊在上海金融界中所占的優(yōu)勢[N].錢業(yè)月報,第8卷第3號,1928.5.
⑤錢福臣,魏建國.民事權(quán)利與憲政——法哲學(xué)視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⑥趙學(xué)軍與趙明伍、劉克勝民間借貸糾紛案案號:(2016)最高法民終138號.
⑦劉憲權(quán),翟寅生.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案件對民事合同效力的影響研究——以非法集資案件中的合同效力為視角[J].政治與法律,2013(10).
*2016年浙江工業(yè)大學(xué)法學(xué)院刑法重點學(xué)科課題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G1341360128001020)。
D922.28;D
A
2095-4379-(2017)16-0048-03
徐亞蘭,浙江工業(yè)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