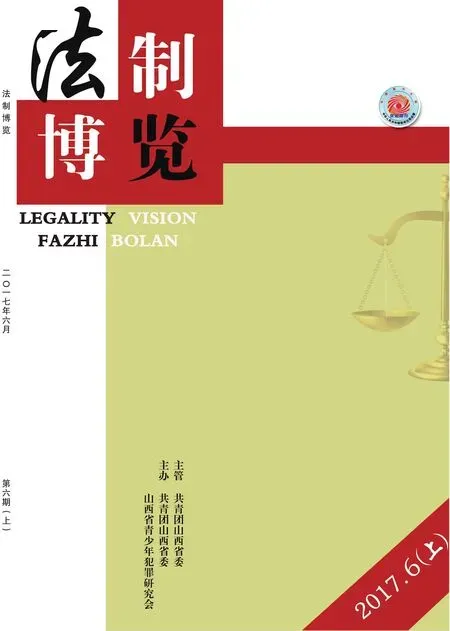論非婚同居的道德風險及其法律規制
王杉杉
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0
?
論非婚同居的道德風險及其法律規制
王杉杉
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0
非婚同居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早已普遍地存在于現實生活當中,同居已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下面就來談一談非婚同居的定義,非婚同居與事實婚姻的比較、非婚同居的原因、非婚同居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及其問題,外國法律對非婚同居的立法規制以及我國法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非婚同居;事實婚姻;原因;道德風險;財產和子女;立法規范
一、非婚同居的概述
非婚同居的定義及特征:
社會學家伯納德提出“未來社會婚姻的最大特點,正是讓那些對婚姻關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做出各自的選擇”。[1]所謂非婚同居,它是指男女雙方基于完全自愿,不受婚姻法約束,不產生婚姻效力的而在一起生活的同居行為。它是一種狀態,有以下特點:
第一、雙方完全基于自愿選擇在一起生活,缺乏結婚的目的。這也就是說排除一方對另一方的欺詐、威脅,雙方都是基于自己的意愿而愿意生活在一起的。“非婚”它所表達的是不處于婚姻的狀態,不受婚姻效力的約束。
第二、男女雙方沒有進行登記結婚,處于無證(結婚證)狀態。因為在我國,結婚必須到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登記是產生合法婚姻效力的條件。而非婚同居它強調的就是“非婚”的狀態,也就是要求男女雙方沒有進行登記結婚,沒有領取結婚證。
第三、男女雙方是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這要求男女雙方必須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能夠為自己所做出的行為承擔法律上的后果。
第四、男女雙方必須有同居的行為,男女雙方在一起同居達到了相當長的時間,公開性和長期性是其特征如果僅僅強調“非婚”而沒有“同居”的行為,那就不能稱之為非婚同居了,同居是非婚的實質行為。
二、非婚同居產生的原因
非婚同居已經是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的流行的生活方式。而它的盛行是經濟、文化、思想等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它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經濟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為其提供一種實用主義條件。國民由傳統的熟人社會進入到一種陌生人的社會,人口的大量流動,維持婚姻家庭間的穩定性的環境因素正處在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使得基本的家庭職能有了重大改變。
第二、文化因素,西方女權運動以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觀念的更新。尤其是女權運動,它釋放了女人的天性,讓女人從男人的桎梏中掙脫出來,開始在社會上有了一席之地。在所有的社會運動中,只有女權運動才能發展得如此的迅速,如此的革命化,徹底地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2]
第三、道德觀念的變化,讓社會開始尊重及實踐這種方式。隨著社會倫理道德的變化和性觀念的轉變,“傷風敗俗”“不知廉恥”的外衣已經從非婚同居的身上給脫下,人們認為婚姻不再是獨一的性結合方式。性道德觀念的轉變,使人們對非婚同居的態度和行為顯著改變,社會大眾對非婚性行為、非婚行為的態度日益寬容。據調查:有婚前性行為的男性有33.4%,女性有17.5%。[3]
三、非婚同居下所帶來的道德風險以及問題
(一)道德風險
法國作家熱內·居伊昂所說:“貞潔不過是一種偏見,一種既不存在與原始人當中,也不存在與真正的文明人當中的偏見。”[1]作家有開明的想法,但并不是每個公民都像這位作家一樣,盡管貞操在現代更多的被看著是公民性自由權,已經打破了男人對女人性自主權限制的囚籠,但是受傳統的道德觀念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婚姻是兩性結合的唯一正常的渠道,未婚同居不被其接受。
(二)女性在同居中受到的傷害
雖然當下非婚同居已經被社會大眾所默認,但它所帶來的風險下女性在同居中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受大眾責難的往往是女性,大多數人會認為是女性自己的不自尊自愛,自己作繭自縛造成的。此外據廣東省某項調查顯示:有62.4%的女性表示對自己沒有結婚就和別人同居生活在一起而感到難過與后悔。[4]主要有:
第一、懷孕流產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傷害。女方如果不小心懷孕,結果往往是被迫墮胎或者極少數選擇了生育,墮胎行為會使女方承受了身體上的傷害和心理上的壓力,而選擇將小孩生下來也必定會帶來計劃外的種種問題和麻煩。
第二、暴力傷害行為。根據全國某項報告顯示:在同居和婚姻生活中遭受到丈夫和同居伴侶的嘲笑與謾罵,用暴力、脅迫的方法控制其人身自由,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經濟上封鎖等各種各樣的暴力行為的女性有24.7%。
第三、經濟損失得不到補償。女性往往被留在家中操勞家務,都會選擇放棄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后來的同居關系解除時,她們得不到任何的補償。因為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往往會帶來經濟糾紛,同居期間男女雙方的財產往往是混同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很難確切的區分同居期間財產的歸屬。根據頒布的《婚姻法解釋(二)》中第一條規定,如果雙方要想到法院去起訴解除這種關系,人民法院是不會受理的,它否認了其可訴性。[3]提到如何處理同居期間財產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10條的規定,提出按一般共有財產解決。[5]
(三)非婚同居對子女的不利影響
如果同居雙方當事人有了孩子的雖然孩子不是在婚姻存續期間出生的,但孩子的權利與合法婚姻狀態下出生的孩子是一樣的,都受法律保護。盡管法律保護非婚子女的合法權益,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遇到了小孩上戶口難、上學難等各種麻煩與問題。對非婚生子女的歧視也是經常性見到,所以他們比婚生子女要敏感,通常都會有一種自卑的心理。
四、非婚同居立法規范的建議
英國法學家米爾恩認為,人權的存在和維護是社會生活之必需,沒有人權就沒有起碼的社會生活。[1]自由是人權的一種體現,而婚姻自由是現代人權社會的一個部分,所以公民結婚與否,由他們自己決定,任何人都不得干涉。非婚同居已經是現代社會的司空見慣的一個現象,它已經不容許法律對它的忽視。但在我國,立法對非婚同居這一方面還是出于空白狀態,這多少不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對此主要有以下建議:
第一、基于非婚同居這個客觀事實的存在,立法者應當對非婚同居進行立法規制,制定并出臺一部關于規范非婚同居這個現象的法律,取消非婚同居在法律地位上的尷尬存在,讓其變得有法可依。法院應該對解除同居關系的起訴予以受理。根據非婚同居關系成立的要件,對其進行實質性的審查,對于不符合非婚同居關系的,裁定駁回起訴,而對構成非婚同居關系的,可以依照一般離婚的案件予以處理。
第二、女性在同居中往往會受到更多的傷害,所以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要考慮到女性權益的保護,對此有以下的建議:1.應當肯定家事勞動的價值。女性在同居中為家務勞動付出了更多的心力,比如照顧老人、撫養孩子、讓另一方無后顧之憂的去工作、身體因生育或操勞受累造成一定的損傷等,女方可以在關系解除時向男方請求相應的補償。2.對于重大過錯的處理。同居期間如果一方有虐待、毆打對方等暴力行為,給對方造成身體或心理傷害時,有過錯的一方應當在解除同居關系時給予對方賠償,另外如果這些傷害行為涉及到刑事方面,被傷害的一方可以到公檢法部門控告。
第三、對于財產、子女問題,1.財產上可以參照婚姻法相關規定。2.在稱呼上就要取消掉“非婚”兩個字,在法律上一律稱為“子女”,沒有什么“非婚生”與“婚生的區分,這是保障所有子女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前提。放開戶籍制度,一旦非婚同居者有了孩子,民政部門就應該讓孩子上戶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又作用于經濟基礎,所以對非婚同居進行一定的法律規范,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非婚同居關系得到規范,必然地會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糾紛與麻煩,社會也會變得更加和諧美好。另外非婚同居的法律規制是對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補充,從而讓那些沒有被婚姻法保護的兩性在非婚同居法律規范得到相應的保障,不管是結婚還是沒有結婚的在一起生活,其權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就更有利于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1]王麗萍.非婚同居的法律規制價值分析[J].學術交流,2010,5(5)(總第194期).
[2]李曉光.從女權主義到后女權主義西方女權主義、女權主義的理論轉型[J].思想戰線,2005,31(2).
[3]陳葦,王薇.我國設立非婚同居法的社會基礎及制度構想[J].甘肅社會科學,2008(1).
[4]徐靜莉.非婚同居關系中女性的保護[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4(5).
[5]韓德剛.非婚同居當事人財產關系淺論[J].法制與社會,2008.2.
Title:The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of the moral hazard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
the unmarried cohabit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has long been common in real life.Cohabitation is a way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the following is to talk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unmarried cohabitation,unmarried cohabitation was compared with the fact that marriage,the cause of the unmarried cohabitation,unmarried cohabitation of moral hazard and its problems,foreign law of unmarried cohabitation legislation regulation and law in our country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Unmarried cohabitation;The fact marriage;Reason;Moral hazard;Legislative norms property and children
D
A
2095-4379-(2017)16-0098-02
王杉杉(1993-),男,漢族,安徽阜陽人,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2016級法律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