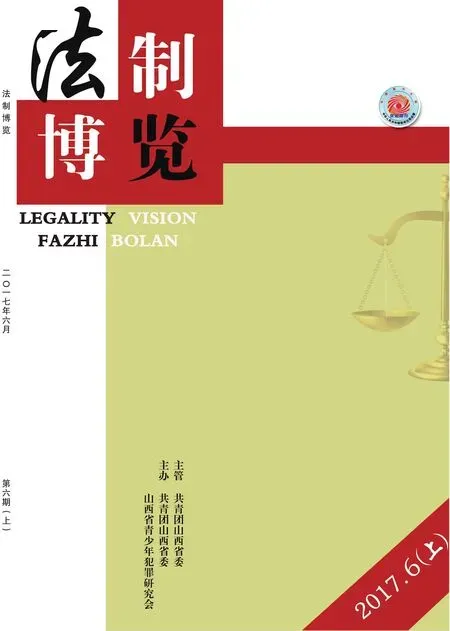淺談媒體審判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張梓恒
南昌大學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
淺談媒體審判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張梓恒
南昌大學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媒體作為社會公眾的發聲渠道是反映民意的重要途徑,司法審判在法治社會中有著聲張正義的職責,在司法活動中,法院要發揮主體作用,媒體也應適當和理性地行使言論權和監督權,如果媒體越位,甚至干預、影響司法審判,則很可能導致“媒體審判”。本文從“媒體審判”切入,從美國和我國的現狀角度對媒體審判對司法獨立的影響進行探討并提出相應建議。
媒體審判;新聞自由;司法獨立
“媒體審判”源于美國新聞傳播法中的一個術語,指媒體不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報道和評論尚處審判過程中的刑事案件,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渲染導向性輿論氛圍,影響司法獨立,妨礙公正審判,具體表現為媒體超越司法審判程序搶先對被告人進行定性或定罪量刑,提前對案件結果是勝訴還是敗訴作出引導性判斷,通過進行有傾向性的猜測或夸大渲染事實等方式,假借民眾之口表達某種具有導向性的觀點,煽動民意對審判機關施壓、影響司法判決。
媒體為了追求新聞自由與轟動效應,為了賺取銷量和關注度而選擇性忽略案件當事人的感受和利益,媒體的“搶先審判”也與一國司法機關追求的司法審判獨立、維護法律權威、保護被告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的核心價值產生極大矛盾,甚至當最終的法院審判結果與媒體的“判決結果”截然不同時,早已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媒體觀點的民眾很可能因此對法院審判產生強烈不滿和抵抗情緒,導致其對國家法制的失望,可見,媒體審判的“后遺癥”對一國法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一、西方的媒體審判——以美國為例
“媒體審判”的起源和西方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密不可分。英美法系國家的陪審團制度,程序上要求由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參與案件的審理,庭審中,他們依據證人證言、相關證據和雙方的辯論判斷案件事實,再由法官在此基礎上適用法律,做出判決。由于陪審團成員都是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普通公民,也不可能生活在與新聞報道完全隔絕的環境中,因此很容易受到具有煽動性的媒體報道的影響,很難在判斷案件事實的過程中保持中立客觀,從而給法官適用法律和作出判決帶來不利影響。
(一)“媒體審判”的典型案例——辛普森殺妻案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出現過眾多體現“媒體審判”的案例,有的案件甚至有轟動全球的影響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辛普森殺妻案。
辛普森案無疑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刑事案件之一,其影響力之所以如此巨大,除了事件主角的名人光環,還和媒體自1994年6月12日起長達一年半的鋪天蓋地的報道密不可分。從案發到審判,僅美國本土就有至少1200名記者參與了報道,在報刊、電視、網絡等各種媒體的炒作之下,“辛普森案”長期占據美國新聞的頭條,媒體極力塑造著辛普森殺人兇手的形象,例如,《時代》雜志將辛普森的收監照片進行加深處理,使讀者在視覺上對辛普森產生消極評價,并將圖片作為封面故事出版發行;有些報紙直接將“惡魔殺手辛普森”作為頭版標題,刊登定論性的評論文章;一些娛樂脫口秀節目爭相邀請法律專家、心理專家現場點評案件、推測審判結果,對案件當事人肆意調笑,將原本應該嚴肅對待的刑事審判變成了公眾的狂歡。在一波又一波的輿論渲染之下,“辛普森有罪”的觀點在深入人心。審判期間,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80%的美國人認為辛普森有罪。
輿論狂潮之下,為了維護司法公正,陪審團由于受到媒體過度報道的影響無法中立地參與案件審理而被解散。審判中,辯方律師指出,兩位關鍵證人——辛普森的鄰居夏夫利和刀具商卡馬喬——都有償地將案件信息透露給了媒體,法官也因此排除了兩位證人的證言。1995年10月3日,美國司法機關頂住媒體審判的壓力,法官判決辛普森無罪,美國全民嘩然,人們紛紛表示判決結果難以置信。判決之后,仍然有大批媒體認為辛普森案是“美國司法歷史上最有爭議的案件”,并在2004年再次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抽樣的近一千兩百名美國人中,仍然有77%的人認為辛普森有罪。“辛普森案”無疑是媒體審判的一個極致體現。
(二)美國法律對避免媒體審判的規定
為了避開媒體干擾以確保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以及為了使被告獲得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賦予的“一個公正陪審團”條款和第十四條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的保護,美國法律規定了降低媒體干擾的措施,總體而言有六項:1、禁言令,即禁止訴訟參與人員向公眾談論案件;2、對媒體的事先限制,即禁止媒體報道任何影響被告人公正審判權的內容。法官需要在平衡被告人公正審判權與新聞自由之間做好判斷,要求嚴格;3、篩選陪審團,即盡可能篩選出沒有受媒體報道影響、能夠中立而公正地審理案件的陪審團;4、法官提醒,即法官提醒和要求陪審團以法庭所展示的證人證言,相關證據以及雙方的辯論等為基礎作出判斷,不要受媒體報道的影響;5、隔離陪審團,即將陪審團成員與外界予以隔離,防止其成員接觸到外界信息;6、延期審理或變更審判地點,即為了盡可能減少媒體關注而采取的措施。然而面對大量且幾乎無孔不入的媒體記者、難以預估的陪審員心理活動以及對陪審員人身自由的尊重,這五項措施在實踐中往往并不能達到避免媒體審判的效果,辛普森案就是媒體審判的極端案例,由于案件主體的特殊性,導致大規模的新聞報道狂潮,最終失去了控制。
二、媒體觀點和法官意志為什么會存在沖突
對這一問題,筆者有兩點觀點:首先,媒體和法官對同一案件事實的認識存在差異。媒體主要通過記者采訪了解案件情況,消息來源較廣也較雜,而且消息沒有經過專門程序進行證實,而司法程序中所認定的事實,需要依照一定的程序進行驗證,例如專家鑒定,只有滿足法律程序的要求才能成為法律上的事實,在審判中發揮作用。其次,媒體和法官對同一案件的評判標準不同。新聞媒體從業者通常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對某一事件的評判標準主要基于社會常識和道德準則,而法官判案是依照法律程序和規定進行的,對案件的評價過程非常嚴格。因此,也可以說,媒體觀點和法官意志之間的沖突,實質上就是借媒體之口表達的公眾內心道德標準與法律的沖突。
三、中國的媒體審判和相關立法狀況
我國自建國以來也不乏在全國影響重大以致吸引媒體廣泛關注的案件,其中媒體搶先充當審判者而“未審先判”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比如張某案、劉某案、蔣某案等,雖然并不能肯定新聞報道影響了當時的審判活動,但媒體大肆渲染帶動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審判獨立,損害了司法權威。為了對新聞媒體出版業進行規范,我國曾在1988年出臺過《新聞法》草案,但最終沒有列入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之內,九十年代初,《出版法》幾次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沒有獲得通過,因此,我國目前還沒有任何的專門立法。
(一)憲法和法律中的原則性規定
《憲法》第35條和第126條分別對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進行原則性規定。《刑事訴訟法》第5條和《民事訴訟法》第6條進一步對司法獨立進行了規定。
(二)司法解釋及其他規定
1993年《人民法院法庭規則》第9條、第10條、第11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中僅規定了新聞記者應當遵守法庭秩序的相關內容,只有1985年由中宣部和中央政法委聯合發出的《關于當前在法制宣傳方面應當注意的問題的通知》和1997年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中才對媒體報道與司法獨立等問題的關系做出了規定。
可以看出,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中,位階高的法律規定幾乎都是原則性規定,針對性不強也不夠明確,而針對媒體報道和司法獨立的具體規定的法律位階過低,并且缺乏制裁性的規定,沒有實踐的可行性,保障力度十分低。
四、針對避免“媒體審判”的對策建議
(一)媒體從業者遵守職業道德,形成職業自律
媒體應該認清自己的角色——客觀地向公眾傳遞相關案件事實的媒介和公正地做出評論的發聲渠道,媒體自身的社會教化功能和輿論導向功能使其應處于理性的位置。媒體不是法官,不具備審理案件的專業法律知識和經驗,在不擅長的領域,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情況下,對法律事件肆意評論和引導輿論,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傷害,更是對我國法治社會進程的傷害。新聞報道不能代替法律事實認定,“未審先判”不能代表是在匡扶正義。
(二)完善法律法規,建立保障機制
根據上文對我國相關立法現狀的分析,筆者認為,應該加快相關領域的立法以填補空缺:1.制定專門的單行法規,例如《媒體法》,實現有法可依;2.提高現行相關具體規范的法律位階,加強法律權威;3.將嚴重通過輿論干擾司法獨立的媒體行為寫入刑法,并規定相應的懲罰措施;4.完善訴訟法,從程序法上規定降低媒體干擾的措施。
[1]展江.‘媒體審判’值得我們擔憂嗎?——對最高法接受輿論監督<規定>的稱許和商榷[N].南方都市報,2010-1-3.
[2]孫濤.對‘媒體審判’的再‘審判’[J].皖西學院學報,2010(1).
[3]湖北省漢江中級人民法院編.網絡輿論與法院審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D
A
2095-4379-(2017)16-0126-02
張梓恒,南昌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知識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