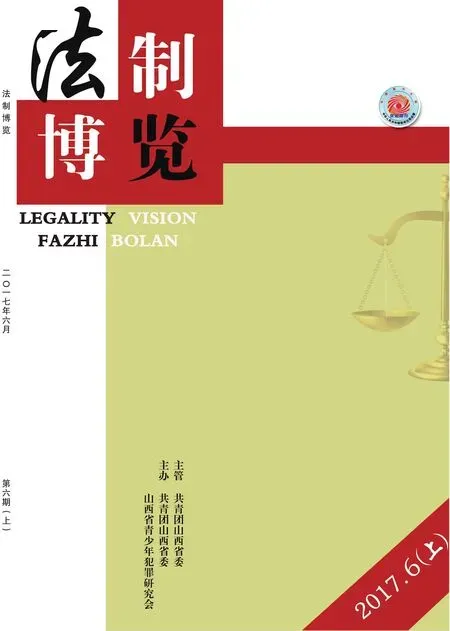從羅馬法“姘合”歷史發展談對我國非婚同居的啟示
張一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
?
從羅馬法“姘合”歷史發展談對我國非婚同居的啟示
張一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
古羅馬時期由于對于通婚權及不同社會階層通婚的限制,出現了區別于正當婚姻,指沒有配偶的男女缺乏婚意地、以穩定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姘合,而姘合作為一種現實大量存在的現象,在王政時期和早期帝國時期不為大眾所接受,沒有成為法律規制的對象,在基督教皇帝時期,雖然對其進行法律上的規則但持否定之意,優士丁尼執政期間,姘合的法律地位得到上升,被認定為低級婚姻。而后由于授予所有人享有與羅馬市民的通婚權,因此姘合的社會基礎消失被取消。姘合與現在非婚同居具有相似之處即婚意的缺乏,從而得以與事實婚區別,而非婚同居的社會基礎與姘合不同,因此不需要賦予其法律效力,而如何判斷是否具有婚意從而區分非婚同居與事實婚值得進一步探討。
姘合;古羅馬;事實婚;非婚同居
一、古羅馬時期姘合與正當婚姻區別
家庭作為古希臘時期和古羅馬時期社會的最基本單位,而家庭的組成通常以合法正當婚姻為基礎和連接點,此外因為與家父權相關的一系列對人的權利和對物的權利,合法正當婚姻在當時社會具有超乎現在的意義。羅馬法中成立正當婚姻建立在婚意和共同居住上①,婚意的外部具體表示為一是雙方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二是得以讓社會知曉雙方為夫妻身份。除此外,還需具備以下要件:1、年齡。男性年滿14周歲,女性年滿12周歲;2、男女雙方或有支配權的家父認可;3、均是未婚人。羅馬社會奉行一夫一妻制,因此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均未與他人建立婚姻關系;4、不得違反禁止性的規定;5、享有通婚權。②
而姘合區別于合法婚姻最大的特征是婚意的缺乏,姘合在羅馬法上是指沒有配偶的男女缺乏婚意地、以穩定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結合。姘合成立的條件與合法婚姻成立的條件大致相似,除不需要婚意及通婚權以外。羅馬法雖然嚴厲懲處通奸者,但姘合卻得以存在,“并不因為有姘合關系而構成通奸罪”③。
二、姘合產生的歷史原因
古代羅馬之所以會產生姘合制度,簡言以概之:主要是因為當時合法婚姻中規定無通婚權者不能結婚,而只有羅馬市民才享有通婚權。而當時大量異邦人的涌入,想結婚者迫于沒有婚姻權只能選擇姘合;即使有通婚權的人,若己身經濟拮據,男無聘禮女無嫁資也只能另謀出路選擇姘合;同時羅馬市民之間,身份地位懸殊者之間也不可通婚,身份尊貴的男子與地位低下的女子也不能成立合法的婚姻關系,也只能選擇姘合,故而姘合不是邪惡之物,而是羅馬合法婚姻嚴苛條件的結果。
三、古羅馬各時期“姘合”的歷史發展
(一)古羅馬王政時期
王政時期指從公元前754年羅馬建城到公元前509年這一時間段。在這個時期羅馬社會具有嚴格的社會道德風俗,甚至不允許個人保持單身的狀態,西塞羅在論法律中明確表示了對單身行為的反對④,更不論對于姘合的難以容忍。
(二)早期帝國時期的姘合
經過共和國后期的戰亂政權更迭以及早期帝國時代古羅馬力量的擴張,社會環境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的變化,使家庭的功能也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在風俗道德上的放松使得以往基于習慣法和道德風俗對婚外關系的否定態度也發生了變化⑤。從公元前27年到公元305年,隨著個人逐漸從傳統道德和社會需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結婚的理由也就多了起來⑥,姘合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但并未成為法律規制的對象。
(三)基督教皇帝時期和優士丁尼時期
從君士坦丁帝開始,基督教成為羅馬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婚姻神圣的態度下,基督教皇帝開始在法律上消滅姘合。他一方面通過諭令使得姘婦和她們所生子女的地位更差,禁止姘夫任何生前或者死后給姘婦及其子女財產上的權利;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法律積極地推動姘居的結合向婚姻轉變,使姘生子的地位準正。⑦在優士丁尼執政期間,姘合的法律地位得到上升,被認定為低級婚姻,一系列改造后姘合被界定為與任何地位的婦女無婚意地穩定同居。他廢除了因政治社會地位形成的婚姻阻礙,授予所有人享有與羅馬市民的通婚權,由此也消除了姘合最初發生的基礎。最終列奧皇帝將其廢除。
四、由姘合引發對非婚同居現象的思考
有學者將未婚異性未婚同居與事實婚、姘合混為一談,我認為姘合與未婚同居的共同點為婚意的缺乏,在外部表現上雙方不以夫妻互待,夫妻身份未得社會認可,但產生姘合的基礎是古羅馬婚姻制度中對身份地位的限制,然而隨著現在婚姻制度的變化,此基礎已經不存在了;而非婚同居與事實婚區別于后者中雙方具有婚意,只是由于結婚的形式要件不具備因此無法變為合法婚姻,因此三者不宜混為一談。而通觀各國立法例,多對事實婚有著相關的法律規制,事實婚在我國也大量存在,因此需對事實婚姻賦予法律效力無需贅述。但在是否需要對非婚同居進行特殊規制上,部分學者認為需要,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將事實婚與非婚同居概念混淆,其二原因為非婚同居現象大量存在。我認為,首先非婚同居不具有婚意從而與事實婚相區別,因此兩者不可等同,其次非婚同居雙方不以夫妻相待,共同居住只是基于雙方合意,正因為社會不認為雙方為夫妻關系,因此雙方的非婚同居行為并不對雙方以外的任何人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屬于私意自治的范疇,雙方之間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由民法調整即可。而當雙方有子女后,子女的有無可否作為同居雙方被社會承認為夫妻的關系的重要標準繼而將同居關系上升至事實婚關系需要進一步探討,即婚意的有無判斷標準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 注 釋 ]
①Ulpiano D.50,17,30 ad sab:Nuptias non concubitus,sed consensus facit.
②劉豫.淺談羅馬法婚姻制度[J].理論前沿,2013(06).
③[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M].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45.
④羅冠男.從事實狀態到法律制度——羅馬法中的“姘居”[J].私法研究,2014(02):78-93.
⑤羅冠男.從事實狀態到法律制度——羅馬法中的“姘居”[J].私法研究,2014(02):78-93.
⑥[德]奧托·基弗.古羅馬風化史[M].姜瑞璋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36.
⑦F.D.Busnelli,M.Santilli,Il problema della famiglia di fatto,in Una legislazione per la familia di fatto? Napoli,p.99(1988).
[1]徐滌宇.歷史視野下夾纏于非婚和婚姻之間的事實婚——兼論我國未來民法典對事實婚的應然構建[J].法學評論,2016(3).
[2]羅冠男.從事實狀態到法律制度——羅馬法中的“姘居”[J].私法研究,2014(02):78-93.
[3]羅冠男.從羅馬法的姘居制度看歐洲事實家庭的規制——與中國比較的視角[J].政法論壇,2015,33(5).
D
A
2095-4379-(2017)16-0221-02
張一帆(1997-),女,漢族,湖北襄陽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民商法系,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