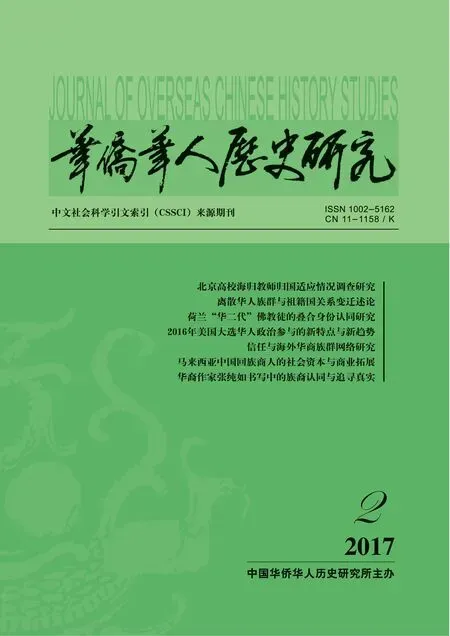族裔認同為基 追尋真實為本*
——對華裔作家張純如書寫的解讀
袁文卓
(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族裔認同為基 追尋真實為本*
——對華裔作家張純如書寫的解讀
袁文卓
(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美國華人;華裔作家;張純如;身份認同;南京大屠殺
論文從“族裔認同與書寫動機”、“追尋真實與伸張正義”以及“張純如的書寫啟示”三個方面對張純如的《蠶絲:錢學森傳》、《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及《美國華裔史錄》等英文作品的書寫脈絡進行解讀。認為張純如的英文書寫基于大量的口述采訪和歷史考證,其作品兼具文學和史學價值。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張純如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深植于心。書寫華人相關題材和探求歷史真實,構成張純如書寫的兩條基本脈絡。她試圖在文學和歷史之間達成某種書寫默契,去揭露一些本應被銘刻但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而被遮蔽了的事實。張純如不僅是一位暢銷書作家,更是一位歷史學家和人權斗士。
北美華裔①華裔不是法律概念而屬于民族學用語,指的是在住在國出生的第二代以上的華人;華僑是指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外籍華人是指已加入外國國籍的原中國公民及其外國籍后裔或中國公民的外國籍后裔。參見張秀明:《華僑華人相關概念的界定與辨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6年第2期。作家依據創作語言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作家采用漢語創作;另一類作家選用英語書寫。②部分華裔作家兼用漢語和英語進行創作,但本文主要依據創作語言的差異將其區分為漢語文學和英語文學這兩類。參見劉俊:《越界與交融:跨區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295~296頁。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總共用英文創作了三部作品,其中包括第一部處女作《蠶絲:錢學森傳》(Thread of the Silkworm)、為人熟知的成名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以及第三部講述華人在美國移民史以及奮斗史的《美國華裔史錄》(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又譯為《美國華人:一部敘述史》)。國內外學界關于張純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揭示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所具有的史學價值,[1]此類文章在張純如的系列研究論文中占據較大篇幅;二是從南京大屠殺國際傳播的視角出發,展現張純如在喚醒世界民眾對這一事件的集體記憶層面所具有的深刻意義;[2]三是國內外學界為紀念張純如女士而刊發的一系列追憶文章。[3]從以上研究成果看,無論是從南京大屠殺史學價值的視角來評析,還是從南京大屠殺國際傳播的視角進行闡發,或是對張純如人格魅力以及精神品格的追憶,這三種角度基本上都聚焦于社會歷史批評法以及外部研究的視角,但忽視了對作者族裔認同、書寫動機以及文本本身的內部研究。由于張純如的書寫基于大量的歷史考證和調查采訪,即便用嚴謹苛刻的學術標準來衡量張純如的英文著作,其作品的學理性也絲毫不遜于任何一位學院派研究者。她不僅是一位暢銷書作家,更是一位歷史學家和人權斗士。本文擬從族裔認同與書寫動機、追尋真實與伸張正義以及張純如的書寫啟示三個維度對張純如的書寫脈絡進行解讀。
一、族裔認同與書寫動機
(一)華人族裔與身份認同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曾指出:“身份從未統一且在當代逐漸支離破碎;身份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構建在許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論述、實踐及地位上的多元組合。”[4]的確,這種復合型身份在海外華人身上尤為突出。海外華人一方面竭力融入當地,另一方面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忘卻故鄉。這種深植于中華民族血脈的情感,不會隨著國籍的更換或歲月流逝而淡忘,相反只會歷久彌新。也正因為如此,書寫華裔題材與回望故鄉便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常見主題。
作家在其一生的創作過程中,可以源源不斷地汲取童年的“永不枯竭的資源”。[5]張純如出身于書香門第,祖父張乃藩③張乃藩,字筱武,1906年生,1930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8月更名國立南京大學)。1933年出任民國政府宿遷縣縣長。1937年春,張乃藩調任太倉縣縣長。同年8月,日軍侵上海,張乃藩在戰火中堅持支前工作3月有余,后隨軍隊撤退至四川。抗戰勝利后,張乃藩先后任鹽城、南通地區專員。1949年去臺灣任“教育部”主任秘書。1976年,張乃藩定居美國洛杉磯。參見朱愛明:《張純如的家族往事》,《今日淮陰》2015年4月7日。早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后任職于國民政府,他勤政為民、頗有口碑;而外祖父張鐵軍④由于張純如父母親都姓張,常有學者將其外祖父張鐵軍誤認為是張純如的祖父,而張純如的祖父實際上應該是張乃藩。參見[美]張盈盈:《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張純如》,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5-46頁。為國軍抗日將領,赴臺后曾擔任《中華日報》總主筆。張純如的父親張紹進和母親張盈盈均為哈佛大學博士。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有過在中國大陸以及中國臺灣接受教育的經歷。盡管童年時期對中國的印象不甚清晰,但這種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無疑加深了中國在張純如心中的印象。對她而言,中國遙遠而神秘,“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先人就來自那個神秘的古老國度。”[6]張純如正是在這樣一個富有中西文化氣息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而這種雙重文化視域下的審美體驗,對張純如后期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不僅體現為其后期作品中的華人題材以及華人歷史書寫,還體現為自覺捍衛華人群體在美國的基本權利。
(二)選題確立與書寫動機
《蠶絲:錢學森傳》的選題最早由編輯蘇珊·拉比娜(Susan Rabiner)確定。[7]該書不僅客觀敘述了錢學森為美國軍事技術進步所做出的貢獻,而且揭露了在“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盛行時期”[8]華裔科學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撥動了美國社會一直以來“種族歧視”[9]的那根敏感神經。回國后的錢學森奮發圖強,帶領其團隊幫助積弱積貧的新中國迅速躋身于火箭軍事強國地位,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所以張純如在這本傳記中還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美國主流社會應該對華人在美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公允肯定;如果仍然采取歧視華人或者亞裔的政策,最后很有可能會自食其果。
張純如書寫南京大屠殺這一沉重的歷史題材,無疑受到了多方面影響:如家族的遭遇、為新書尋找創作素材以及替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發聲等。這幾種創作動機之間實際上相互影響與作用:一方面,張純如的華裔身份使得她本能地將揭露日軍侵華暴行作為自身的職責和使命;另一方面,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冷戰”格局的影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并未得到徹底清算,這也為后來日本右翼勢力的復辟埋下隱患。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出版過程中,張純如就曾多次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10]而這些反過來則一直激勵著張純如的書寫。童年時期關于大屠殺的印象可視為張純如創作動機的原始基點。她曾坦言:“在我的整個童年,南京大屠殺一直深藏于心,隱喻著一種無法言說的邪惡。”[11]從懵懂時期聽聞父輩講述記憶里的南京大屠殺,經自己查證后的一無所獲,再到一次偶然機會目睹相關影像與父輩早年談論的南京浩劫竟如此吻合。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有一個由模糊到清晰,再到必須替受害者發聲的過程。
《美國華裔史錄》講述了貫穿3個世紀150多年的華人在美國的歷史。美國華裔史不僅是一部移民史與奮斗史,更是一部苦難史與屈辱史。作者在文中總結了華人自踏上美國本土以來在各個領域為美國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披露了在不同時期華人所遭受到的歧視與不公正待遇,尤其是當中美兩國關系處于冰點時華人所度過的艱難期。這部口述史不僅將書寫對象瞄準了杰出華人,也將視野聚焦于普通華人的奮斗歷程。起初,張純如也曾擔心這個選題是否過于寬泛,但疑慮很快消散,因為她不可能讓這樣一個探索她“自身民族歷史的機會”[12]白白溜走。進而言之,張純如身負一種使命去書寫一部誠實且符合史實的美國華裔移民史與奮斗史。為此,她曾在該書引言里對華人的優秀品質進行過總結。比如華人群體普遍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華人具有勤勞樸實的傳統、對家庭的無限忠誠以及富有創造性等優良品質。正是基于以上特質,華人能夠迅速地融入當地社會。而他們的后代也通常能夠在“醫學領域、法律領域、工程以及財政等領域迅速嶄露頭角”。[13]所以從某種程度而言,張純如的論述糾正了長期以來充斥于美國以及西方主流媒體中被扭曲了的華人形象。
從《蠶絲:錢學森傳》到《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再到《美國華裔史錄》的書寫,張純如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一以貫之。這不僅體現為其作品選題中的華人相關性,更表現為一種自覺將華人在國內(指的是華人在美國受歧視的事實)以及國外(發生在中國南京的大屠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作為書寫核心。這三本書的主題看似各自獨立,但依據作品內容以及作者的主旨闡發,可以推論出民族認同的問題。張純如一方面具有“美式的西方思想”,[14]但另一方面卻認為自己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正是在這樣一種族裔認同的驅使下,她不僅要替那些在二戰中被無辜殺害的同胞們呼喊,而且還要為飽受歧視的華人群體發聲。值得欣慰的是,美國國會于2012年6月正式宣布就《1882年排華法案》自發布以來“對華人造成的歧視和傷害”向華人道歉。[15]因此,張純如的書寫與對華人權利的捍衛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范疇,從而具有了某種普世價值。而通過對張純如作品的分析可以發現,除了對其自身族裔與身份認同的發掘之外,追尋真實與伸張正義成為解讀其英文書寫的另外一個維度。
二、追尋真實與伸張正義
有學者曾將北美華人英語文學作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美國華人作家如湯婷婷、譚恩美,她們的作品“符合美國人對東方的想象”,[16]所以比較暢銷;第二類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旅美作家如林語堂,他們筆下的東方敘事較為客觀;第三類則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留學熱移居國外的新移民作家,如哈金等。按照這種分類,張純如應歸為第一類美國華人作家。然而,這種劃分也并不能囊括第一類作家的所有創作模式。誠然,張純如關于中國(或東方)的第一印象離不開家庭教育,但她的書寫卻有著充分的調查、采訪以及追尋的過程。其作品主旨多聚焦于重大的歷史題材或是“非小說”,這也從客觀上決定了她的書寫必須依靠大量的歷史事實。因此關于第一類英語文學作家的劃分,實際上還可以再細化為兩類:第一類是以作品審美符合美國人對中國想象的湯婷婷和譚恩美為代表;而另外一類則是以張純如為代表的一批非虛構作家,他們往往以調查考證為基點,創作的文本多為歷史類題材或者非虛構類作品。
(一)張純如書寫的基本特征
張純如的書寫基于不斷的調查、采訪、口述直至抵達書寫對象的深層內核。王曉映指出:“張純如是作家,但不是虛構題材的創作人;張純如也被視為歷史研究者,但并不是學院派的學術分子。”[17]其實不論是張純如的作家身份,還是其歷史學者的敘述姿態,這都與她在大學里所接受的專業訓練以及早期的記者經歷緊密相關。即便是她將新聞報道所恪守的中立、客觀以及平衡的原則,有意無意地運用到自身歷史紀實類作品的書寫之中,但也絲毫未削弱其作品本身的學理性。相反,張純如的作品正是建立在“扎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的歷史著作。[18]尤其是對相關資料的收集以及證據鏈的把握較為充分,使得她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顯得游刃有余。
為確保《蠶絲:錢學森傳》書寫材料的可靠性以及論述的嚴謹性,張純如親自尋訪了錢學森生活過的地方,并成功采訪了錢學森的秘書、朋友甚至他的兒子錢永剛,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一些歷史細節問題,也在張純如的調研過程中逐漸浮出水面。如錢永剛在受訪中對其父當年“將生命中近20年的時間”[19]奉獻給美國,最后卻遭無禮驅逐表示憤怒和不解。正是這種從多重視角對人物的全景透視,使得張純如筆下的錢學森形象顯得圓潤飽滿,也更加貼近歷史人物的本真。這本傳記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學界對錢學森在美經歷研究的缺失,并從多維視角再現了一個“立體且個性鮮明”[20]的錢學森形象。
同樣,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資料收集過程中,張純如不僅親抵南京實地調研,而且還在中方人員的幫助下順利采訪到了親歷大屠殺的幸存者。從之前約翰·馬吉等傳教士日記中的記載,到與南京幸存者口中“證言的吻合”,[21]正是張純如不懈探尋的結果。也正是這種對真相的矢志不渝的追尋精神,《拉貝日記》以及《惠特琳日記》等一批重要證據才得以公之于眾。正如孫宅巍所言:“張純如是發現南京大屠殺核心資料《拉貝日記》的關鍵人物,她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讓歐美人士翔實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殺,在世界范圍內對揭露日軍暴行具有重要意義。”[22]這也正契合了張純如的書寫初衷,為沉默者呼喊,警醒世人勿重蹈覆轍。
在張純如的成長過程中,也曾遇到過類似美國白人同學提出的“當中美開戰,你將會支持哪一方?”[23]的尖銳問題,盡管當時的張純如還只是一位擁有華裔血統,卻從未踏足中國半步的美國人。而通過這個事例可以看出,華人在美國依然被視為異鄉人。這群擁有著多重屬性的群體,無時無刻不在找尋著精神的慰藉以及心靈的依傍。盡管從文化心理依存的角度而言,華裔青年一代對故土的思念遠不及父輩那么深刻,但作為一種中西文化碰撞后的選擇,面對華人群體在美國一直以來遭受的種族歧視,使得以張純如為代表的一批華裔作家,期待通過自己的筆觸替華人群體發聲。
(二)張純如書寫的獨特視角
對歷史真相的揭示,基于不懈的探索以及多重證據鏈之間的相互佐證。張純如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中主要采取了三種敘事視角—日本人的視角(施暴人的視角)、中國人的視角(受害者的視角)以及南京大屠殺發生時親歷日軍所為的歐美人視角(獨立第三方)。這三種敘述視角之間相互闡釋、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一個堅固的三角關系。一直以來,由于日本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采取拒不承認和刻意遮蔽的做法,中國作為受害方對此暴行的揭露難以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這段慘痛經歷如果通過第三方—歐美人士的視角講述勢必會更有說服力。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日記的披露,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①羅伯特·威爾遜1904年出生于南京,這里也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所以在南京危急的時刻,他選擇留了下來。威爾遜是當時留在南京唯一的一名外科醫生,南京大屠殺開始后,他在金陵大學的鼓樓醫院分秒必爭地為傷員做手術,他大概一個小時就要做一例截肢手術。后來,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為在南京所見的一切做證,他是真正把中國人當成同胞看待的外國醫生。參見[美]張純如著,譚春霞、焦國林譯:《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03~111頁。以及牧師約翰·馬吉②約翰·馬吉(John Magee),美國傳教士。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期間,馬吉擔任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他設立難民傷兵醫院,參與救援了數量巨大且面臨被屠殺的中國人,與20多位堅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譜寫了一曲動人的人道主義樂章。參見[美]張純如著,譚春霞、焦國林譯:《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8~140頁。等第三方證詞的出現,無疑從多個角度印證了南京大屠殺史實的真實性。在張純如看來:“對日本政府而言,需要做三件事情:首先是補償受害者,他們至今未有實際行動;其次對所有的南京市民做出一個誠懇的、正式的官方道歉;第三就是停止篡改教科書的行為。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刻意粉飾南京大屠殺,使得日本學生至今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仍十分有限。”[24]然而,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仍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如篡改教科書、打擊尊重史實的進步人士,以及抵制一些旨在揭露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書籍在本國的出版和傳播等,妄圖達到否認歷史、愚弄國民的目的。
《美國華裔史錄》的寫作基于華人在美國一直以來所遭受到的種族歧視。在歐美一些主流媒體以及相關書籍中,亞洲的女性往往被視為性工作者,而亞洲的男性也經常以渾渾噩噩的癮君子等一系列病態形象示人。從某種程度而言,“寫書也是消除偏見的一種方式”。[25]為撰寫這本口述史,張純如利用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說服華人社團向她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如反映個人以及家族移民史的信件、日記等。其實早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簽售期間,她就曾遇到過許多素未謀面的華人。在這些華人中,不僅有修筑鐵路時期遺留下來的華工后代,也有因學業而踏上美國留學的新移民;既有一字不識的工人,也有獲得過諾貝爾獎并任教于大學的著名學者。在張純如看來,書寫一部真實反映美籍華人生活,并以此來駁斥那些長期以來滲透于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中的“粗魯無禮的對中國人的成見”,[26]對她來說是一種職責。因此,《美國華裔史錄》的書寫已經超過了作為一位作家本身的職責和使命,從而上升到了一種爭取平等、捍衛正義以及呼吁人權的高度。這本口述史的出版有利于糾正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被扭曲了的華人形象,并進一步反思華人在美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張純如的文字給人的感覺通常不是一種愉悅的享受,而是凝結著歷史的沉重以及對人性的剖析。從一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到后來的暢銷書作家,由一名作家以及歷史學者轉變為后來的民權斗士,張純如一生擁有著“多重身份”,[27]然而,有一種精神卻貫穿了她的所有角色,這便是從內心生發出來的一種對華人族裔的認同、對歷史真相的追尋以及對正義的捍衛。正是這種精神,其作品才能夠最大程度地接近書寫對象的客觀真實,獲得積極的傳播效果。而她的個人價值以及歷史意義,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以彰顯。
三、張純如的書寫啟示
(一)自始至終確立一種高遠的寫作目標
張純如從寫作初始便深諳“文字不朽”的真諦,并在實際創作過程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審視其三部作品,無論從前期的選題確立到資料收集,還是從實地調研到最后書寫成稿,無不凝結著張純如的辛勤汗水。這種苛刻和嚴厲的自我要求,源于一種尊重史實的基本態度。如經過三年收集資料采寫而成的處女作《蠶絲:錢學森傳》雖未獲得較好的銷量,卻為張純如在美國作家界以及出版圈贏得了一個不錯的名聲,同時也為《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以及《美國華裔史錄》的書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張純如看來:“生命終將消逝,但書和文字可以流傳。....文字是留住靈魂的唯一方式。演講之所以令我激動,因為雖然演講者已然作古,長眠地下,但他們的精神卻世代流傳。對我來說,這是真正的宗教—最好的永生。”[28]文字不朽被張純如視為實現永生的終極方式,因此,她的創作自始至終都富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當我們用馬斯諾需求層次理論來解讀其書寫動機時,張純如顯然應歸屬為需求層次理論的最高層—即追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為了集中精力書寫,她通常選擇夜間工作、白天休息。這樣一方面錯開了與丈夫工作的時間差,另一方面也利于自己安靜思考和潛心寫作。為了激勵自己書寫,她甚至將南京大屠殺照片掛在書房抬頭可見的地方。每當讀到同胞的悲慘經歷,她都義憤填膺、感同身受。馬斯洛曾指出:“自我實現的人所獻身的事業,可以解釋為內在價值的體現和化身,而不是指達到工作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種手段,也不是指機能上的自主。這些事業之所以為自我實現的人所愛戀(和內投),是因為它們包含著這些內在價值。”[29]張純如對歷史真實的追尋和揭露本身便是一種個人價值的內在體現,正是這樣一個弱女子,她義無反顧地扛起了書寫一個民族屈辱歷史的重擔。
(二)對真實的不懈追尋以及對正義的堅定捍衛
在張純如第一部作品《蠶絲:錢學森傳》的書寫中,涉及到大量有關導彈技術的專業術語,如空氣動力學、噴氣推進以及航天技術、工程控制論等概念。而對這些術語以及相關知識的掌握,有利于作者更好地刻畫傳記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為此,她研讀了大量文獻,并向專業人士請教了相關的理論問題。因此,當我們閱讀到這些專有名詞的時候,絲毫不覺得生硬或者突兀。正是因為作者在書寫過程中早已將諸多復雜抽象的術語,簡化為一些淺顯易懂的概念。同樣,在《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里,張純如選取了施暴方日本人的視角、受害方中國人的視角以及作為獨立第三方歐美人視角進行對比闡釋以及相關佐證,尤其是在對相關細節的處理以及證據的把握方面令人信服。曾有一位名為羅納德·如塔卡的民族學教授公開宣稱:“華裔以及其他亞裔美國人,就好比是從不同沿海國家來美的外地人。”[30]可以看出,即便對美國高等學府的部分教授而言,華人以及亞裔也仍然被視為異鄉人。尤其是華人對美國社會的繁榮所做出的貢獻,也未獲得公允的肯定。正如張純如后來在接受采訪時所言:“寫那些具有普世意義的主題對我來說很重要。在我一生中,那些與正義被侵犯有關的主題總是能引起我的共鳴。”[31]這種對真實的不懈追尋以及對正義的堅守和捍衛,幾乎貫穿張純如創作的始終。而對普世意義作品的追求與書寫,則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作家的創作激情,這其中也暗含著一種責任和使命的驅動。
(三)關注歷史題材并自覺樹立一種社會責任感
以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題材的書寫為例。在張純如看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人數正在逐年減少,而趁著這些歷史的見證者尚在人世,她最大的愿望便是希望該書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激勵更多的作家以及歷史學者來調查幸存者的經歷。更為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夠以此“喚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擔他們對南京大屠殺應負的責任。”[32]這種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的客觀書寫,正是基于一種以史為鑒以及對社會歷史負責的態度。其實往往真正令人感到恐懼以及羞愧的,并不是戰爭以及暴行本身,而是我們拒絕反思,以及“拒絕懺悔”。[33]而反思以及懺悔又正好與張純如在書中經常引用埃利·威塞爾的那句名言—“遺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相互呼應。真實的歷史被講述,邪惡得到懲罰,正義得到伸張,這便是張純如一直奉行的創作理念。關于批判,法國社會學家福柯認為:“批判是主體對權利的質疑,是主體的反抗和反思,是對主體的屈從狀態的解除。從根本上來說,批判是不被統治的藝術。”[34]批判不僅僅體現在主體對權利的反叛和消解,更是知識分子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使命,以及對被遮蔽事實的公開反對。因此,南京大屠殺書寫的深層意義便在于重鑄民族精神,以及喚醒集體以及個人對這場災難的“復合記憶”。[35]尤其是在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36]的當下,只有深層追溯人性的復雜,才能從“啟蒙現代性的源頭”[37]探究人類本性的根源。此外,也正由于張純如的不懈探索,才為后來構建這一集體記憶的小說家提供了可供參考和書寫的人物原型,比如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的諸多人物,以及約翰·拉貝、明妮·魏特琳的私人日記最早便是由張純如率先發掘。而在《美國華裔史錄》的創作過程中,張純如同樣秉承了正義、客觀以及追求真實的創作原則,將華人在美國的移民史及屈辱史公之于眾。因此,張純如的英文書寫具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以及反思性。
如果說高遠的寫作目標(或書寫動機)是張純如文學創作的前提,那么書寫華人相關題材以及對歷史事實的不懈追尋,則構成張純如書寫的兩條基本線索。二者基于一種個體對社會歷史的高度責任感。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身份認同與追尋真實相互補充、互為闡釋,辨證統一于張純如的英文書寫中。
四、小結
國內外學界關于張純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南京大屠殺史學價值以及意義的梳理、關于南京大屠殺國際傳播價值的評析,以及對張純如女士本人精神價值的追憶。相較《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影響而言,國內外學界對張純如其他兩本著作的研究尚處于初期。當然這不僅是因為另外兩本英文著作翻譯為中文稍晚(《美國華裔史錄》尚未翻譯為中文),而且也與《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巨大影響幾乎蓋過了其他兩部著作有著較大的關系。當我們將張純如的三部作品放在同一維度去考察,作家的族裔認同與書寫動機以及追尋真實與伸張正義是我們進行解讀的核心。而通過對這兩個維度的闡發上升到對張純如書寫啟示的總結,則為我們全面審視張純如及其英語書寫提供了一條解讀路徑。不同于一般的小說家,張純如的書寫基于大量的歷史和考證、采訪和口述,其作品深層的文史敘事意義往往超越了單純的文學價值。從某種程度而言,張純如并非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家,而歷史學家的身份似乎更為貼切。她的書寫動機融個人、民族以及華人族裔的“自我反抗”為一體,因而具有了一種敘事張力,隱藏在這種敘事視角背后的是一種對正義以及平等的捍衛。尤其是在日本官方仍然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美國華人歧視現象依然存在的當下,從多維度跨視角去解讀張純如及其英文書寫,對于我們厘清她的書寫脈絡并在整體的視域中去把握華人書寫大有裨益。從這個角度而言,張純如及其作品仍然值得我們不斷探索和深究。
[注釋]
[1] 參見楊夏鳴:《傾情注翰墨,筆端揭真相—華人女作家張純如在實地調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南京史志》1999年第1期;張連紅:《歷史無法忘卻:張純如與她的〈南京大屠殺〉》,《鐘山風雨》2004年第6期;王衛星:《為了歷史不被人們遺忘—張純如南京之行》,《檔案與建設》2005年第1期;孫英春:《張純如:她用生命照亮人類的歷史》,《勞動保障世界》2008年第1期;Damien Kinney, “Rediscovering a Massacre:The Filmic Legacy of Iris Chang’s The Rape of Nanking”,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1, February 2012, pp.11-23;等等。
[2] 參見徐藍:《“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張純如和她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世界知識》1998年第11期;文潔若:《記住張純如和相關的書—抗戰勝利60周年有感》,《博覽群書》2005年第2期;辛潔:《張純如與南京大屠殺的國際傳播》,國際關系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王霞:《不能遺忘的創傷—讀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Christopher Barnard, “The Rape of Nanking in Japanese high school Textbooks:History texts as closed texts”, Revista Canaria deEstudios Ingleses, No.40, 2000, p.156;等等。
[3] 參見劉美玲:《〈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張純如精神的延續》,《藝術評論》2009年第6期;孫宅巍:《我與英文版〈南京大屠殺〉著者張純如的交往》,《日本侵華史研究》2013年第4期;David Gergen, Iris Chang and the Forgotten Holocaust(《張純如與被遺忘的大屠殺》),2007年10月中旬于美國紐約出版;楊夏鳴:《我與張純如的交往》,《江淮文史》2015年第2期。
[4] [英]斯圖亞特·霍爾、保羅·杜蓋伊編著,龐璃譯:《文化身份問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頁。
[5] 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6頁。
[6] [26][28][31][美]張盈盈著,魯伊譯:《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張純如》,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7、250、345~346、346頁。
[7][19]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New York:Basic Books, 1995, pp.6, 15.
[8][美]田長焯、裴高才:《田長焯:見證海外華人自發維護抗戰史實真相》,《世紀行》2014年第5期。
[9][美]梁伯華:《正義的天使:張純如》,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頁。
[10] JinMing Chang, A Shadow of History: A Case Study on The Rape of Nanking from the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The Master’s thesis of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 2009, p.1.
[11] [32][美]張純如:《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ⅩⅩⅥ-ⅩⅩⅦ、ⅩⅩⅩⅠⅠⅠ頁。
[12] [13][23][25][30]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A Narrative History, NewYork:Penguin Books, 2004, pp.15, 12, 14, 15-16, 14.
[14] Mingli Yao ,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Self-Identity: Critiques of Iris Chang’s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The Master’s thesis of Tamkang University , 2006, p.1.
[15] 曹雨:《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的立法過程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6] 陳祖群、肖寶鳳:《對話:北美華人文學中的漢語文學與英語文學》,《華文文學》2008年第1期。
[17] 王曉映:《張純如—從一名卓越的記者到一位非虛構作家》,《傳媒觀察》2012年第6期。
[18] 趙文書:《跨世紀華裔美國文學非虛構作品評述》,《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20] 雷雨:《有感于張純如筆下的錢學森》,《軍事記者》2010年第3期。
[21] 楊夏鳴:《傾情注翰墨,筆端揭真相—華人女作家張純如在實地調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南京史志》1999年第1期。
[22] 孫宅巍:《我與英文版〈南京大屠殺〉著者張純如的交往》,《日本侵華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4] David Gergen, Iris Chang and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February 1998), http://www.pds.org/newshour/bb/ entertainment-jan-june98-chang_02-20.
[27] Paula Kamen, Finding Iris Chang:Friendship, Ambition, and the Loss of an Extraordinary Mind, Philadelphia:Da Capo Press, 2007, p.16.
[29] [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超越性動機》,石磊編譯:《馬斯洛談自我超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41頁。
[33] 楊婷婷:《論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人道主義內蘊》,《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34][法]米歇爾·福柯著,汪民安譯:《什么是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0頁。
[35] Damien Kinney, “Rediscovering a Massacre:The Filmic Legacy of Iris Chang’s The Rape of Nanking”,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1, February 2012, pp.11-23.
[36] Christopher Barnard, “The Rape of Nanking in Japanese High School Textbooks:History Texts as Closed Texts”,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No.40, 2000, p.156.
[37] 洪治綱:《集體記憶的重構與現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殺〉、〈金陵十三釵〉和〈南京安魂曲〉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10期。
[責任編輯:密素敏]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s Basis, Pursuit of Historical Reality as Nature—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Iris Chang’s Writing
YUAN Wen-zhuo
(Chinese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merican Chines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ris Chang; identity; The Rape of Nanking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writing contexts in Iris Chang’s “Thread of the Silkworm” ,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and other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thnic identity and writing motivation”,“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justice” and “Iris Chang’s writing inspiration” . It indicates that Iris Chang’s English writing has bot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based on abundant oral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As a n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Iris Chang’s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is profoundly rooted in her heart. Writing Chinese related themes and exploring the truths of history constitute Iris Chang’s two basic writing contexts. She tried to achieve tacit understanding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expose the facts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scribed but obscur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Iris Chang is not only a best-selling author, but also a historian and a fighter of human rights.
I711.074
A
1002-5162(2017)02-0071-08
2016-11-07;
2017-03-31
袁文卓(1989—),男,湖北荊州人,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華文文學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社會啟蒙與文學思潮的雙向互動”(項目批準號:16JJD750019)中期成果;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史研究”(13ZWA001)中期成果。感謝《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匿名評審專家及編輯部老師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