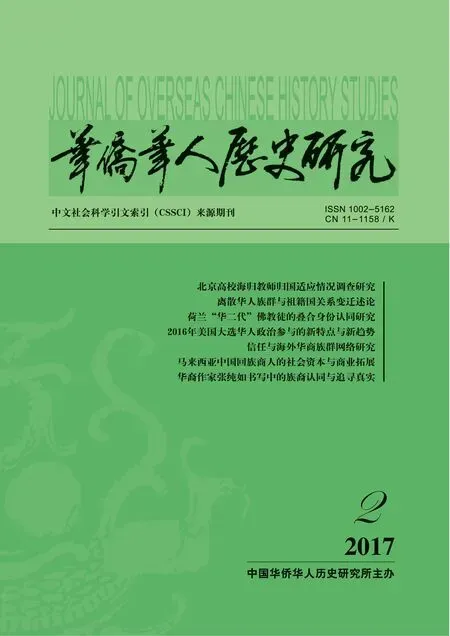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情況調查研究
——以北京高校為例的分析
史興松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100029)
分析探討
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情況調查研究
——以北京高校為例的分析
史興松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100029)
人才引進;北京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
論文利用歸國適應理論,通過分析三所北京高校的30名海歸教師深度訪談結果,從環境因素、自身因素和組織因素三個方面探討了他們的歸國適應情況。結果表明,幾乎所有海歸教師在回國初期都感受過不同程度的歸國適應困難,回國時間越長,歸國適應困難越有所好轉。適應過程中,很多教師產生過較強烈的疑惑、不滿、焦慮等負面情緒,這不僅會降低海歸教師的心理適應、社會文化適應和總體生活質量,還會較大程度影響其工作質量。為確保高校人才引進的效益,有必要充分了解海歸教師群體的歸國文化適應狀態、遇到的困難及相關訴求,從政府、學校和個人等多個層面共同探尋解決路徑。
隨著世界經濟格局不斷變化及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人員選擇回國就業,他們被社會賦予一個特定名稱—海歸。截至2015年年底,我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221.86萬人,其中2015年回國40.91萬人,同比增長12.1%。[1]
盡管近年留學回國人數逐年增長,但已回國的海歸有相當一部分(超過25%)在國內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歸國適應困難。[2]許多海歸因成果無法轉化、單位或市場不認可或其他種種適應困難而被迫撤離,甚至選擇重新出國。這些歸國人員的適應問題不但會影響他們自身的工作績效和生活滿意度,而且其適應成敗的“溢出效應”①溢出效應指一個人或組織在進行某項活動時,不僅會產生活動所預期的效果,而且會對之外的人或社會產生影響。會影響到其他留學人員的歸國意愿。其中,高校海歸教師因處于知識與信息傳播的前沿,其思想認知狀態會對在校生乃至更廣泛的社會群體產生重要影響。因而,有必要了解高校海歸教師的歸國適應情況,探討如何幫助他們盡快實現歸國適應,以達成國際化人力資源管理的效益最大化,而切實做好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隨著國家對海歸群體重視程度日趨增強,近年來國內學者針對海歸群體的研究也愈來愈廣泛深入。例如,有的學者探討海歸對企業創新發展及經營業績的影響,[3]有的對高校海歸教師的生存現狀、思想狀況或課堂教學策略等情況展開調研。[4]已有研究從多維角度為我們了解海歸群體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實證支持,但基于完整的跨文化適應理論視角,對海歸教師群體進行的相關研究還不夠充分。本研究將汲取較為成熟的跨文化適應研究理論精華,建立理論框架,以三所北京高校的海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回國后的適應情況、遇到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進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應對措施。
一、理論框架
歸國適應(Readjustment 或reentry adaptation)研究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5]主要從跨文化交際學、社會學、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等視角探討個體從國外回到祖國后交際行為的演變歷程、表現形式及轉變結果,為理解人們在歸國適應過程中表現出的復雜現象及階段性特征提供線索。
學者們認為,歸國適應的類型具有多層面特征。[6]布萊克(Black)及其同事將歸國適應分為一般性適應、工作性適應以及互動性適應。[7]沃德(Ward)等人將跨文化適應劃分為兩個層面,即心理適應和社會文化適應。[8]威利(Valle)等認為歸國適應可劃分為工作適應和總體適應。[9]雖然所用術語不同,但究其根本,學者們大多是從心理適應、社會文化適應(包含一般適應和互動適應)和工作適應的角度對歸國適應進行多維探討。
歸國適應影響因素大體可以劃分為三類:環境因素、自身因素和組織因素。其中,環境因素主要指歸國適應過程中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因素,如文化因素、社會支持以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等;自身因素包括性格因素,人際溝通能力,對祖國和他國文化的態度,歸國期望、意愿與動機以及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歸國時間長短等人口統計學因素;[10]組織因素則與組織管理有關,主要指工作角色和組織支持。[11]以往相關研究的理論框架可概括如下(見圖1)。

圖1 歸國適應研究理論模型
本研究擬在以上理論框架指導下,通過實證調研,針對如下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一是了解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情況、遇到的問題以及適應類型;二是識別影響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的多元因素;三是探討促進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的有效措施。
二、研究方法
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參考上述理論模型構建訪談提綱,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對來自3所不同高校(分別為985、211及普通高等院校)的30名海歸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訪談集中在2016年9月份進行。訪談對象選擇標準為:一是來自上述三所院校的在職任課教師;二是具備一年以上留學經歷并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參與調研人群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
由表1可見,受訪教師中男性7人,女性23人。①因訪談對象選取主要采用就近原則,受研究者學科背景局限,研究對象主要為文科背景,因而受訪者女性偏多,以上局限期待能在未來研究中有所改善。在海外攻讀博士(博士后)者17名,碩士13名。出國平均年限為4.68年(其中最長11年,最短1年)。留學國家大部分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美國10名、英國6名、法國3名)。②這與2016年10月13日教育部統計公布的中國留學生去向國仍以美、英、澳、加、法、德等西方國家為主的總體分布趨勢相符,具體參見http://www.01hn.com/redianshijian/459824.html。回國平均時間為6.6年。總體工作適應程度良好(M=4.83〉均值3.5)。回國后,認為自身現狀未能滿足回國前期望的(即期望〉實際)有10人,占33.3%。其他人認為現狀與自身期望相符或超出期望。下面將基于訪談結果,以歸國適應的理論框架為脈絡,對受訪者反映比較突出的歸國適應問題及影響因素進行梳理及總結研究。
三、調研結果
下文將參照歸國適應研究理論框架(圖1),主要從環境因素、自身因素和組織因素三個維度分析總結影響海歸教師歸國適應的各項因素。
(一)環境因素
1. 文化因素
以往研究指出,文化因素是影響歸國適應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中,絕大部分受訪海歸教師曾在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占總數的86.7%),而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迥異。很多海歸教師出國時比較年輕,在適應海外文化沖擊的過程中,較快接受并內化了國外的行為方式、生活習慣、思維模式乃至價值觀念。回到祖國時,他們已經形成的新的文化思維模式與國內的思維方式時而會出現沖突。在祖國感受到的文化沖突,對海歸的心理沖擊甚至會超出海外文化沖擊帶來的心理壓力。
本研究中,海歸教師對文化差異的不適應在歸國初期反應明顯。在表層文化層面,受訪者普遍對國內的環境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教育資源不均衡等問題存在不同程度的適應困難。例如,若干教師回國初期因環境污染問題生病,甚至得肺炎或哮喘;食品安全問題使有的教師在外吃飯有所顧慮;教育資源不均衡使很多教師為子女的入托或入學問題感到焦慮、對國內的應試教育體制無可奈何,有的教師對孩子究竟應該接受中式還是西式教育左右為難。
在深層文化層面,海歸教師在回國初期,對國內比較復雜的人際溝通模式較難適應。比較共性的問題是,受西式交際方式影響,海歸教師傾向于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通常認為遇見問題時直接指出問題、表明觀點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但在國內環境中,他們逐漸認識到這種交際方式容易遭到誤解,甚至無意中造成矛盾。意識到這一問題后,他們開始對自己的交際方式產生疑慮,感覺無所適從。幾位教師不約而同地表示,發現問題后逐漸學會盡量少說話,轉而默默觀察別人的說話方式,以體會更適合國內的交往模式。
在教學中,有的教師試圖將西方較受歡迎的以學生為主體,鼓勵批判性思維、提倡互動教學、強調在“做中學”等教學方式和教學理念移植到國內課堂,但國內傳統教學更接受以教師為主體的“傳道—授業—解惑式”的教學模式。有部分學生不能很好適應海歸教師的教學方式,在評教時給出負面評價,而學校評教時往往倚重學生評價結果,部分教師因此被迫調整教學模式。
2.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影響歸國適應的另一重要環境因素。長期留學在外,很多海歸回國時面臨建立新的人際關系的問題。在人際關系受到高度重視的中國社會,工作內外的社會環境如果對海歸表現出友好、支持和尊重,則會使其心理壓力減小,促其較快產生歸屬感;反之,如果所處社會環境對海歸不夠友好寬容,甚至出現排斥情況,那么,他們在適應過程中就會感受更多困難及心理壓力。對海歸來說,工作中上級態度和同事態度可能會對工作適應和互動適應產生影響,甚至還有可能對總體適應產生溢出效應。此外,家人是否支持、包容對其歸國適應也會產生重要影響。
訪談中,海歸教師對社會支持問題感觸頗深。比較普遍的反映是,回國后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是自己逐漸適應的后盾和保障,但有些家人對個人生活的過度干預(如婚姻問題)給他們帶來額外困擾。在單位中,受西方較為簡單的人際關系模式影響,海歸教師較難理解國內復雜的人際交往模式,這使他們難以快速融入國內的交際圈、科研圈。如何妥善處理人際關系對相當一部分海歸來說造成額外心理困擾。
在工作環境中,單位對海歸教師取得教學科研成果的期待值較大。在這種環境下,取得突出成績的教師往往因為擠占有限資源,引起同事的反感乃至排擠;而不能快速取得科研成果的教師也倍感壓力。在提及科研壓力問題時,眾多教師提出的一個顯性甚至共性的問題是:在國外,只要觀點新穎、有培養價值或成果質量過硬,就能贏得支持和尊重,而國內根深蒂固的“等級”以及“關系”效應,使得諸多海歸“望機會興嘆”。長期在海外求學,使得海歸缺乏國內學術圈潛在、微妙但又極其重要的師承關系、人脈關系,這使相當一部分教師在學術發表、晉升、項目申請中,不是因為個人業務能力而是因為不可控的人情因素受挫,其工作積極性難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對于這一問題,有位教師指出,他回國后曾在兩個不同單位任職,發現不同領導的風格對單位整體工作環境以及對海歸教師的支持力度均產生重要影響。
3. 當地生活情況
以往研究表明,歸國人員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等當地生活環境也會對其歸國適應產生影響,如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生活消費很高、地理位置和生活環境不盡如人意,歸國適應就會受到影響。
本研究受訪教師均在北京高校任職,北京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雖在國內存在優勢,但物價水平較高,很多教師認為“生活消費比國外高”,尤其住房問題成為非常顯性的問題。對于回國晚、年紀輕的教師尤其構成巨大生存壓力。例如,教師Y提及,剛回國前三年不停變動租房地點,不停搬家,直到第三年底買到房子,才感覺真正安頓下來;教師Z回國已有10年,但因各種原因至今沒買到住房,而且因為所租用周轉房離學校太遠,大多時間住在辦公室。居無定所無疑會造成適應困難,不乏有年輕海歸教師最終因房價問題,選擇退居二線城市。
(二)自身因素
另外,歸國適應還與個人自身因素密切相關,包括性格因素,人際溝通能力,文化態度,歸國期望、意愿與動機以及人口統計學因素。
1. 性格因素
克萊曼(Coleman)指出,星級員工的優秀表現,90%都應歸功于其情商,而非其認知能力。[12]歸國者的情商,也即性格因素,在很多情況下比歸國者的業務素質更為重要。性格因素決定或影響著歸國者在面對文化沖突時是否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是否能以積極主動的態度重新融入到祖國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以及是否能正確處理歸國適應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本研究中,樂觀、開朗、外向的教師適應得明顯快一些,他們回國后很快交到新朋友,對生活的滿意度大幅提高。相反,性格內向者則感受到較大的適應困難。
2. 人際溝通能力
海歸在新環境中與他人的接觸和交流不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其文化適應,同時也是歸國者在當地適應程度的一個很重要的指向標。如果能夠在新的社會群體中迅速建立社交網絡、友好順暢地與當地人接觸、交流,會有效減輕歸國者在新的社會群體中的孤獨感以及歸國適應帶來的壓力。[13]
這一點與上文提及的性格因素有一定關系,但同時也與海歸特有的身份認同有關。例如,相當一部分教師提及自己遇到海歸特有的文化適應問題和感觸時,大多時間靠自己慢慢消化調整,不知怎樣與同事溝通,時常感覺有苦無處說,有苦說不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在新單位的人際溝通與適應。
3. 文化態度
貝利(Berry)及艾肯(Aycan)等學者均指出,跨文化適應過程中,人們對待祖國和他國文化的態度會對其文化適應產生具體影響。[14]貝利使用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指代個體在與兩個不同文化群體接觸過程中文化及心理上的雙重改變。對于海歸來說,回歸祖國后,其文化態度及交際行為究竟是親中、親外、折中,還是與兩邊均疏遠,對其歸國適應會產生重要影響。
調研中發現,受訪教師大多在文化態度上屬于親中或折中態度,這部分教師目前總體適應情況良好。相對而言,適應調整程度較差的教師更容易滿腹怨言、經常拿國外文化與國內文化做比對,對國內文化負面意見居多。在文化調適過程中,親外思想較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他們對本土文化的再適應過程,這類教師的總體適應情況至今仍不佳。
4. 歸國期望、意愿與動機
以往研究表明,海歸回國前對歸國后工作生活的期望與現實是否匹配也會影響其歸國適應。[15]歸國期望較低時,實際生活滿意度就較高,反之感受的適應困難較多。另外,歸國人員是否有歸國動機和意愿,動機和意愿是否強烈,對歸國適應也會產生影響,通常歸國動機和意愿越強,越有可能主動適應社會文化環境。
本次調研結果表明,歸國期望、意愿和動機對歸國適應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接受訪談的大部分教師屬于主動選擇回國就業,但也有個別教師是因為外界因素(如為了家人)回國,自身并沒做好回國心理準備,此類教師所體會的適應困難相對明顯。從歸國期望角度看,本次調研中,出國時年齡較小,畢業后很快自主選擇回國的教師適應困難相對較小。他們原有期望通常并不很高,對自己畢業后能在北京高校找到教職本身已經覺得達到心理預期,對于按部就班爭取職稱晉升、逐漸提高待遇等,覺得無可厚非,相關心理壓力較小。同時,因為年紀較輕,相對而言感受到的周圍環境壓力乃至排擠都不甚明顯。相反,對于人到中年,出國前已在國內高校工作過一段時間,為提高自身業務素質,中途撇家舍業出國留學的教師,歸國適應時面臨的壓力明顯較大。他們出國前在教學崗位上已有積累,回國后發現當年的同齡人在工作崗位上已確立學術地位或行政地位,而自己卻因為出國求學反倒處處落后于人,此時如果在學術發表、職稱晉升、項目申請等問題上受挫,往往出現非常強烈的心理沖擊與波動。
5. 人口統計學因素
跨文化領域學者關注的人口統計學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歸國時間長短等。本次調研中,人口統計學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對歸國適應產生影響。年齡小的海歸雖然在單位適應相對順暢,但因剛進入工作崗位,經濟基礎薄弱,受物價尤其是房價沖擊明顯。女性教師因長期攻讀博士學位,如工作后仍未成家,會感受到來自家長及社會環境的較大壓力。年齡較大的教師如住房問題已解決則生活相對穩定,但沒解決住房者則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相比較而言,學歷相對低的教師科研壓力相對較小,學歷高的博士或博士后科研壓力較大,因科研壓力引起的不適感更強,因職稱晉升不順引起的焦慮感更重。另外,歸國時間長短對適應狀況影響較大,大多受訪者反映剛回國的第一、二年所感受的適應困難最強烈、明顯,之后逐漸好轉。
(三)組織因素
近年來,學者們越來越關注組織因素的影響力。帕克(Parker)與麥克伊沃(McEvoy)認為,組織因素包括組織成本和收益、組織提供的工作機會、歸國人員與工作單位的聯系程度、回國時提供的幫助、工作任命(角色清晰度、工作挑戰性)、歸國人員培訓、組織文化、組織規模等因素。[16]艾肯(Aycan)研究提及的組織特征包括公司機構價值取向、戰略計劃、組織支持、本地文化多樣化培訓等。
對于本研究中的海歸教師而言,一個比較顯性、屢次被提及的與組織因素相關的問題是:回國后與國外學術圈的聯系逐漸削弱、難以為繼,而與國內的學術圈和學術規范又難于迅速接軌,于是感覺夾在中間,有種失重踏空的感覺。
具體而言,海歸教師在國外學習的科研方向、研究方法、理論流派與國內研究傳統容易存在較大差異。剛回國時,有相當一部分人感覺自己駕御中文學術語言的能力有限,論文寫作方式與國內不接軌,研究主題不屬于國內熱點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研究法)在國內期刊發表幾率低,于是,研究成果在國內發表機會很少。國際發表固然是一條途徑,很多海歸也的確在國際發表方面成為所在高校的主力軍。然而,國際發表往往挑戰性更大,發表周期更長,而國內高校對教師的評價機制通常重視數量高于重視質量—即雖然有高質量高級別論文發表,但因客觀因素(如發表周期長、難度系數高),導致其國際論文發表數量與同行國內論文發表數量相比處于劣勢,于是在評職評優方面容易處于劣勢。
為迎合國內高校評價機制,相當一部分教師被迫擱置國外所學,轉而揣摩國內學術熱點、方法、學術規范等,國外所學沒有得到用武之地。且向國內學術范式轉型過程中,因不熟悉國內研究范式而大多苦苦“自學”摸索,耗時低效。繼續保持國際發表路線的教師,有部分人為追求“量”而放棄“質”,例如,發表大量SSCI期刊書評,求功利而忽視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與追求。
還有教師反映,回國時間越長,發現維持國際發表能力越難。一方面,受以上因素影響,教師投入較多時間研究國內科研模式,受時間精力限制,教師對國際最新文獻及熱點話題跟蹤乏力;另一方面,以前在國外時,他們經常通過學校內部交流或通過參加頂尖學術會議了解最新學術動態,但現在所屬學校一則學者內部交流尚未形成常規,另外對出國開會管束非常嚴格、手續繁瑣,且對教師會后發表要求過高(如要求會后發表1篇SSCI期刊文章才能報銷參會費用),導致教師很少或幾乎放棄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以上因素綜合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海歸教師對國際學術熱點的跟蹤,而其在國內發表又存在“先天不足”,于是部分人會感覺兩腳踏空、憂心忡忡。
除了主攻科研的教師有諸多不適外,主攻教學的海歸教師也有自己的苦衷。例如,教師H反映,自己出國前曾在國內高校任講師4年,在美國讀博期間一直在學校做助教,博士畢業后在另一所美國高校任助理教授3年。前后有11年教學經驗。然而,回國后,國內高校只承認其在國內任教的4年工齡,在美國高校的工齡不被認可,目前該教師仍為講師,且因近年專注教學,科研發表數量不足,導致其講師級別與新入職的年輕人級別一致,屬講師最低級別。該教師感受到極大不公,情緒極其低落。與此類似,部分海歸博士在科研發表方面難以達到學校要求,而其他工作業績、能力和資歷又得不到充分認可,從而產生消極情緒,這無疑會對其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益產生負面影響,有違高校引進海歸教師的初衷。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理論回顧與實證調研,考察了高校海歸教師歸國適應的總體狀態及影響因素。訪談結果表明,幾乎所有海歸教師在回國初期都感受過不同程度的歸國適應困難,回國時間越長,歸國適應困難越有所好轉。適應過程中,很多教師體會到較強烈的疑惑、不滿、焦慮等負面情緒,這不僅會降低海歸教師的心理適應、社會文化適應和總體生活質量,還會較大程度影響其工作情緒和工作質量。為確保高校人才引進的效益,有必要充分了解海歸教師群體的歸國文化適應狀態、遇到的困難及相關訴求,并探討有效解決方案。本文依據調研結果,認為歸國適應問題需從政府、學校和個人等多個層面共同探尋解決路徑。
(一)國家層面:提供物質保障
國家及教育管理部門應充分意識到,大多數海歸是在發達國家留學后回到國內任教。我國近年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有長足進展,但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內的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污染問題、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居住條件及高房價問題等,會使相當一部分海歸教師在回國初期面臨嚴重困擾。國家近年來大力鼓勵并吸引留學人員回國,與此同時,怎樣才能提供充分合理的物質保障,幫助引進人才迅速解決基本生活問題,使其能夠盡快安居樂業、全身心投入工作,這些是需要國家及教育管理部門亟待思考并采取有效措施著力解決的問題。例如,為解決海歸教師的安居問題,政府可考慮為引進海歸教師提供穩定的周轉房,或為其申請限價房或自住房提供綠色通道或相應政策保障。針對海歸子女教育問題,政府也可考慮為其子女入學提供適當政策傾斜,助其子女有機會享有良好教育資源,從真正意義上為其解除后顧之憂。
(二)學校層面:給予精神支持和組織支持
調研表明,海歸教師面臨歸國適應困難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共同性。例如,歸國初期(近一年左右)往往是其適應困難最明顯的時期;長期海外留學使很多教師接受并內化了所在留學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及行為規范,對國內價值觀念及社會行為需要逐漸理解適應。很多教師感受到各種困惑,但因沒有適當的溝通渠道而情緒低落、自我懷疑,不了解這種現象對海歸而言比較常見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針對這一問題,學校應有充分預知并且予以理解。管理者應了解這一群體教師可能遇到的歸國適應問題,并有意識地提供相關支持和幫助。例如,學校可以通過組織座談的方式,為海歸教師提供表達訴求、尋求解決方案的溝通渠道和平臺;可以組織講座,請成功適應國內環境的海歸教師為新入職的海歸教師講解適應過程、經驗及建議;可以定期組織海歸教師聯誼會,使有共同語言、有相近訴求的群體有彼此交流、互相學習的平臺;也可以借助新媒體(如建立海歸教師微信群),使大家能夠互通有無,彼此互助。因為這一群體對很多問題互有共鳴、感同身受,互相交流能增加心理疏導的溝通渠道。此外,針對海歸教師對國內學術環境、學術網絡的不熟悉、難融入問題,學校可請相關領域成熟學者做相關講座,幫助海歸教師了解情況,鼓勵他們積極尋求解決方案。例如,通過積極參加學術會議,拓展國內學術圈認同度;積極參與校內學術團隊科研項目,以盡快了解國內學術規范。
針對受訪者反映比較集中的組織管理問題,學校可以參考受訪者提出的建議,考慮改善方法。例如,積極創造條件,保證海歸教師能夠與國際學術前沿保持密切交流。另外,注重營造寬松自由的工作氛圍,給予海歸教師群體獨立性和自由度,釋放他們的研究熱情和潛力;遵循人才發展的自身規律性,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另外,管理層應與引進的人才多多溝通,使海外高層次人才能更快地融入新的環境。例如,海歸教師普遍反映因自身“關系網”不健全,在校內外學術圈發展舉步維艱。針對這一問題,一方面,學校可以正確引導,幫助海歸教師了解并融入國內學術團隊,逐步建立有效交流、資源共享的合作網絡。另一方面,在評職稱、評優時,學校應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管理考核機制及激勵機制,建立健全公平、透明、真正以成果或“生產力”為導向的評選機制,減少主觀人為因素的過多干預。只有真正以“生產力”為評價標準,才能充分鼓勵海歸教師努力通過真才實學取得應得的社會認可。另外,針對海歸教師群體的個性化問題,應考慮采用多樣化成果認定途徑,而不是簡單地以發表論文數量等來衡量工作業績。海歸教師在國外任職的經歷和時間應該被納入考核范疇,而且學校應該考慮給偏重教學的海歸教師取得學校認可的機會,鼓勵有教學專長的教師能夠潛心從事基礎教學科研工作,并為這種教師提供上升空間。
(三)個人層面
除了各高校和教學組織可以為海歸教師歸國適應提供支持和幫助外,海歸自身也必須有意識進行自我調整。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有意識主動進行適應調整有利于盡快融入國內工作生活環境;相反,消極抗拒、任憑負面情緒滋長,則很容易造成惡性循環,不利于達成心理適應及工作適應。為快速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海歸教師應主動調整自身心理狀態,主動適應國內環境、積極轉換自身角色。遇到問題時,一味地抵制、抱怨并不利于解決問題。不能改變現實的情況下需要調整自身的心態,以平和理性的態度來看待國內環境。對于不利的因素,要以積極正面的心態去面對,用恰當的方式表達訴求,積極尋求解決途徑。在此過程中,學會包容、理解、融入、積極應對,才是積極健康的歸國文化適應態度。
本文依據歸國適應理論框架對北京高校海歸教師的適應情況及影響因素進行了調查并提出相應研究啟示。研究雖存在自身局限,但希望能為政府部門、高校管理者、高校統戰部門及相關教師提供一定參考。
[注釋]
[1]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6年5月30日,http://www.gov. cn/xinwen/2016-05/30/content_5078119.htm。
[2] 易凌峰、趙青、歐陽碩:《海歸知識員工歸國適應影響因素分析》,《統計與決策》2010年第3期。
[3] 劉青、張超、呂若思、盧進勇:《“海歸”創業經營業績是否更優:來自中國民營企業的證據》,《世界經濟》2013年第12期。
[4] 李唐、程麗如、方舒:《高校海歸青年教師生存現狀分析—基于ZR大學等首都六所高校的調查》,《學海》2015年第6期;李娟:《高校海歸青年教師思想狀況調查研究—以北京市6所高校為例》,《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陳燕:《契約印象:海歸教師重塑高校課堂的跨文化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
[5] John Gullahorn and Jeanne Gullahorn, “An Extension of the U-curve Hypothesi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19 (April 1963), pp.33-47.
[6] J. Berry,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29 (December 2005), pp. 697-712.
[7] J. Black, M. Mendenhall and G. Oddou,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6, No.2(April 1991), pp. 291-317.
[8] C. Ward and W. C. Chang,“ ‘Cultural Fit’: A New Perspective on Personality and Sojourners Adjust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21, No.3 (July 2004), pp.525-533.
[9] E. Ma,R. Valle and I.Ma, “Analysis of the Repatriation Adjustment Process in the Spanish Contex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31(1) (2010), pp.21-41.
[10] 史興松:《駐外商務人士跨文化適應研究》,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頁。
[11] J. Black, H. Gregersen and M. Mendenhall,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patriation Adju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16, No. 4 (December 1992), pp.727-745.
[12] J.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 No. 3 (October 1988), pp.95-120.
[13] Y. Kim,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age, Thousand Oaks, CA., 2001.
[14] J. Berry,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a New Society”,International Migration Quarterly, Vol.30, No. 2 (April 1992), pp. 69-87;Z. Aycan, “Acculturation of Expatriate Managers: A Process Model of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New Approaches to Employee Management, Vol. 4, No. 3 (July 1997) , pp.1-40.
[15] C. Ward and A. Kennedy,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23, No. 4 (October. 1999), pp. 659-677.
[16] B. Parker and G. McEvoy, “Initial Examination of 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7, No. 4 (December 1993), pp.355-381.
[責任編輯:密素敏]
A Study on University Returnee Teachers’ Status of Repatriate Adaptation—Taking Teachers from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s Examples
SHI Xing-s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talent introductio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returnee teachers; repatriate adaptation
Based on repatriate adaptation theor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on 30 returnee faculties from 3 Beijing universiti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teachers’ status of repatriate adaptation from environmental,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It is found that almost every returnee teacher had encountered certain re-adaptation difficulties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their return. The situation improves along with their length of stay.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adaptation, many of them experienced strong sense of doubt, dissatisfaction, anxiety and other negative sentiments. These not only impede their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overall life quality, but also considerably mediate their job effectiveness.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roducing talents to univers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returnee teachers’ re-adaptation status, problems encountered, relevant appeals, and to seek solutions from governmental, university as well as individual dimensions.
G645.1
A
1002-5162(2017)02-0001-09
2017-01-16;
2017-03-24
史興松(1972—),女,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跨文化適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