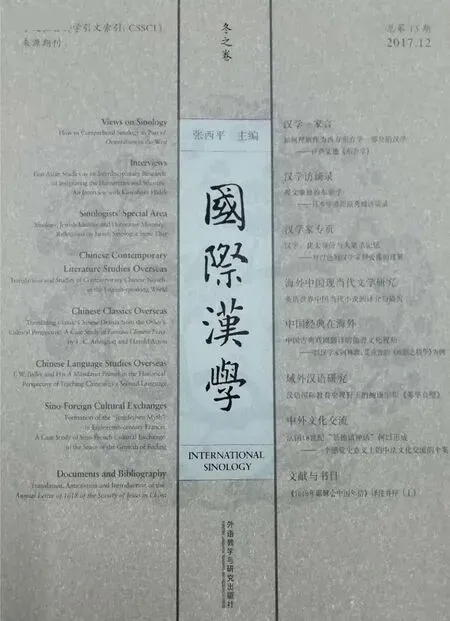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見林而不見樹”—評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
任何一部文學史著作皆或隱或顯地貫穿、體現著作者本人的文學史觀。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Die Chinesischf Literatur IM 20.Jahrhundert)亦不例外。在前言中,顧彬寫道,他在“行文中給出的評價都是個人的主觀見解,并不圖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經久不滅。”①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頁。以下引用該著文字,均于正文中注明頁碼。此種表述令人驚訝。周作人在90年前即1927年發表的《答蕓深先生》一文中,已經涉及文學史撰寫及文學史觀問題,周作人說,“文學史如果不是個人的愛讀書目提要,只選中意的詩文來評論一番”,那么,它就是“以敘述文學潮流之變遷為主”。②周作人:《談龍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沒有一部像樣的文學史會僅僅代表著者個人一己之看法。實際上,顧彬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書寫,更多借助了德國學者的翻譯、評論和研究。在第二章中,顧彬甚至以決然的口氣說道:“任何一部文學史的寫作的關鍵點在于,它絕對必須以其他學者的認識為依托。”(第60頁)文學史家個人的主觀見解與其他學者的認識之間,最終要達成某種一致性;而過于強烈的主觀見解,則往往造成一種認識上的盲區。
這部文學史有一個明顯的特點,腳注部分已經顯示了,它所引用的評論、觀點全部出自德國學者,幾乎看不到中國批評家、文學史家的論述。一只眼睛只能看到全體的一半。倘若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外國文學史家撰寫某國文學史,行文中僅僅引用中國學者和翻譯家的評述和研究,僅僅依賴二手資料,而不選擇、采錄該國批評家和學者的批評、論述,那么,如此的著作從成色、質地上看,只能是二三流的,其可信度不可能有多高。中國出色的外國文學史家們,他們奉獻出來的著作呈現了原汁原味的特點。舉一個例子:葉渭渠、唐月梅著《20世紀日本文學史》③葉渭渠、唐月梅:《20世紀日本文學史》(第4版),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年。,凡所引用之處,均出自日文資料,偶爾采用中譯本;著者的史識及史觀隱藏在豐富的史料后面,亦體現在對文學思潮的梳理和作家作品的評價等方面。讀罷全書,在大體知曉文學史演變的同時,多少了解了優秀作家作品。相比之下,顧彬的“主觀見解”以及只引本國學者成果的行文方式,妨礙了他的認識、判斷和取舍,不能區分出優秀作家與次要作家,也不能確定經典的和優秀的作品,而這恰是一個文學史家的職志所在,是一部文學史的最終目的。
在文學史的起始和性質、重要文學理論問題、文學現象、作家作品評價諸多方面,這部文學史都存在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整體框架基本上為一種邏輯的建構,而非史實的描述、辨析和判斷,尤非立足于史實基礎上對文學史規律的探尋。因而在貌似嚴密的邏輯鏈下面,實則是過于隨意的鏈接、撮合,那種表現在論述方面的過度闡釋,則貫穿了全書始終,隨處可見。
一
顧彬把20世紀中國文學史劃分為“民國時期文學”與“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這是一種保險、安全而又不用心思的劃分法,沒什么可說的。證明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這才顯示了顧彬的文學史構想,顯示了他的良苦用心。對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個影響頗為廣泛的觀點—中國現代作家的眼光只盯著自己民族和國家,從未超出中國范疇,未能“把中國的困蹇,喻為現代人的病態”①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461頁。,故而與世界文學觀念相左,顧彬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可以看出他是并不認可的(第7、9頁)。針對一種普遍缺乏的中國現代文學“置根于世界文學”的認識,顧彬提出了他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學是自我救贖工程”的論點,來證明情況并非如此。此亦可看作他對中國現代文學性質的定位。概括起來,大致有四點:
第一,“五四”運動的解放具有雙重意義,即個人解放和社會解放,前者從屬于后者;無論是個人自由還是社會自由均以“救國”為目的,“這是中國從1919年到1949年走過的道路,文學只是這一道路的反映”。作家甘愿為此放棄自身全部利益,原因在于“這和中國革命的反宗教的、世俗化了的特征有關”。(第30頁)
第二,類似于“福音”世俗化形式的“現代和改革”并未帶來政治和社會的“救贖”,結果是“旨在將中國從民族和社會的災難中拯救出來的中國現代派的許諾,一旦被當作了宗教替代品,其后果很可能就是讓知識分子翹首期待一個‘超人’、一個‘領袖’,也就是一個彌賽亞式的被世俗化的圣者形象,從而無條件地獻身到革命事業中去”。(第32頁)
第三,對超人的接受以及伴隨著“打倒孔家店”之類口號,“導致了對人的力量不斷升級的信仰”,過去的傳統失靈了,自我在尼采學說的滋養下增強和膨脹;過去是“神的顯靈”(傳統),現在則是“自我顯靈”了,“從‘神的顯靈’向‘自我的顯靈’過渡不是從宗教向世俗化態度的簡單轉移,而是新觀念利用了舊傳統的象征之物,由此使自己成為了一種新宗教。激情再一次為其所用,這種激情現在承擔了合法化的功用”。(第43—44頁)
第四,以郭沫若詩歌為例,過去依靠傳統、依靠宗教來拓展自身能力的東西,現在變成了“自身”,郭沫若詩中“歡呼自我”,將一切“歸功于自己”,說明其間發生了一種“崇高的轉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傳統,崇高的首先是個人,然后是集體,尤其是國家”。郭沫若那么起勁地先是歌頌個人,然后再歌頌無產階級,接著又歌頌起了領袖,即為一個顯在的例證。(第46頁)
這便是顧彬的中國現代文學“自我救贖工程”的主要內容,再濃縮一下其主旨:傳統失靈了,改革“救贖”失敗了,個人或“自我”由此膨脹為一種“新宗教”;既然成了“新宗教”,勢必會“造神”,會尋找一種替代品—集體、國家,最好是一個超人式的領袖。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推導出的結論與“置根于世界文學”這個大前提之間,南其轅而北其轍。
仿佛為了強化中國現代文學就是“置根”于世界文學、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顧彬干脆說道:“中國現代文學嚴格說來也可以理解為對西方范本的‘翻譯’。”此處的“翻譯”乃實指,非象征意義,顧彬說,“要研究一部現代中國文學的著作,先摸清它當時所據的底本情況絕不是無足輕重的”,他抱怨本來屬于“翻譯學”的任務卻落在文學研究者頭上,負擔太重了。(第72頁)
顧彬的文學史闡釋顯然是一種邏輯建構,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實基本無關。他不是從現代文學史實中抽繹某種共性,而是先設定了“救贖”觀念之后,再以現代文學事例作為證明。其實,這個觀念本來不證自明,何須證明。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所謂“救贖工程”內容何以那樣的奇奇怪怪、莫名其妙;也唯有明白了這一點,也才能夠看出顧彬的“循環論證”讓他自己陷入了一個悖論之中—“救贖”工程導致的自我、集體、國家、超人、領袖云云,不正是夏志清早就指摘過的眼光只盯著民族、國家因而難有超越的觀點嗎?
在導論結尾部分,顧彬解釋了中國現代文學為何至今不能“從闡釋的政治軌道上完全掙脫出來”,原因在于“檔案還未全部開放”,研究者無法擺脫偏見,“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決于闡釋者及其闡釋的形象。”(第9頁)也因此,顧彬忽視現代文學史研究中已經取得的共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常識,以闡釋代替常識,在兩種缺乏內在邏輯關系的對象之間,直接建立起一種邏輯鏈,就好像歷史上確鑿無疑地發生過這種事情一樣。最典型的案例表現在現當代文學過渡期的描述及闡釋上。
從史實的角度言之,蘇曼殊對新文學的影響甚微,根本不能與梁啟超、林紓等人相提并論,新文學運動的第一二代作家們甚至不提蘇曼殊的名字。1948年,朱光潛發表《現代中國文學》一文,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進行初步總結:
由古文學到新文學,中間經過一個很重要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一些影響很大的作品既然夠不上現在所謂“新”,卻也不像古人所謂“古”。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林紓的翻譯小說,嚴復的翻譯學術文,章士釗的政論文以及白話文未流行以前的一般學術文與政論文都屬于這一類。他們還是運用文言,卻已打破古文的許多拘束,往往盡情流露,酣暢淋漓,容易引人入勝。
新文學所受的影響主要是西方文學,所以不得不略談翻譯。林紓以古文譯二流小說,歪曲刪節,原文風味無存。但是,他是第一個人引起中國人對西方小說發生興趣的,功勞未可泯沒。①朱光潛:《朱光潛全集·欣慨室中國文學論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56—157、160頁。
史實重證據,后來的研究者哪怕用了再好的闡釋,也不能替代事實本身,顧彬卻在行文中不經意間把一種解釋當成了事實。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一節中,顧彬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實證性地論斷道,蘇曼殊有幾篇小說給文言文小說畫上句號,“并且過渡到了一種現代性的敘事策略”;他更為實證性地下斷語:
蘇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對于病態沒有采取回避態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對病態做了不加粉飾的描寫。他成功地做到了把新素材示范性地集中于單個人物,通過典范而使之具象化。像眾多同時代人一樣,他也為中國現代派的搖擺不定精神打下了根基,這種根基和在西方一樣,一方面具有精密、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卻帶有遲于行動、內心分裂、躁動、苦悶和自我失落的特點。(第22頁)
這段文字中第一句就錯了。要論起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師,還輪不到蘇曼殊。胡適于1922年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其中第七節專論章太炎,稱贊章是古文學五十年結束時期“結束的人物”,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也即古文學的最后一位大師。②胡適:《胡適文存二集》(二),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47、153頁。顧彬所說蘇曼殊與“眾多同時代人一樣”,為一種精神“打下了根基”,本應為確鑿的事實和證據,卻出自于一種隨意的表述。倘要找事實、找影響、找“眾多同時代人”、找怎樣打下一種精神基礎,總之,拿出證據來。還真的沒有,因為蘇曼殊本來影響就很小,無論怎樣夸大亦與事實無涉。
顧彬的邏輯建構還表現在當代文學(1949—1979年)與新時期文學關系的論述上。對這兩個時段的文學史,現在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種共識—這是兩種擁有不同話語系統、不同性質的文學,“階級性”和“人性”標示了二者間的區別。顧彬聲稱,他不會像其他人那樣避而不談甚或嘲諷1949—1979年的文學,他認為那幾十年的文學作品“構成了一種自有的美學體系”,要嚴肅地對待之,目的在于“可以借助這些作品認識毛主義的內在性質,以及去理解1979年以后的新文學,而人們經常把新文學同之前的文學對立起來”。如何理解呢?顧彬做了一個示范性的分析:比如,翟永明1984年發表的《女人》組詩中“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來”以及“太陽,我在懷疑”,表明“這不僅對郭沫若代表的太陽崇拜,也是對官方話語中的光明隱喻—類似《光明日報》標題—提出質疑”,這種解釋似乎把文學當成了社會學材料。顧彬說,他只能如此理解,因為“目前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第255頁)
中國新時期文學對前30年尤其“文革”文學的反撥、改寫、戲仿等,不在少數,莫言《紅高粱家族》對戰爭文學的改寫,即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顧彬不以莫言為例,而選取了他為之“寫了無數文章”的翟永明(第323頁注釋②),足見他個人的偏好,獨不見文學內部的演變規律。在本書中,顧彬多次以翟永明及其詩歌作為闡釋的根據,比如“北島的‘我不相信’和后來翟永明的‘我站起來’共同構成了80年代男性和女性反抗的支柱”(第304頁)。“我不相信”(《回答》)在當時即產生了較大反響和影響,已經成為了一個特定的和固定的文學形象,傳達著一個時代的心聲和訴求。相比之下,翟永明的“我站起來”其時鮮有人知,今天亦無人提及。一個影響廣泛的意象與一個無人知曉的意象,如何能夠同時構成一對精神上的“支柱”?對翟永明的詩歌,顧彬似乎有點欲罷不能,論述楊煉詩《人日》時,他再次寫道,楊煉的詩作“再造了由郭沫若創立、由翟永明終結的太陽崇拜”(第334頁)。倘若翟永明真的終結了“太陽崇拜”,那將不僅僅是當代文學史,而且也是當代中國史上大書特書的一筆,人人皆知了。
附帶一句,翟永明詩歌中有一個特點,意象上喜用全稱判斷,描述和抒情方面則多用極致的說法。試從《女人》組詩中摘出數句,以見一斑:“歲月正在屠殺人類的秩序”“整個宇宙充滿我的眼睛”“所有的歲月”“我創造黑夜使人類幸免于難”“使大地在你腳下卑微地轉動”“我就容納這個世界”“從此我舉起一個沉重的天空”“用人類的唯一手段”“苦難……被重新寫進天空”等等。這樣一種亢奮、激昂以及大而無當的文風、詩風,與前30年文學尤其與“文革”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真想要細繹兩種不同形態文學間的因果變化,翟永明的詩歌當是一個無可替代的案例。
在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上,顧彬更是不要事實證據,只著意于一種建構。比如“文革”時期的“三突出”原則,顧彬斷然寫道:
為了同1949年以來所謂的文藝黑路線作斗爭,江青推出五部樣板戲作為藝術創作模式,典型體現了“三突出”的新美學觀。……我們發現,這實際上移植了基督文明“最后的晚餐”之類的繪畫作品,毛主義繪畫在突出政治領袖方面無疑借鑒了前者。從文學角度而言,事情當然不會表現得那么明顯。但我們無疑可以從中看出某種相似性。(第287頁)
“三突出”原則為于會泳首創。據戴嘉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1968年,時值“樣板戲”問世一周年,《文匯報》文藝部負責人約請于會泳寫一篇文章,專述在江青領導下“樣板戲”如何在兩條路線斗爭中勝利誕生。于會泳注意到江青在“京劇革命”中顛來倒去只有一句話“塑造好革命英雄形象”,經過反復揣摩、迎合,于會泳第一次發明了新名詞“三突出”,后經姚文元修改,遂逐漸成為“文革”時期文藝工作者必須恪守的金科玉律。①戴嘉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第218—220頁。從醞釀到出臺,于會泳并沒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從“基督文明”、從“最后的晚餐”中受到啟發,從而發明“三突出”原則。顧彬依據何種稀見史料,那樣肯定地說他“發現”了這個名詞“實際上移植”了基督文明?
二
在評價、闡釋一個文本時,這部文學史著作確乎體現了顧彬本人的文學史觀,即個人“主觀見解”過于強烈,對某個文本的分析和結論,往往將其從作家的整體創作風格中抽離出來,忽略了文本本身的主旨和意圖。所謂主觀,不是不要理論,師心自用,顧彬會依仗另外一些他似乎感興趣的觀念、理論,如宇宙、天地、生命、宗教、性等等,切入一個文本。這些觀念和理論與一個文本自身得以產生的語境基本上沒有多大關系,所以,顧彬的闡釋讓人一讀之下會覺得新奇,再讀之后便覺新奇到了奇怪的地步。歸納起來,大致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放大一個文本中居次要地位的主題,或者給一個文本附加它本身沒有的,也不可能擁有的內涵和意義。閱讀這種分析,讓人覺得好像也有道理,但是覺得無論他怎么說,所說的就是與該文本無關。試舉二例。先看魯迅的例子:
反之,在短篇小說《一件小事》中我們可看到作者后來同情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某種預示。在這篇小說中作者的目光離開了粗俗淳樸的民間大眾,他通過人力車夫這個形象把無產階級變成了未來的承擔者;同時第一次投身于民國時代的社會事件中。魯迅是第一位在小說中關注無權無勢的下層民眾的作家。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阿Q正傳》中,他破天荒地給一位農民作“傳”,給這位受侮辱者豎起了一方紀念碑。(第39頁)
《一件小事》創作于1919年,受到了當時倡導的“勞工神圣”理論影響,也有魯迅自己的一點平日乘坐人力車經歷在內,或許還受到了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橘子》的啟發,后者寫了一個鄉下貧苦女孩的美好心靈。①何德功:《中日啟蒙文學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212頁。《一件小事》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之所以如此之大,大到與其形制、內容不相符合的程度,張中行就頗不以為然地說,是沾了入選中學語文教材的光,“名聲大會孕育獨占性”。②張中行:《張中行作品集》(第五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93頁。今天回頭再看這個小說,它確實只是一篇速寫,魯迅把自己的所見所感,也就是一種即時的情緒放大了,說它乃一時興到之語,亦未嘗不可。1919年的魯迅,正處于全力批判國民性且鋒芒畢露的階段,他的筆下突然出現了一個背影高大的人力車夫,高大到“須仰視才見”的程度,這與其時魯迅的整體創作風格嚴重不符。張中行視此篇為“濫竽充數”,雖用語刻薄,亦屬準確評價。顧彬脫離開必要的歷史語境,給這個文本戴上了兩頂高帽子:“同情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把無產階級變成了未來的承擔者”。對1919年的魯迅來說,馬克思主義思想、無產階級等等還是些很生僻的詞語,一直要到1928年與創造社、太陽社成員論戰時,才漸次出現在他的筆下。其實,顧彬給這個文本戴上大帽子,無非想要表明魯迅具有預見能力和先見之明。過去魯迅研究中存在著一種將魯迅拔高的風氣,用后來發生的歷史事件印證魯迅先前發表的文章,其邏輯方法為由果推導出因,最后在因、果之間劃上等號。顧彬或許也受此風氣浸染,走得則更遠了。嚴格地說,魯迅“通過人力車夫這個形象把無產階級變成了未來的承擔者;同時第一次投身于民國時代的社會事件中”,整個句子意指它不只是對文本的分析,也是關于魯迅本人的史實。可是,說魯迅在1919年就通過一篇速寫作品把“無產階級”變成了“未來的承擔者”,這個結論未免過于簡單化;同時,魯迅在1919年“第一次”投入民國的社會事件中,也是一個常識性錯誤。1912年2月中旬,魯迅即離開紹興前往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開始了他的一系列參與教育、社會的活動,何必要等到1919年寫《一件小事》的時候,才投身“社會事件”中?
再看阿Q。顧彬的第一句話便說錯了,阿Q并不是“一位農民”,無需多說;視阿Q為一個“受侮辱者”,也大成問題。喝醉了酒的阿Q,于得意之余,會飄飄然地唱幾句“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假洋鬼子”之所以拿黃漆手杖敲打他的癩疤腦袋,蓋因他罵人家“禿兒。驢……”在先;頭上同樣挨了趙秀才的一頓竹杠,也屬自找晦氣,蓋因情欲發動,想和趙家傭人吳媽“困覺”。阿Q性格中頗有好斗的因子,誰敢觸及他的“癩疤瘡”,便立刻全疤通紅地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力氣小的他便打”,和王胡打,和小D打,打不過時,“大抵改為怒目而視了”。欺負起更為弱小的小尼姑來,阿Q一點也不手軟,摸人家的頭,扭人家的臉,于看客們的喝彩聲中又狠狠地用力一擰,這才放手。如此一個近似于無賴的人物,怎么可能是“受侮辱者”呢?魯迅豎起的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諸多低劣不堪的東西,那真的不是一方“紀念碑”。
第二,在一些文本中總想著要發掘出性的意蘊來,在性的主題上又挖出更深的“寓意”。試以對張天翼短篇小說《脊背與奶子》的分析為例。
“族紳”長太爺是一淫棍,覬覦村婦任三嫂,尤對其豐滿堅挺的奶子充滿難以遏制的欲望,百計勾引、以債相逼而終不成,于是以其有相好為罪名,施行家法,判決“筋條”抽打一百下,后任三嫂設計逃出。這便是《脊背與奶子》的大致情節。故事并不復雜,描畫頗為生動,人物情態躍然紙上,多寫實,少夸張,與張天翼其他諷刺小說有些區別。顧彬挑出“奶子”意象,闡發了其中意義:
小說把奶子比喻作墳堆,也含有這一種寓意:正是女性生養和哺育了祖先,祖先能繼續活在后代的意識中,也是因為后人仿效那哺育了他們祖先的形式。我們知道,以充作榜樣的故事中,母乳的滋養也是對病入膏肓的家族長輩一種孝敬的方式。長太爺三次伸手去抓任三嫂的乳房,不只是對一個性目標的攫取,這里的抓也包含了一種延續自己和宗族生命的要求。兒媳婦的密謀讓這些希望都化為泡影。她逃脫了,只剩下墳堆和長太爺對她身體的回憶,農村的娜拉取得了勝利,男性家長制勢將滅亡。(第144頁)
“奶子”和“墳墓”兩個意象出自小說第八節也是最后一節:
東邊掛出了大半個月亮,像一瓣橘子。長太爺在孝子橋邊踱著。突出的顴骨在月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覺得一切的景物都可愛起來,那些干枯的瘦樹仿佛很苗條。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對他笑。墳堆像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過這可有點兒不大對,墳堆是硬的。①張天翼:《張天翼短篇小說選集》(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第341頁。
比照可知,顧彬誤讀了,讀反了,不是“小說把奶子比喻作墳堆”,長太爺在孝子橋邊等任三嫂,淫欲撓心,看著月光下一切都那么可愛,連“墳墓”也像任三嫂的奶子。整個文本的傾向性非常明確:一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所謂“族紳”,為了滿足個人欲望,先使用“家法”把誓不相從的任三嫂打個半死,接著又以任三嫂丈夫欠錢相要挾,讓她陪睡來抵賬。這是一個否定性的人物,是被作者著力鞭撻的反面形象,可顧彬卻從中釋讀出了正面意義:長太爺多次想抓任三嫂的乳房,表達了延續宗族生命的要求;奶子以及“母乳”也成了對長太爺之流的“孝敬方式”。這樣的解釋,源于解釋者不能體察,尤其不能感受文本的傾向、文氣、情調、氛圍所致。
再看顧彬對郁達夫短篇小說《過去》的闡釋。郁達夫的部分小說中帶有色情、變態的意味,這篇也是。敘事者—一個報紙編輯,喜歡上了一個活潑然而時時對其施虐的女子,以肥掌擊臉,拿尖頭鞋踢腰,一切玩弄、輕視都會讓他感到“不可名狀的滿足”;想到她那肥嫩白皙的腳,要是放在自己的碗里“咀吮一番”,一定很舒服,想及此又“要多吃一碗”飯。對這樣一個除了有些許色情意味而別無深意的細節,顧彬從中闡發出了“更深層的維度”:
鞋的象征對象是陰戶。去折磨和用來折磨主人公的物件,因此正是他所期盼的對象。此外,飯碗在傳統意義上代表著宇宙秩序:上象征著天,下象征著地。男人在傳統意義上是天,女人是地。如果這種秩序顛倒過來,碗中的雙足象征性地居于上方,女人控制著男人。男人變成了女人的奴仆,咀吮雙足對于生命之重要就如同對米飯的需求。(第59頁)
這些“寓意”或“維度”,屬過度闡釋,與文本無關。
類似的闡發所在多有,如茅盾《子夜》“是一部明爭暗斗的兩性之戰”(第113頁),如茹志鵑《百合花》中敘事者(護士)和新媳婦都愛上小通訊員,后者犧牲后掛包里的兩個饅頭也表示了“東西成雙,(心上)人跡杳然”(第271—272頁)等。顧彬高度評價歌劇《劉三姐》為“民族藝術的典范”,概括它的內容為“一名叫劉三姐的青年女子能夠和三名男子對歌。這種常用的舞臺技巧叫做‘一女三男’。這種歌劇至今仍然吸引著中國觀眾”。(第290頁)實際上那“三男”只是財主莫海仁請來的三個鄉村秀才。莫財主以收田、還錢相逼,欲強娶劉三姐,劉則以對歌為條件:對輸了,嫁給莫財主;對贏了,從此不許莫財主禁山封地、霸占西山茶林。莫財主重金請來陶、李、羅三個“之乎者也爛秀才”與劉三姐對歌,這幾位哪里是劉的對手,幾番比唱,最終“張口結舌”“狼狽下場”。劉三姐與三個“爛秀才”對歌是在第五場“對歌”,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細節,即便勉強概括為“一女三男”,也不可以作為全劇的結構或者技巧。①《劉三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1年,第33—51頁。不知顧彬何所據,竟歸納出了帶有情色意味的“一女三男”的技巧,而且還是舞臺上的“常用技巧”。
魯迅早已指出了,有些“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魯迅所舉的例子,乃日本人安岡秀夫《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安岡氏說中國人嗜筍,且想象其挺然翹然的姿勢,可證這是一個好色的民族。②《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8頁。顧彬的闡釋比起安岡氏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以西方宗教概念、術語,來比附一些文本或意象,有時甚至走得更遠,在沒有文獻證據的情況下,斷定某些文本或意象受到了西方宗教的影響。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對魯迅“荒原”意象的闡釋。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說獨有叫喊于生人中得不到反應,其感覺便“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慨嘆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顧彬肯定地說“荒原”一詞就是出自于《圣經》:“在魯迅的早期作品中出現的曠野意象,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派的一個母題,在其中我們可以辨認出不同的范本來。它與聲音的結合最明顯的當然是出自《圣經》。但是怎樣合乎道理地解釋這樣的猜想:即它與‘曠野中的呼喊者’是相關的?……作家以先知自命,他在回顧中卻充滿了批判精神。”(第32頁)這里顧彬也作了一點考證,追蹤了“參考書目”:辜鴻銘于20世紀20年代曾在德國出版過一本論文集,名為《吶喊》,表示書名的詞語可追溯至拉丁文《圣經》中。但是,顧彬并沒有進一步論證,辜鴻銘所用的書名與魯迅小說集名“吶喊”,特別是與“荒原”意象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魯迅于何時接觸到辜鴻銘的論文;誰能證明魯迅筆下的“荒原”即是通過辜書、再直達《圣經》的,等等。把中文譯本《圣經》里的“曠野”等同于魯迅筆下的“荒原”,也是很隨意的一種行文方式。
如果稍稍顧及上下文聯系,《〈吶喊〉自序》中的“荒原”一詞并非多么難以索解,它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懷抱啟蒙主義文學觀念的魯迅,獨自叫喊于“生人”即國民中間,卻得不到一絲回應,使他感到寂寞,一如置身于無邊際的“荒原”,“荒原”顯然指中國社會。尚鉞發表于1925年的《魯迅先生》一文中,以大半篇幅談論《〈吶喊〉自序》一文,明確地說道,魯迅文中的“荒原”就是中國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別說做夢了,“連‘寂寞’也快被摩擦消滅了”,而與此“寂寞”適成反比的“只有沉溺于虛榮、驕傲、勢利忙殺、欺騙忙殺的沒有靈魂的東西”。③尚鉞:《魯迅先生》,李何林編《魯迅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頁。
《〈吶喊〉自序》中還有一個更為著名的比喻“鐵屋子”,亦指中國社會,與“荒原”同義,此可證“荒原”意象并不是出自《圣經》中的“曠野”。李歐梵認為“鐵屋子”可以當作“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象征”,亦可看成魯迅“黯淡的內心”。④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9—40頁。“荒原”與“鐵屋子”實則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名稱雖異,所指為一,都是為了強化一種啟蒙主題和意圖。
在當代文學部分,除了前文已引所謂“三突出”理論出自基督文明外,顧彬還以同樣的方式論述了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
……浩然的小說《金光大道》……只要浩然作品的主人公在引用毛澤東的話,馬上就從普通字體換成粗體字印刷。這種做法也許是借自《圣經》,耶穌和保羅的重要話語也是通過改變字體以示突出。浩然小說標題中“道”和“光”等用語也具有某些《圣經》色彩,符合認知過程的敘述結構以及“尋找”的敘述技巧也是如此。當然“道”也可以從中國傳統的“道”的不同含義中得到解釋……(第294—295頁)
關于“文革”中引用語錄時用黑體字,學者趙鵬、王永魁做了考證:“文革”爆發前后,各大報刊突出引文、語錄的首選字體是楷體,轉折點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同日刊登《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凡引用語錄處全部采用黑體。此后,黑體字語錄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兩報一刊”上,黑體字為語錄所獨享,甚至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詞;有時為了避諱帶有貶義的“黑”字,便將這種字體稱為“粗體字”。趙、王文章還考證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中常有黑體字出現,但與“文革”時引用有區別,這只是一種排版手段,意在提醒讀者留意而已,但此處并非有什么重要理論,有時也可能是論敵的觀點。俄文版中有黑體的地方,中文版也照排為黑體。①趙鵬、王永魁:《“文化大革命”時期領袖語錄專用字體的演變》,《百年潮》2014年第6期,第63—64、67頁。由此可推斷,小說《金光大道》中語錄黑體字當效仿“兩報一刊”,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兩報一刊”是否學自馬列經典著作,則不得而知,趙、王二位學者亦未明確出處。那么,所謂“粗體字”或許借自《圣經》,就是一個缺乏根據的虛假判斷。
浩然小說中“道”和“光”字具有《圣經》色彩,或與中國傳統的“道”相關,亦有可糾正的地方。對于浩然這樣一個“左”到骨子里、終其一生以假為真的農民作家而言,自己小說中的關鍵詞“金光大道”,竟然被說成源自于《圣經》,或與中國傳統的“道”有關,而非出自“兩報一刊”、領袖語錄,何勞他人來相幫辯解,浩然本人也會起而抗議的。“文革”期間,宗教同種種傳統文化形式一樣,皆在徹底掃蕩之列;一個對彼時中國歷史情狀稍有了解的人,不會把一部塑造“高大全”人物的作品與《圣經》、與中國傳統勾連到一起。
第四,對有的作品的種類和體裁判斷失誤,從而導致論斷失據。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把老舍《貓城記》視為“科幻小說”—“他唯一的一部科幻小說在西方很受重視,而在中國則不然”(第117頁)。
《貓城記》完成于1932年,最初發表于《現代》雜志。1947年出版“改定本”,老舍寫了一篇“新序”,開首就說這是一部寓言小說:
在我的十來本長篇小說中,《貓城記》是最“軟”的一本。原因是:(1)諷刺的喻言需要最高的機智,與最潑辣的文筆;而我恰好無此才氣。(2)喻言中要以物明意,聲東擊西,所以人物往往不能充分發展—顧及人(或貓)的發展,便很容易丟失了故意中的暗示;顧及暗示,則人物的發展受到限制,而成為傀儡。②舒乙主編:《貓城記 新韓穆烈德》(老舍小說精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年,第2頁。
老舍說的“喻言”,即為后來通行的“寓言”。名從主人,老舍對自己小說性質的定位是準確的。小說寫了主人公“我”乘好友駕駛的飛機飛往火星旅行,失事后墜落在貓國,友人摔死,自己亦被貓國高官挾持而去,為其看守“迷林”。整部小說敘述了主人公在貓國的種種經歷。就批判國民性這一點而言,《貓城記》是老舍所有小說中批判程度至為強烈的一部。在小說中,主人公以“我的偉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國”為理想標準,反照了貓國一系列國民性特點,試舉幾例:“貓人有歷史,兩萬多年的文明”,貓人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是一切國中最古的國”;貓語“自由”一詞意為欺負別人、不合作、搗亂、背約毀誓;“敬畏外國人”是貓人天性中的一個特點;貓人心眼很多,必要時也會冒一些險;自私,以自我為中心;“不敢欺負外人,可是對他們自己是勇于爭斗的”;貓國的“法律不過是幾行刻在石頭上的字”;貓人沒有幫忙的習慣;“敷衍”是貓人活下去的唯一方式;“見便宜便撿著”是貓人的習慣,等等。《貓城記》是一部傷心之書,是一部寄寓著大沉痛的書。無怪乎梁實秋當年讀了小說之后,高度評價這是老舍“最進步的一部作品”,勝過他以前的小說,“藝術思想都到了成熟的地步”。③梁實秋:《梁實秋文集》(第七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第198頁。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等著《文學術語詞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1957)有一個定義:“科幻小說指的是那樣一些故事—與純粹的幻想小說不同—這些故事通過涉及已知或想象的科學原理,或是設計好的技術進步,或是社會結構發生巨變,試圖使其虛構的世界顯得合情合理”,而幻想小說則反映了“未來的烏托邦”。④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爾特·哈珀姆著,吳松江等編譯:《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56—357頁。
《貓城記》中既無“科學原理”因素,亦無“烏托邦”因素,所有的是對國民性的批判,以及對時事曲折隱晦的嘲諷。因此,顧彬說它是科幻小說,他錯了;國內也有人說它是一部科幻小說,還有說是政治小說的,他們都錯了。
對作品種類的判斷失誤還表現在關于《四世同堂》的論述上,不知顧彬根據何種版本,認定這是一部“章回小說”和“戰爭小說”(第183頁)。視其為“戰爭小說”,多少靠一點邊兒,小說大背景設置在抗日戰爭時期;把它當作章回小說,顯然不恰當。老舍在序言中交代了小說的組織:一百段,百萬字,共三部—《惶惑》《偷生》《饑荒》,系故事緊緊相聯的“三部曲”。顧彬那樣肯定地說它是“章回小說”,至少能拿出一種表面證據,比如小說形式上有多少回目,可《四世同堂》并非章回形式,是以節為順序的。
類似的失誤不止這一處。在提及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時,顧彬寫道,這個小說是對清人文康《兒女英雄傳》的“再創作”(第271頁注釋①吳奔星:《文學作品研究》(第一輯),北京:東方書店,1954年,第224—225頁。)。既然認定為“再創作”,后一部作品與作為模板的前一部作品之間,當有大體相同的故事、人物、情節以及主題等等,其間變異、演化自不待言。可《新兒女英雄傳》與文康的小說,除了借用“兒女英雄”這幾個字,加一“新”字以避同名之嫌,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關聯的地方。袁、孔小說名亦自有出處,第十六回“愛和仇”第一節,主人公牛大水、楊小梅結婚時,朋友送來喜聯,第一副“新人兒推倒舊制度/老戰友結成新夫婦”,嵌一“新”字;第二副“打日本才算好兒女/救祖國方是真英雄”,嵌“兒女”“英雄”二詞,合起來便是小說名。說借鑒、吸收古典小說方法,亦無不可,吳奔星當年撰文評介此小說,概括了幾個特點,其中之一即為繼承、發展了《水滸傳》《紅樓夢》等古典現實主義傳統,采用了章回體的民族形式,吸取、革新了“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寫作方法,強化了故事性,以吸引讀者。①吳奔星甚至沒有提及文康《兒女英雄傳》,這很能說明問題。
從這里也反映出,顧彬分析文本時往往不僅有穿鑿過甚的一面,亦有輕率、武斷的一面。還可舉出不少例子來,如:老殘“他生活在‘殘’中,卻以補殘也就是創造秩序為己任”(第14頁);《孽海花》寫一青樓女子、一朵花,“花”即“中華之喻”(第16頁);孔乙己生活不斷惡化,“使得他無力償還酒債而死”(第38頁);蕭紅《呼蘭河傳》中街道上的“泥坑”代表著“普遍的東西,它生來如此,本質上從沒有改變過”(第224頁);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傾城”,“自古以來就代表著一種讓國家、城市為之而破滅的美”(第228頁);老舍《正紅旗下》里的“鷂子”象征著“即將摧毀養鳥藝術、中國文化的力量”(第290頁),等等。
三
顧著文學史還存在著若干明顯的常識性、知識性錯誤,試略舉數例。
第二章論“五四運動”一節中,顧彬寫道:“破壞的對象是一切傳統的和中國的東西。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921年胡適提出的口號‘打倒孔家店’。”(第 23 頁)
此說法有誤。第一,這并非是一個“口號”;第二,準確地說,不是胡適要打倒,而是胡適稱贊吳虞“只手”打孔家店;第三,“打倒孔家店”表述不準確,正確表述應為“打孔家店”。這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可以說中國現代史上流傳甚廣、誤傳最多的話,出自胡適為《吳虞文錄》所作的一篇序文,結尾兩段: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②《胡適文存》(四)(影印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259頁。
這已經成了學術史上的一樁公案,略知其由來的會說吳虞打孔家店,僅憑耳食之言的便紛傳為胡適要打孔家店了,至今還在以訛傳訛。
吳虞在五四前后頗為活躍,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多篇文章,批判孔子及儒家學說,鋒芒畢露,比如“故余謂盜跖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比如“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比如孔子“誠可為專制時代官僚之萬世師表也”等等。①吳虞:《吳虞文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6、31、35頁。所以,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是,吳虞對胡適的稱贊并不十分領情,三年之后即1924年,在回答《晨報》記者提問時,吳虞自稱“未嘗自居于打孔家店者”,胡適他們對自己的稱許“皆謬矣”。有研究者認為,吳虞的態度其實不矛盾,他反對的是被歷代利用了的孔子,而非孔子本人。②鄧星盈等著:《吳虞思想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73、74頁。胡適后來在他的口述自傳中也說過近似的話,他對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嚴厲的,但對孔子本人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非常尊崇。③《胡適傳記作品合編》(第一卷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71頁。
在第二章第三節“文學的激進化”中,顧彬論述延安文學時寫道:“延安代表著由一種批判文學向肯定文學的轉折。毛澤東斷然宣布,雜文時代已過去了,就是說,在批判對手方面,政論散文在過去已經達到了其目的,現在應該為那些幫助歌頌自己人的文學形式所取代。”(第191頁)
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雜文時代已經過去了”的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部分第四節中,毛澤東專門談到了因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而產生的“各種糊涂觀念”,“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就是其中之一,針對以羅烽《還是雜文的時代》為代表所反映出的一種文學傾向,分析并設定了雜文寫作的邊界:魯迅生活在黑暗勢力統治下,使用冷嘲熱諷的雜文是正確的,但在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只要“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非敵人的立場上,可用雜文形式批評“人民的缺點”;立場對了,諷刺也是需要的,“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④《延安文藝作品精編 1 理論詩歌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6—27頁。
毛澤東特別強調分清敵我、站對立場,盡管他也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政治觀點正確而無藝術力量的標語口號式作品,要求藝術與政治、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但主要的還是重在政治方面,看作家的政治表現。也即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而非敵人的立場,諷刺手法的雜文才是需要的。這也意味著雜文會被有條件地允許存在下去。
實際上,即使到了1957年,毛澤東也沒有明確反對過雜文、宣布取消雜文;相反,他主張雜文無須只顧及一點,甚至可以寫得全面一些。據陳晉《毛澤東文藝生涯》(下卷 1949—1976),毛澤東在1957年數次談及雜文:于同年3月份的一次文藝界座談會上,巴金提到有人說雜文不能全面,魯迅的雜文就只講一點,毛澤東接過話頭,同樣舉魯迅為例,說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雜文就有力量;4月份,對《人民日報》社長鄧拓等又說過“雜文要有”,也可以寫得全面些,魯迅的雜文就很全面云云。⑤陳晉:《毛澤東文藝生涯》(下卷 1949—1976),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473、483頁。可證毛澤東并沒有說過“雜文時代過去了”的話。
在論述艾青詩歌時,顧彬附帶提到馮至,說了一句頗為嚴重的話—“曾于1957和1958年間將艾青送到刀俎上的馮至……”(第213頁)。倘若事情真是如此,史實亦無可辯駁地證明是馮至把艾青送到刀俎上,那么馮至在文學史上將會以另一種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現。
馮至確曾于1958年發表過《駁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中充斥著五六十年代特有的詞語、術語和文風,是一種蠻橫的道德譴責和政治批判,諸如“靈魂這樣骯臟”“生活這樣腐朽”“站在革命的敵人方面去了”“這些資產階級的濫調”等等。不止馮至一人,據周紅興《艾青傳》,從1957年9月開始至1958年4月,有20多位詩人、作家和學者,在《人民日報》《文匯報》《文藝報》《解放日報》《文學研究》等報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批判艾青,那種譴責和謾罵,與馮至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定要追問究竟是誰把艾青送上刀俎,人人有份,只記到馮至一人名下,這是不公平的。倘再追溯起來,這20多個批判艾青的人未必個個心甘情愿,那樣整齊地聯手攻擊艾青,他們不過是奉命寫作、以求自保而已。
艾青之所以被打成右派,除了時代氣候外,具體原因是詩人講了“真話”。周紅興《艾青傳》寫道:
反右派斗爭不斷擴大化。艾青對這場斗爭很不理解,并說了一些同情被斗爭的人的話,像“我們黨內總是一些人整人,一些人挨整”、“斗爭丁玲是殘忍的,斗爭江豐是一棍子打死”等等,便被打進“丁陳反黨集團”,對他的批判不斷升級并迅速公諸報端。①周紅興:《艾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436頁。
1958年1月《文藝報》重新刊登了延安時期的一批雜文,其中就有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由最高領袖親自撰寫的“按語”,把艾青、丁玲、王實味等人打入了“反革命”“敵人”之列,最終宣判了這些人的命運。
就在艾青“陷入深潭之時”,王震伸出了援助之手,請艾青夫婦到北大荒,1958年4月艾青離開北京,乘火車前往黑龍江密山縣,這原是他們的終點。次年又被安排前往新疆。對艾青來說,這當然是一種很及時的保護。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殘、致死的人,艾青畢竟還算幸運。附帶一句,舒蕪將胡風送上刀俎,這才是當代文學史上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再也找不出比這更為恰當的第二個例子了。
還須一提,顧彬對典故“知音”,理解上有偏差:
并且從中國中古時代以來,對于真正友誼的設想就是同他人的聲音和傾聽有些關系的。一個朋友,一位知音,即知己,就是知道我的聲音,也就是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聲音,意味著知道我在講述時以詩情或音調所要表達的東西。(第215頁)
春秋時俞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琴,能從中聽出彈者的心聲。此處“音”專指琴聲、音樂,并不是人發出的“聲音”。《文心雕龍·知音》:“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王運熙先生譯文:“知音真是困難啊。音樂確實難以深入理解,能夠深入理解的人難以遇到,遇到能深入理解的知音,千年只有一次吧。”②王運熙等:《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8頁。后稱朋友、知己為“知音”。賈島《題詩后》:“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杜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皆指朋友、知己。顧彬將“知音”理解為“他人的聲音”“我的聲音”,顯然有點望文生義。
也有翻譯方面的粗疏大意,最突出的是,隨意混用“現代派”和“現代主義”兩個術語,試舉數例:“旨在將中國從民族和社會的災難中拯救出來的中國現代派的許諾”(第32頁);“這些知識分子把自己看作是‘曠野的呼喊者’,努力表明自己是出自于(西方)現代派之列的‘拯救者’”(第42—43頁);“魯迅這位現代派老前輩無論在事件風浪中還是在……”(第102頁);“如果不對西方現代派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對茅盾有公允的評價的”(第106頁);“因此,1949年之后現代派的落潮以及1979年后的現代派回歸也伴隨著女性身體的遮掩和裸露”(第112頁);“廢名……似乎又該被稱為一個現代派的代表”(第146頁);“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中心文本是《雨巷》”(第154頁);“中國現代主義1925年誕生于上海震旦大學”(第156頁);“現代主義這一派實際上是象征派和后期新月派的融合”(第159頁),等等。現代主義和現代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存在著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袁可嘉先生在《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一書中解釋道:“‘現代主義’文學指一種文學思潮,與‘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相對而言;‘現代派’文學是表現這一思潮的六個流派—象征主義、未來主義、意象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的總稱。”③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頁。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直接以“現代派”命名的只有戴望舒一派,這一派有時被稱為象征派,之所以被稱為“現代派”,主要還是因為施蟄存等主編《現代》雜志,用刊物之名來命名。其他帶有現代派色彩的流派,都各有其名,如40年代形成的“《中國新詩》派”或“九葉詩派”,新時期的“朦朧詩派”等,并無一個明確被稱為“現代派”的文學流派。兩個術語混用,以至于把魯迅都劃入一個不存在的“現代派”,實為不該出現的失誤。
此外,翻譯中還有不少硬傷,有必要指出其中幾條,如:
“周作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雜文《論人的文學》”(第26頁),《論人的文學》應為《人的文學》,這是被胡適稱譽為“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一篇最平實偉大的宣言”。①劉運峰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 191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這是一篇文藝批評,周作人本人視為文藝“論文”,并不是譯者所謂的“雜文”;
“胡適自己1920年作的抒情詩集《嘗試》乏善可陳……”(第29頁),《嘗試》應為《嘗試集》,此為新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
“李準……的小說《不能走這條路》”(第267頁),恰恰譯反了,應為《不能走那條路》;
“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簡稱‘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亦稱‘二月紀要’……”(第293頁注釋③),譯名隨意增刪,“召集”應為“召開的”,“座談”應為“座談會”,準確名稱應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一般簡稱《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更多簡稱為《紀要》,很少有稱為“二月紀要”的。
漢學家們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其理論是新異的,視角是獨特的,但他們缺乏心領神會。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言:“西洋人評論不很中肯,那可以理解。他們不是個中人,只從外面看個大概,見林而不見樹,領略大同而忽視小異。”②錢鐘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頁。自然,顧彬也不例外。
高奕睿和敦煌漢文寫本研究
高奕睿(Imre Galambos),1967年出生于匈牙利,1994年本科畢業于匈牙利羅蘭大學后,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博士學位,2002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戰國時期的漢字正字法研究》(“The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riting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2002—2012年,在英國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部工作。2012年至今,任教于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精通英、法、德、中、日等多門語言。作為新興漢學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漢文和西夏文寫本的正字研究和古文書學研究。目前已出版有《漢文傳統的翻譯與西夏文化的教授》(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2015)、《漢文寫本研究:從戰國時代至20世紀》(Studi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2013)、《寫本與行者:一個10世紀佛教朝圣者的漢藏文書》(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 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2012)、《早期漢字正字法:新出寫本的證據》(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2006)等著作和四十余篇論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