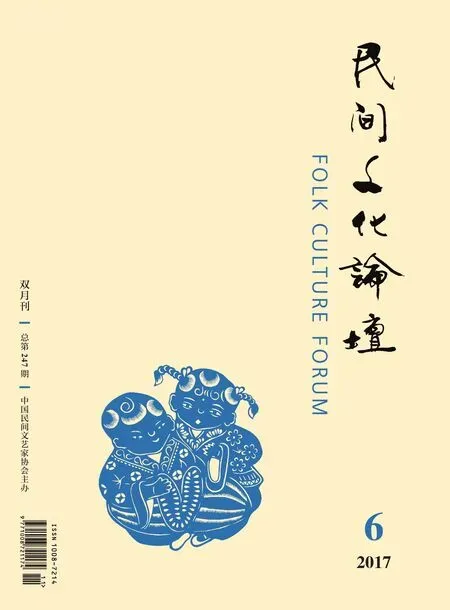從關公傳說看事實向文化的演化
鄒明華
從關公傳說看事實向文化的演化
鄒明華
以歷史上的關羽成為文化上的關公的例子,展示傳說研究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文化的生成過程與機制,其中箭垛式人物的傳說學概念可以成為理解文化生成機制的工具。關于關羽的史志記載只有千字左右,關羽的經歷原本只是個別性的事實,但是傳說塑造了關公的形象,融匯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并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而接受關公文化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因為這種文化共享而成為相互認同的社會。
關公傳說;關公文化;箭垛式人物
傳說是一種言說特定存在(人、物或事件)①傳說的主角和主題通常是人物,但是有的也可以是事物(動植物、自然景觀、事件等),為了論述的簡便,本文主要談人物。的敘事方式。任何人物,一旦進入傳說,成為傳說的講述對象,就會發生某種神奇的轉化,那種偶然的、個別的東西一下子具有了廣泛的意義。作為經驗上的存在,人是個別的,人的活動是偶然的,似乎并不與現場之外的人發生聯系。如果沒有進入傳說,他在特定的地方出現,事件在特定的地方發生,后來就會在原地消逝;但是進入傳說之后,偶然的活動因為敘述的機制構成了具有廣泛關聯潛力的故事,使人們有興趣傳講它,主動與它建立語言的和意義的聯系,并因為傳講,人與人被廣泛地連接起來,成為借助講述活動與故事文本的認同群體。有時候,這種認同群體能夠廣泛到覆蓋一個文明的范圍,其中一些傳說甚至世世代代傳講下來,具有貫通長久歷史的強大作用。
在中國社會,關公的傳說就具有這樣的地位和分量。三國時期蜀將關羽在身后成為傳說的主角,在后世被追封至“關圣大帝”,成為各地、各行各業崇祀的神,成為中華道德“忠義仁信勇”的化身,形成了名副其實的“關公文化”,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以至海外華人社會都形成了廣泛的文化認同。
傳說是民間文學的一種體裁,對于傳說的研究當然首先是民間文學的研究。但是,傳說及其講述活動又是一種民俗現象、社會現象。實際上,對于傳說的多學科的探究一直以來并不缺乏,例如哲學取向的研究(真實性、專名②鄒明華:《專名與傳說的真實性問題》,《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歷史學取向的研究(如趙世瑜③如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信仰的坐標:中國民間諸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文本、文類、語境與歷史重構》,《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后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民俗學和人類學取向的研究(如聞一多對伏羲與女媧、端午節起源的研究④聞一多:《聞一多全集》,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民國37年)。)等,都有突出的成果。影響深遠的顧頡剛的古史傳說研究、孟姜女傳說研究①顧頡剛先生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這一“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意義重大、影響深遠。1924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可參見《顧頡剛全集》之“民俗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也都是超越了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其實,傳說把個別性的人事轉化成為具有特定意向的敘事,其所發揮的把人們廣泛連接起來的功能,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意涵,不是僅僅民間文學研究所能夠充分認識的。因此,對于傳說的研究就一直是以文本分析為主的民間文學研究與把它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的其它學科研究并存的。但是,這兩種研究取向如何兼容、銜接,具有內在的相通性,卻是我們需要努力嘗試、探索的方向。
傳說在人類生活中被廣泛利用,是因為它具備對于社會聯系的生成潛力。我們試著分析傳說的這種潛力,看到這種潛力在實際的歷史現實中發揮出來,成為文化的生成能力。關公傳說對于關公文化的生成所發揮的作用,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如果我們結合傳說學的箭垛式人物的概念看關公傳說與關公文化的聯系與轉化,也能夠在民間文學的研究與民俗學、文化學的研究之間展現兩種研究所具有的一種內在聯系。
一、歷史人物關羽的史實
關于關羽的史志記載總共不過千字。在陳壽《三國志?蜀書》等文獻中記載的關公的生平大致是:關羽字云長,河東解州(今山西運城)人。東漢末與張飛從劉備起兵。建安五年,關羽兵敗于曹操,于白馬坡斬袁紹大將顏良,被曹封為“漢壽亭侯”,后回歸劉備。鎮守荊州時,曾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鎮華夏。公元220年荊州失守,關公被孫權部下呂蒙殺害,“頭定洛陽,身困當陽”,孫權將關羽首級獻給曹操,曹操刻沉香木為軀,厚葬于洛陽,孫權以侯禮將其身軀葬于當陽。死后追謚壯繆侯。
綜合各方面資料,可以把關羽一生的經歷概括為:
第一,出生于貧寒家庭,但從小在其父的教導下,熟讀《春秋》,并且練就了一身的好武藝;25歲時殺死橫行鄉里的惡霸呂熊。
第二,對朋友講究義氣、信義,尤其是與異姓兄弟劉備和張飛那種“寢則同床,恩如兄弟”的關系,為世人所稱道。關羽對劉備忠心耿耿,“千里走單騎”回歸劉備,一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連敵方的曹操也不得不“義之”;同時關羽又是一個知恩必報的義士,殺死顏良,為曹操解了白馬之圍;相傳赤壁之戰中,關羽竟違背軍令,在華容道上放了曹操。
第三,他的勇猛在當時聞名遐邇,“威震華夏”,有斬顏良、殺龐德、擊敗曹將夏侯墩、溫酒斬華雄、刮骨療毒等事跡;他都督荊州期間,曾嚇得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第四,關羽生前的官位并不高,具體大概曾任以下職務:初平二年(191),任別部司馬;建安四年(199),派關羽守下邳,行下邳太守事;建安五年(200),曹操拜他為偏將軍,封漢壽亭侯;建安十四年(209),任襄陽太守、蕩寇將軍;建安二十年(214),任命都督荊州事務;建安二十四年(219),拜為前將軍。這些職務或是地方長官,或是軍隊的先鋒,并不顯赫。
第五,由于關羽生前的業跡以及他與劉備的特殊關系,死后才被追謚為壯繆侯。①鄭土有:《關公信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
從史志來看,關羽的生平在內容上固然也算豐富,但是所涉及的地方與人事就大千世界來說畢竟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事并不會必然與后世之人有直接的聯系。他在后世成為人人知曉的人、各地遍立祠廟祭拜的神、十多個行業供奉的祖師、中國傳統做人價值的化身,卻有賴于圍繞他、以他的名義形成的文化。關羽事實轉化為關公文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一個讓各個地方、各種人與他建立意義聯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讓事跡成為完整的敘事、讓故事具有真實性、讓敘事承載人們的關懷并具有人們需要的意義的傳說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二、文化人物關公的生成
關羽在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中固然可以看到忠臣、猛將、義士的行事,但是他的整個形象不能夠說是清晰的,因為真實的人不可能是按照道德教條、神格生活的,但歷代的傳說(以故事體、戲曲體、小說體出現)、尤其是宋以后的各種官方與民間的努力,把各種事跡黏附到他身上,并賦予他的形象以清晰的道德意義和神圣意義。像集大成的《三國演義》,就借鑒了許多民間傳說的內容。典型的如單刀赴會,《老圃叢談》中說:“古來名將如關羽者甚多,而關羽獨為婦孺所稱,則小說標榜之力 ……小說中顛倒事實,尤莫如關羽之單刀赴會。《吳志》言:‘魯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然則冒險赴會,乃魯肅就關羽,非關羽就魯肅也。諸如此類,殆不勝辯。要之關羽雖萬人敵,有國士之風,然世多溢美,皆小說之力。”②轉自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頁。也就是我們今天知曉的關羽,已與歷史上的關羽有較大的差異。但是,關羽已經在人民心中成為關公,他的“忠義”品格,使各種能夠體現忠義等傳統價值的事跡附著在他身上,這就是傳說學的“箭垛式” 人物的形成邏輯,是“文化”人物的形成規律。
在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歷史人物死后被奉為神的并非少見;一位人神受到特定時期、特定區域人們祭拜的也難以勝數;但是,一位人神能夠在全國大范圍內盛行千年以上的卻是鳳毛麟角,只有極少數幾位。關公就屬這鳳毛麟角中的一位,正如明代馮夢禎《漢壽亭侯贊》云:“生為名將,歿為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③宋萬忠、武建華標點注釋:《解梁關帝志》,卷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4頁。關羽之所以成為“忠義”的化身,成為“武圣”,是由官方與民間相配合、借助通俗文藝的傳播力量持續建構而成的。
我們首先能夠清楚地看到官方的作用。清代著名學者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十五中概述:“凡人之歿而為神,大概初歿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歷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又封夫人為九懿德武肅英皇后,子平為竭忠王,興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為張世杰。其道壇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蕪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有崇為武廟,與孔廟并祀。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圣大帝。”①(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十五,欒保群、呂宗力校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2—623頁。雖然唐之前民間對關羽的信仰活動已經出現,但趙翼所列關公信仰從宋代進入官方祀典以后的步步高升過程是比較完整的。
北宋宋徽宗趙佶于崇寧元年(1102)追封關羽為“忠惠公”,第二年又進封關羽為“崇寧真君”,大觀三年(1108)再封關羽為“胎烈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又封關羽為“義勇武安王”,在短短的21年時間內,徽宗皇帝追封關羽達四次,由侯進公,由公進君,由君進王。南宋時,高宗趙構于建炎二年(1128)封關羽為“壯穆義勇王”,宋孝宗又于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關羽為“英濟王”。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統治者也懂得利用關羽,以忠義勇武約束臣民,教化民眾。元文宗圖帖睦爾便于天歷元年(1328)在南宋追封的英濟王的前面又加上了“顯靈義勇武安”,全稱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為什么關羽在宋代突然被官方所重視?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關羽身上所表現的忠勇、義氣正好契合了統治集團的需要。
明代統治集團來自民間,深諳民間神靈信仰對民眾的教化作用,對關羽的賜封越來越高:正德四年(1509), 朝廷下令將全國的關羽廟一律改為“忠武廟”;萬歷二十二年(1594),明神宗朱翊把關羽進爵為帝,關廟的名字也由“忠武廟”改為“英烈”;萬歷四十二年(1614)十月十日,朱翊又加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神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
像元朝一樣,清朝也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清朝統治者更加注重利用關羽身上的“忠義”精神。清朝入主中原后,采用了撫恤和禮待明朝將士、重用漢族官吏和知識分子等政治措施,以消除華夷之防和對立、反抗的情緒。在思想文化領域,采取了提倡和宣傳忠君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基本政策,大力尊孔,崇尚程朱理學,提倡尊君、忠君思想。正是適應這種政治的需要,清朝才把關羽大加神化。因為一方面關羽是漢族,易為漢族官僚和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經歷代統治的封賜及《三國演義》的影響,關羽已成為“忠義”的化身。利用關羽宣傳忠義、忠君思想,影響民眾,易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到光緒五年(1879),關羽的封號長達二十四個字,被封為“忠義神武靈佑神勇威顯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
由此可見,自宋代以來歷代統治者對關羽的推崇、封賜,主要是緣于其身上體現的“忠義”等傳統精神價值,有利于統治秩序。由于統治者的大力推崇,使得關羽的影響越來越大,廟宇遍及大江南北。
其次,民間的力量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關羽的事跡在民間流傳廣泛,而且不斷得到“神化”。尤其是在與關羽的生活有過交集的地方,如他的家鄉山西南部、他駐守過的湖北荊州等地。據史料記載:從公元210年到220年,關羽鎮守荊州10年,這是他一生當中最輝煌的時期,關羽一生令人仰慕的品格與業績主要在鎮守荊州期間展現;荊州又是關羽落敗喪身事業終結之所,失荊州走麥城被斬于臨沮(時為荊州南郡所屬)的悲劇結局深深喚起后人的同情與惋惜。荊州民間流傳著許多膾炙人口的三國故事與傳說。荊州市境內的古城以及洪湖、監利、石首、公安等縣市,都是著名的三國勝地。從洪湖烏林大戰古戰場的烏林寨、曹操灣、圓椅灣、搖頭山、紅血巷、萬人坑、白骨塌、赤林口,到曹操敗走華容道的馬鞍橋、救曹田、曹鞭港、放曹坡;從石首劉郎浦迎娶孫夫人的繡林山、錦幘亭、照影橋、牌樓堰、朝天口、望夫山與望夫臺,到公安劉備大本營、左公走馬堤、孫夫人城、呂蒙城、陸遜湖等等,總計有110多處,形成一個龐大的三國文化遺址群落。關公在荊州留下的足跡可以說是遍及各個角落,點將臺、卸甲、馬跑泉、關渡口、余烈山等遺跡都因關公而聞名,而且伴隨著大量的民間傳說。
在民間流傳的關羽傳說中,往往突出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他神奇的出生和死后顯靈。西南、西北地區認為關公是火神(火德星君、火龍)下凡;東部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則認為關公是神龍轉世。關公顯靈是他死后成神具神性靈性的象征,是各地關帝廟林立的由來,也是關公信仰的一種普遍的外在表現形式。傳說關公顯靈始于隋代,第一個關帝廟也建于隋代。在《佛祖統紀》第六卷的“智者禪師”條目中,記載了一位名叫智顗的僧人見到關公顯圣的故事。①(宋)釋志磐撰:《佛祖統紀校注》,釋道法注解,第六卷《東土九祖紀三之一?智者禪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智顗( 538—597年)是陳、隋時天臺宗的創始人,生于荊州華容,于隋開皇十二年(592)在當陽(今屬湖北省)玉泉山建玉泉寺,曾見二人威嚴如王,長者美髯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自通姓名,乃關羽父子,請于近山建寺,智顗從之。通過這些傳說以突出關羽的“神性”。二是突出他的“義薄云天”。“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在中國流傳極為廣泛,在這則故事中所宣傳的正是一種朋友間的義氣。劉、關、張三人在桃園結為異姓兄弟,三人共誓:“……同心協力,救國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②(明)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5頁。在這則傳說中,一方面強化了關羽的“義氣”,另一方面對民間社會有重要的影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成為義結金蘭時的必用語。
第三,通俗文藝的傳播效力也值得重視。關公的形象之所以能夠成立,當然是因為傳說奠定了各種神奇、巧合、卓絕的事跡的可信基礎,但是關公的形象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關公信仰之所以能香火旺盛, 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更有傳播效果的通俗文藝諸體裁,包括戲曲、 說唱文學、通俗小說、造型藝術等,在民眾的生活中無所不在,無孔不入,觸動社會的每個個體,包括那些不識字的普通民眾。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對關公信仰的盛行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清代王侃在《江州筆談》卷下中說:“《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孺,今天下無不知有關忠義者,演義之功也。忠義廟貌滿天下,而有使其不安者,亦誤于演義耳。”③魯迅:《小說舊聞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第38頁。
在中國戲曲界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奇特稱謂——關戲, 有人說它是一個獨特的劇種,但又不屬嚴格意義上的劇種,因為劇種一般是按演唱的風格、流派、語言、產生和流傳的地方等來區分的,如京劇、滬劇、婺劇、秦劇等。而關戲則是指專門圍繞關羽的事跡而展開的戲,是就劇目的內容而言的。關戲在許多劇種都有一定數量的劇目。因專演一個人的事跡而稱為一種戲,這種情況在中國戲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如著名戲曲理論家蔣星煜先生在《關羽在古典戲曲中的藝術形象》一文中所說:“安徽曾經存在過專演關羽的古典戲曲劇種,名之曰夫子戲。一部分古典戲曲劇種中, 關羽的扮演成為單獨一門腳色分行,名之曰紅生。從元人雜劇開始, 演員往往不自報關羽的姓名而自稱關某,諸如此類等等,都足以說明關羽成了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 與此同時,關羽戲的表演藝術也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成為中國戲曲藝術遺產中的寶藏之一。”④蔣星煜:《關羽在古典戲曲中的藝術形象》,《戲劇研究》,1984年第1期。關公戲曲一方面隨著關公信仰的流行而產生,因信仰的因素而形成了許多獨特的關公戲俗,關公戲曲的演出早期大多在關公廟會上;另一方面關公戲曲以通俗易懂、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對宣傳和塑造關公形象,對關公信仰的盛行,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由于社會各階層對關羽的推崇,關羽已經不是自然人,而成為了文化的關公,關公(關帝、關老爺)已成為一個“專名”。一說到關公,就是“忠義”等最高人格的代名詞。這種“專名”事實上在很早就已通過傳說以及發揮傳說的機制的其它文藝形式所造就,典型的案例如《水滸傳》中為了爭取關羽的后裔大刀關勝上山入伙,宋江表示情愿讓位給關勝。其原因就在于關勝是關羽的后裔,關羽是“忠義”的化身,關勝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三、從關羽傳說理解文化的生成過程與機制
文明社會的文化傳承總是通過不斷地尋找載體、賦予載體以自己偏好的意義而生生不息的,與此同時,載體的不斷累積也不斷地豐富了文化的內涵,擴大了文化的影響。關羽被社會所選中,他的個人經歷被重新組織成為傳說的敘事,與信仰結合,讓越來越多的人感興趣,從內心里相信,結果就成為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被廣泛共享的文化。個別人物、偶然事件進入傳說的機制就是社會記憶的一種機制。在傳說的這種機制里看,所謂文化,就是使一些事實被篩選出來不被遺忘,從而使社會的價值得到體現,口傳心授,代代相傳。
情境中作為個別現象的關羽及其事實所出現的場景是非常有限的,與之發生聯系的人也自然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們審視關羽演繹成為關公,蔚為無所不在的關公文化,能夠看到傳說及其傳講活動在這個神奇轉變中的作用。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傳說造就具有社會廣泛性的文化生成機制,我們能夠發現傳說學的箭垛式人物概念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這是關羽成為傳說的主角而使故事豐富起來的過程,實質上也是關羽的生平演繹為豐富的關公文化的過程。關公使中國社會建立了跨越地域、貫通歷史、融匯三教、感召萬眾的一體聯系,其傳說化的過程就是承載更廣泛內容的文化化的過程。這個文化生成的過程,通過傳說學的箭垛式人物概念能夠得到準確的理解。在這里,傳說學的研究能夠作為方法幫助我們開展涉獵更廣的文化研究。
關公從歷史人物關羽演化而來,突破了生命的時限、地域的范圍,成為中國人在價值、情感、信仰、人格上廣泛關聯的文化形象,對于心中有關公的中國人來說,人雖不在,卻“尚在存”,這就是文化的功能。方孝孺《寧海縣廟碑》中指出:“古之享天下萬民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于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云長,用兵荊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余載,窮荒暇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為偉人。當其生時,揮霍宇宙,頓摧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為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并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郁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眾人俱泯,則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在存,咸愿紀德,刻之柱石,俾永世無惑。”①轉引自《關帝志》卷三“藝文上”,據宋萬忠、武建華標點注釋:《解梁關帝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6—187頁。方孝孺解釋關侯能夠成為本不相干的寧海人的紀念對象,在內核上是因為其忠義精神,在形式上是因為他被神化。其實,他講的“神”化,就是那個時代人們容易接受的“文化”化。方孝孺所記的寧海案例,在過去一千多年發生在全國各地,在近代還擴及海外。翻查中國各地的方志、碑銘,關廟廣見于各地,在很多地方實際上是“村村有關廟”。舊時北京地區的關廟以及以關公為主神的寺廟就不止一百多處。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也曾經注意到華北關公信仰的廣泛分布,視之為中國社會的代表性文化現象。①[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關廟不僅見于各地漢族地區,也多見于內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還見于越南、朝鮮、日本、東南亞。傳說是把不同的地方聯結起來、把不同地方的人聯結起來的節點,傳說的形成與傳承過程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被聯結起來的過程。這也就是文化共同體生長的一種基本機制。
除了地域與民族的廣泛關聯性,關公文化還是貫通代表中華文化的儒釋道的一個紐帶。對于關公,儒稱圣,釋稱佛,道稱天尊。關公夜讀《春秋》,是經典的畫像內容;他在佛教和道教中都有極高的位置。以此而論,關公文化實際上是經典文化的融合貫通的生動載體。關公是由具有確認真實性的傳說敘事所塑造的道德楷模,是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的化身,常被以“義”“忠義”或“忠義仁信勇”的概括為民眾所傳頌,道德文化可以看作關公文化的核心。關公以“忠義”等形象內涵聞名于世,示范于眾,成為忠義的化身。
關公文化也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合成的產物。因為有長期的民間傳說與信仰的群眾基礎,官方從宋代開始不斷對他加封,尊及“帝”“圣”;因為有官方的認可,民間更是廣立祠宇,關公是十多行業的祖師爺,是民間為了護佑兒童成長被寄養最多的男神,被視為身家祿命的保護神、財神而得到熱情奉祀。關公文化隨著人口的海外流動,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為華人的團結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文化紐帶作用。
沒有一個人能夠代表一種文化,但是傳說這種體裁能夠被運用創造一組敘事來包含一個民族的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從而使特定的傳說人物代表一種文化。從真實的人物到傳說人物的過程也就是成為箭垛式人物的集大成過程。這個接納萬“箭”(博采眾長)的匯總與合成機制包括多個層次的傳說學內容:(1)在真實生活層次,把不同人的經歷歸入一個傳說人物;(2)在傳說的傳講層次,通過傳說的不斷再加工突出那些能夠承載民族文化內涵的母題、情節,一方面不斷把關于其他人物的傳說移花接木過來,一方面不斷對本人物的傳說或其故事進行篩選、整合,使傳說人物在形象上更具有一致性,更像“一個”人物;(3)在地域和族群的層次,該人物傳說具有更多樣的異文,以適應地域或族群的偏好,看似使這個箭垛上能夠接納更多或更多品種的“箭”。從上述關公傳說的生成與跨歷史、多地域、多民族的流傳和流變來看,關公故事的箭垛式生成與中華文化的綜合表達力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面向。由此,本文算是完成了一種通過敘事分析的傳說學向內容分析的文化學的轉換的嘗試。作者希望這種嘗試能夠兼顧乃至銜接民間文學的研究與以民間文學為對象的民俗學、文化學的研究。
I207.7
A
1008-7214(2017)06-0059-07
鄒明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丁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