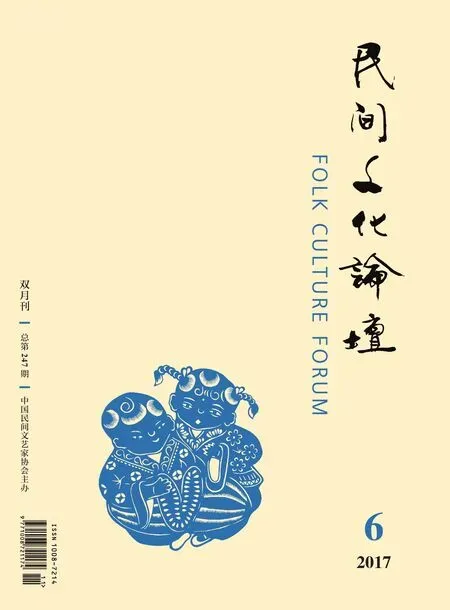邁入21世紀的口頭史詩:以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為例*
[德 ]卡爾? 賴希爾(Karl Reichl) 著 陳婷婷 譯
邁入21世紀的口頭史詩:以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為例*
[德 ]卡爾? 賴希爾(Karl Reichl) 著 陳婷婷 譯
隨著世界各地識文斷字的人越來越多,口頭傳統遭到了邊緣化。科學技術的革新,從收音機到電影電視再到英特網,大眾可以接觸到各種新的娛樂形式,這使得史詩演述者的聲音顯得多余。在很多情況下,口頭史詩被轉化為書面文本,以書籍的形式呈現。有時口頭史詩也被轉化為更為流行的新式,比如卡通、電影、木偶戲或者互動游戲。要說更為正式的形式,則是由口頭史詩改編的歌劇、詩體改寫和重述。雖然上述種種變化都出現在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上,但該史詩的口頭演述和口頭傳統在吉爾吉斯斯坦和新疆的柯爾克孜語地區仍具有驚人的活力。一方面,我們曾有九十多歲高齡的著名的新疆柯爾克孜瑪納斯奇居素普?瑪瑪依;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才四五歲就能演述相當長度的史詩段落的小史詩歌手。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本文將討論柯爾克孜史詩傳統向年輕一代傳承的方式,以及為何史詩《瑪納斯》在柯爾克孜族的文化認同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
《瑪納斯》;柯爾克孜;口頭傳統;傳承;演述
1995年,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舉行了“千年瑪納斯”慶典,慶祝史詩《瑪納斯》問世1000年。1000年前,當一位來自西歐的旅行者橫跨了如今分屬德、俄、法、英四國的廣袤區域,收集當地詩歌時,發現這些詩歌中絕大部分都是口頭創編、演述、并代代傳承的,這一情況與在中亞出現的情形頗為類似。一些詩歌是敘述性的,并且大部分篇幅是歌頌由神或英雄做出的英勇事跡。英雄歌無疑盛行于這一地區。這些英雄歌中的一些可能含有史詩的成分,雖然中世紀史詩無論它們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都無法與篇幅宏大、內容廣博的藏族史詩《格薩爾》以及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相比。
在中世紀的進程中,書寫技藝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而口頭創編和演述詩歌的技藝卻日益遭到邊緣化。這當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只有當15世紀印刷術發明之后,口頭詩歌才逐漸從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學形式中消失。口頭詩歌仍然在不斷被創編和演述,只是在多數情況下面向的觀眾是流行大眾。史詩歌手復雜精巧的演述技藝被街頭歌謠演唱者的粗糙質樸的用韻所取代。傳統民間歌謠演唱者的演述鮮有人聞。早期口頭敘事詩的現代遺存,恐怕只有在博物館的展件、民俗節的歌唱表演和戲劇舞臺上才能找到了。
作為一個歐洲人,我在亞洲見證了仍然勃興的口頭史詩傳統,不禁產生了疑問:在亞洲,史詩歌手的技藝是否也經歷了與歐洲早期階段的史詩歌手相似的衰落。觀照各色操持突厥語的人,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衰落確實正在發生。這是一個緩慢的進程,并且在一些地區發生的比另一些地區更慢。早在19世紀中葉,匈牙利突厥學家萬別里(Herman V á mb é ry)就預言到,中亞的發展進步很快將會把舊的生活方式席卷殆盡,隨之而去的還有口頭傳統。在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巨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加速了口頭史詩傳統在許多蘇聯突厥語地區的衰落:譬如韃靼地區、巴什基爾地區、阿塞拜疆地區、土庫曼斯坦地區、烏茲別克地區、卡拉卡爾帕克地區、哈薩克地區和雅庫特地區,等等,不一而足。對土耳其也可以做出相似的結論,20世紀初葉,凱末爾?阿塔蒂爾克發動的革命對土耳其進行了一場徹底的變革。阿塔蒂爾克發動的變革一直延續,在20世紀50年代甚至出現加速,難怪2008年土耳其民俗學家伊爾漢?巴什葛茲(?lhan Ba?g?z)在他關于土耳其民間傳奇故事的著作(叫做hikaye)的結尾中做出這樣的評論:近幾年的社會變革幾乎摧毀了土耳其的口頭史詩演述藝術。
我剛才提到的改變并沒有立即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生存產生影響。有趣的是,倒是在農業集體化實行多年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蘇聯突厥語地區的口頭史詩演述得以被錄音,當時很多通過傳統方式習得演唱技藝的史詩歌手還在世。其中很多杰出的歌手活到了20世紀下半葉,甚至活到了21世紀。朱馬拜吉繞?巴扎羅夫(Jumabay-jirau Bazarov)是卡拉卡爾帕克人(一個生活在烏茲別克斯坦咸海南部的民族)當中最后一個純粹的傳統史詩歌手,我很幸運在他2006年去世前將他的演唱曲庫完全錄制了下來。
在一些地區,史詩吟誦的技藝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這得益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大力支持,一些講突厥語的人能夠藉此機會為這個瀕于消失的史詩吟誦傳統注入新的活力。譬如,雅庫特史詩傳統就是一例。他們的口頭史詩《歐隆克》(Olonkho)于2008年被收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比格薩爾史詩收入該名錄早一年。這激發雅庫特人開展了一大批新的活動。雖然這些活動并未催生新的史詩藝人,但卻提升了雅庫特人對自身口頭傳統的意識和自豪感,更為重要的是,加強了人們對這一本土傳統在收集、建檔方面的重視。
收集和建檔是口頭史詩現代研究領域的重要目標,特別是民間還有需要去收集的史詩。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已經被巧妙地安排在關于格薩爾史詩傳統的9年計劃中:
建立9個目標基地,以保護史詩傳統;
成立3個培訓學校,以支持年輕史詩演述者;
設立12個史詩演述場所,提供給當地少數民族社區;
開展長期跟蹤觀察和在地化的田野研究;
為史詩傳統傳承人建立檔案;
建立“格薩爾史詩傳統國家檔案”;
組織“國際格薩爾史詩演述節”;
促進那些可以傳播和欣賞史詩傳統的教育項目。
然而,不論外界支持和國際認同有多么重要,口頭傳統的生命力的葆有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與這一口頭傳統所植根的土壤息息相關的因素。只有一個突厥語地區成功地將其口頭史詩傳統延續到了21世紀。我所提到的延續史詩傳統的柯爾克孜人,既包括生活在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的柯爾克孜人,也包括生活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柯爾克孜人。為何口頭史詩吟唱的技藝仍然在柯爾克孜人中流行,而在哈薩克人、維吾爾人和烏茲別克斯坦人這些近鄰中卻沒得到相同程度的流行呢?這當然有些歷史性因素。維吾爾人和烏茲別克人已有數個世紀的書寫傳統,這就意味著,與柯爾克孜人相比,口頭史詩在維吾爾人和烏茲別克人的文化中扮演著更為次要的角色。哈薩克人與柯爾克孜人一樣有高度發達的口頭藝術,生活方式上保持著延續了幾個世紀的游牧式畜牧主義。書面文化早早就被引介到哈薩克人當中,哈薩克斯坦20世紀的社會變革對傳統生活和藝術形式都有深遠的影響。在如今的哈薩克斯坦,雖然在克孜勒奧爾達開設了傳統音樂學校專門培訓歌手,但史詩歌手仍然很少。可是,在歌曲大賽(aytys)上即興創編歌曲的技藝仍然十分流行。
19世紀,柯爾克孜最濃厚的口頭史詩傳統存留于所有操持突厥語的人中。瓦西里?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在其1885年出版于圣彼得堡的柯爾克孜口頭詩歌譯著中評價道:“柯爾克孜人極其純熟地掌握著他們的語言。他們語言十分流暢,沒有停頓或遲疑,并且知道如何在表述清楚簡潔的同時不失優雅。即使是在日常談話中,他們的句子結構都富于清晰的韻律,這說明他們將句子像詩句和詩節一樣連綴起來,聽起來猶如詩歌。”但修辭的華麗并不足以使一項口頭傳統生機永存。只有當傳統代代相傳時,才具有生機。和生活在西方工業文明世界或中國城市中心的年輕人一樣,吉爾吉斯斯坦的年輕一代也同樣程度地接受著全球化后現代文化的影響。年輕的柯爾克孜男女對音樂的喜好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同代人并無太大區別,他們也同樣熱衷于享受現代娛樂和交流技術所提供的便利。這種情況也同樣出現在老一輩人當中,至少在原則上是這樣。來自新疆的柯爾克孜族歌手馬拜特?薩爾塔袞(Mambet Sartakhun),我第一次給他錄音是1989年。等到我2011年再次找他錄音時,他已經用上了智能手機。但他的手機鈴聲倒是很傳統:那是史詩《瑪納斯》的旋律!
雖然正經歷著現代化,但本土的傳統仍然在延續。You Tube上有一段視頻,里面一個五歲大小的柯爾克孜男孩正在演述《瑪納斯》的選段。這并不是特例。在1995年吉爾吉斯斯坦舉行的“千年瑪納斯”慶典上,許多年輕人——其中許多還是孩子——都在演述《瑪納斯》選段。年輕的柯爾克孜男女無疑還可以有學習《瑪納斯》的興趣,雖然掌握口頭演述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只靠興趣是遠遠不夠的。瑪納斯史詩藝人(瑪納斯奇)必須記誦整部史詩的相當長的篇幅,才能被認可為一位合格的演述者。要學唱《瑪納斯》,光有好記性是不夠的,還需要畢生對演述藝術的執著投入。決定成為瑪納斯奇往往是經驗性的。很多史詩藝人都曾提及自己特殊的經歷。根據他們的講述,他們在睡夢里或幻境里受命演述瑪納斯,并被賦予了神奇的技藝和力量。這樣的“夢授說”也見于其它傳統中:譬如在藏文化中就有。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掌握一部史詩并不只是對記憶力的考驗和刻苦學習的結果,還需要藝人本身的特殊稟賦和全身心的執著。
如今,年輕的柯爾克孜史詩藝人已經約定俗成地從文本中學習史詩,而不再靠老師的言傳身教。教授史詩的老師,例如大師級史詩藝人,仍然招收學生,譬如新疆的柯爾克孜史詩藝人馬拜特?薩爾塔袞。2011年我為他的3個學生錄音。這些學徒藝人一方面通過老師的口授學習技藝,另一方面仍然通過書面文本或錄音材料來學藝。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阿地里教授通過調查發現,新疆的44個瑪納斯奇中,有41個通過印刷或手寫的書面文本來學唱史詩。磁帶、視頻和DVD的應用也很廣泛。這樣的學習方式說明文本是被記誦的。然而,當一個藝人已經記誦了相當長篇幅的文本,他對史詩所用的語言的音步也就熟悉起來。這就意味著,一個史詩片段也可以用不同的話語加以表述,但一定是在史詩特定的形式和音步的框架下。對口頭史詩的口頭程式特性的研究已經對我們理解這一現象起到了幫助。
為何《瑪納斯》仍然作為口頭史詩加以流傳,而其它突厥傳統中的史詩僅存現于書面形式或經過改編的電影、戲劇、歌劇中?反觀“柯爾克孜現象”,我們可以從中推測出使口頭史詩傳統保持生機的原因。依我之見,傳統口頭藝術得以生存延續的最重要因素是它在自身得以實踐的文化評價體系中擁有一個位置,或許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就意味著,該口頭藝術被視為其文化中的一個連續性因素,它的缺失將導致文化空間的巨大改變。當然,改變總是不斷發生的,而且象征著生機而不是衰退。語言總是不斷發生著變化,所有的文化事件和思想模式亦然。但缺失則是另一回事。語言學家告訴我們,語言一旦失傳,就很難再恢復生機。
文化價值系統的中心位置常常會被宗教概念所占據,而且可以看出,文化中宗教實踐和儀式與口頭史詩相關聯的部分(比如在印度),往往更容易存活并延續下來。但《瑪納斯》不是一部宗教史詩。伊斯蘭教在這部史詩居于次要位置,而且我們可以確定,柯爾克孜的英雄詩傳統比伊斯蘭教傳入中亞的時間要早。雖然在《瑪納斯》中可以找到薩滿教和其他一些前伊斯蘭教概念的蹤影,但對史詩整體來說,它們既不居于中心位置,也不具有典型特征。
C.M.鮑勒(C. M. Bowra)在其著作《英雄詩》(Heroic Poetry,1952年出版于倫敦)中,將英雄詩定義為動作的詩。在《瑪納斯》中確實有很多動作,而這部史詩之所以吸引聽眾,部分原因想必是因為引人入勝、充滿張力的故事。但這并不是其主要吸引力之所在。任何一部現代動作電影中,都有比《瑪納斯》更讓人激動的驚險場面。如果傳統史詩的寶貴之處僅僅局限在其娛樂價值上,那么它就很容易被其它形式的娛樂所侵蝕,而我們的技術時代恰恰擁有大量的各色娛樂形式。
當我們仔細審視史詩和它在柯爾克孜社會中的作用時,或許可以給出答案。根據由居素普?瑪瑪依的演述所記錄下的《瑪納斯》,在英雄誕生之前,詩行已經延展了1700多行。與此相似的是,在根據薩基姆拜?奧拉巴闊夫(Saghymbay Oroabaqov)的演述所寫下的《瑪納斯》中,英雄誕生于第1580行。史詩介紹性部分的重點,英雄誕生前的1500多行詩句,都是圍繞部落起源和歷史所展開的:柯爾克孜族來自哪里,誰是他們的祖先,他們的早期歷史是怎樣的。這樣的問答在史詩中不斷出現,不僅出現在開頭部分,而且貫穿整個情節。從這一點上講,《瑪納斯》與柯爾克孜中流傳的另一個口頭傳統文類頗為接近,這就是口述家譜。正如在其他游牧社會中,氏族與部落的聯盟組成社會主干。應當知曉自己的“七個祖先”(jeti ata),這樣的觀點在哈薩克人、卡拉卡爾帕克人和柯爾克孜人中被廣為認可和接受,但并不一定得到嚴格的執行。一個人其在氏族部落系統中的位置,將“歷史地”定義這個個體。
我想,對于大多數柯爾克孜人來說,瑪納斯是他們柯爾克孜身份屬性的一部分。即使他們對這個史詩并不十分了解、對其口頭演述的認識也僅僅來源于電影或電視節目。早些時候,在書面文化得以傳播和歷史編纂學發明之前,像《瑪納斯》這樣的史詩是被當成歷史來看待的:它是關于種族的歷史,關于起源的故事,關于種族子群發展和聯盟的記述。當然,在現代社會,《瑪納斯》和其它類似史詩的真實性遭到了人們的質疑。甚至史詩藝人也堅持聲稱自己并沒有親臨其所敘述的場景。柯爾克孜史詩中有這樣一個程式,那就是“半真半假”。另一方面,史詩藝人強調自己在傳承鏈上的位置,將他們的知識作為確真的知識而加以合法化。英雄和各種事件被當成與聽眾的祖先和部落起源有關的史實加以呈現,這使得史詩最終成為史實。民族身份無疑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確認。
所有民族都需要民族身份的象征,所有群體都需要象征著群體團結的標志。許多國家的機場都以該國的杰出人物命名,譬如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巴黎的戴高樂機場和波恩-科隆的康拉德阿登納機場。吉爾吉斯斯坦的比什凱克國際機場名為“瑪納斯”。比什凱克機場采用這樣的方式銘記史詩英雄的名字,或許顯得比較獨特。對柯爾克孜人來說瑪納斯無疑具有象征意義。
I207.9
A
1008-7214(2017)06-0066-04
卡爾?賴希爾( Karl R eichl),德國波恩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口頭傳統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譯者簡介]陳婷婷,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系博士。
* 本文根據卡爾?賴希爾(Karl Reichl)教授于2012年7月17日在青海西寧“格薩爾與世界史詩”國際學術論壇大會上所發表的英語論文翻譯而成。賴希爾教授欣然同意并授權《民間文化論壇》在中國首發該文的中文版。
丁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