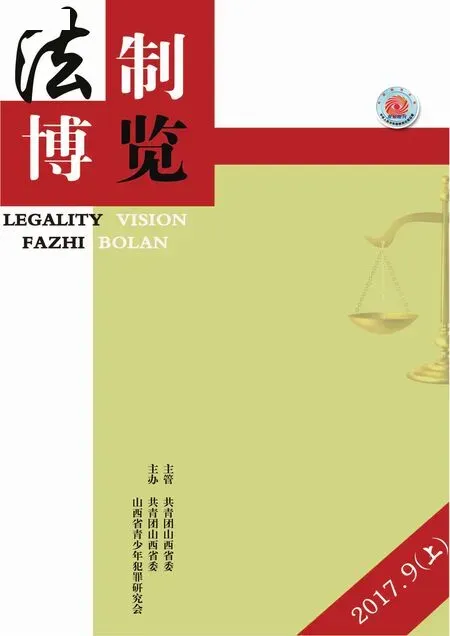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內涵解析
王永祥
河套學院,內蒙古 巴彥淖爾 015000
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內涵解析
王永祥
河套學院,內蒙古 巴彥淖爾 015000
清末的放墾蒙地政策的推行,以及后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使得蒙古民族的草場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面積縮小嚴重,部分用于放牧的草場被開墾耕種。1947年4月23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通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綱領》第十條規定:“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之完整”。群體共有以及日耳曼所有權也有類似的制度構造。
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土地總有權;群體共有;總同共有
一、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的緣起
從鴉片戰爭開始,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國推行所謂“新政”,針對蒙古民族草場所有權最主要的政策就是“放墾蒙地”。放墾蒙地就是允許漢族的農民以向政府繳納押荒銀和地租為條件來開墾和租種原蒙古人用于放牧的草場。這一政策實質上嚴重破壞了蒙古民族的草場所有權和經營權。“放墾蒙地的直接后果是,大片水草豐美的牧場被墾種,清政府既得地利又獲地權;而大批蒙古族牧民被排擠驅趕到山區荒漠和邊遠地帶,少數被迫轉務農業,這對蒙古民族是一場空前的災難;大批被招墾種蒙地的漢族農民,也要付出難以承受的大量的押荒銀和地租,遭受承重的經濟搜刮。而放墾官員和地商正是從中漁利和肥私者。”[1]清末的放墾蒙地政策的推行,以及后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使得蒙古民族的草場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面積縮小嚴重,部分用于放牧的草場被開墾耕種。
在這種背景下,《綱領》第十條規定:“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之完整。保護牧場,保護自治區域內其他民族之土地現有權利。”
二、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的內涵解讀
李玉偉教授的以下說法涉及到《綱領》第十條的土地總有權制度:“土地分配的政策是要沒收敵偽土地分配給貧苦無地的農民,同時規定了兩個原則。第一,分配土地時,要照顧基層群眾的利益,不分蒙漢,使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第二,強調保護蒙地總有權。政府在分給農民土地后,頒發地照;分得土地者可以使用、受益或出賣,但必須交納蒙租。”[2]閆天靈博士的以下說法也涉及到《綱領》第十條的土地總有權制度:“明代時,蒙古地區的土地由鄂托克、愛馬克(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單位,一個鄂托克由一個或多個愛馬克組成)等憑自治力量來占有分配,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完全由部落統一進行,即土地歸各旗總有。清初劃分旗界后,延續了各旗的土地總有制。蒙旗土地的總有制,與蒙古游牧經濟是連為一體的。清中后期,隨著放墾及漢民的移入,農業經濟和租佃關系發展起來。20世紀后,蒙旗土地總有制在農業區和半農業區已基本瓦解。“土地總有”成為廣義上的概念。這里所講的保護蒙地總有權,就是確保土地在本旗蒙古族民眾之間流轉,實質上是私有的。”[3]
本文認為,以上的解讀有幾個問題值得商榷。第一,關于“分得土地者可以使用、受益或出賣,但必須交納蒙租”的表述。李玉偉教授文中所指的蒙古族農民分得土地后,享有使用、受益和出賣三種權利,但需要承擔繳納蒙租的義務。從法學的角度,應該將其修改為“分得土地者享有使用權能、收益權能和處分權能,但必須交納蒙租”。“受益”和“收益”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不同的學科引起的表述上的差異。出賣是指所有權的轉移。只有享有所有權的主體才可能享有出賣的權利,如果當時分得土地的蒙古族農民享有所有權,那么為什么還要繳納蒙租呢?顯然,李玉偉教授想表達的意思是土地的轉包,實質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這是一種處分權能。第二,關于李玉偉教授在注釋中參考的閆天靈博士的觀點:“土地在本旗蒙古族民眾之間流轉,實質上是私有的”。如前所述,既然要繳納蒙租,說明當時的蒙古族農民并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就是說土地不是私有的。流轉是以繳納土地租金為條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移,是承包人與轉包人之間通過轉包合同轉讓經營權的法律行為。土地所有權歸屬不發生變更,因此,也不能將其界定為:“實質上是私有的。”
三、與《綱領》第十條類似制度的比較及本文觀點
第一種與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較為相似的制度是越南的群體共有,韓松教授稱其為總同共有。《越南民法典》第234條:“群體共有的宗族、村、邑、鄉、宗教群眾和其他居民群體對用于滿足整個群體的合法共同利益目的按習慣形成的財產、群體成員貢獻、捐獻的財產、接受的贈給、整個群體的財產和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來源的財產的所有,群體的各個成員根據協議或習慣,為了本群體的共同利益共同管理、使用、處分本群體的共同財產,但不得違反法律和社會道德,群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共有財產”。這是《越南民法典》規定的群體共有制度,這一制度與《綱領》第十條規定的保護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極為相似。這種共有形式既不屬于按份共有也不是共同共有,韓松教授將其概括為總同共有:“農民集體所有權可以采取由一定的集體范圍內的全體農民集體成員共同所有的形式,而且認為這種共同所有形式,不可能采取我國民法中現有的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形式,而是在繼承和更新傳統總有形式的基礎上的一種新型總有形式。為了從邏輯關系上與我國民法中的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并稱,我將這種新型總有稱之為總同共有。”[4]
另一種與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較為相似的制度是日耳曼民族的馬克爾公社公有制。日耳曼民族的早期也是游牧生活,后來定居之后,土地由公社共有,在公社內部分給個人,這就是日耳曼民族早期的土地公有制。這和蒙古民族的土地總有權制度很相似。韓松教授對日耳曼法上的所有權做了如下概括:“在羅馬法上,一個物上只能有一個所有權,所有權具有單一性和歸一力,在本質上為所有人的自由處分權。而日耳曼法上的所有權,以物的利用為中心,其意義是具體的、相對的,所有權之內容不過為物之完全利用權而已。”
本文認為,無論群體共有還是總同共有亦或是日耳曼所有權,其共性就是所有權能與其他全能分屬于不同的主體行使。這也是蒙古民族土地總有權制度最大的特點,由蒙古民族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而收益權和承包經營權由蒙古族集體成員行使。
[1]郝維民.內蒙古革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2]李玉偉,劉瀚倫.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土地工作研究[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9(5).
[3]閆天靈.漢族移民對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71-282.
[4]韓松.論總同共有[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0(4).
河套學院科研課題《法的運行視角下內蒙古失地農民權益保障研究》(項目編號:HYSQ201522);內蒙古大學研究生科研項目《內蒙古農民依法維護土地承包經營權意愿缺失的影響因素和對策研究》(項目編號:S20161012619)。
D
A
2095-4379-(2017)25-0051-02
王永祥(1985-),男,漢族,內蒙古四子王旗人,法律碩士研究生,河套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