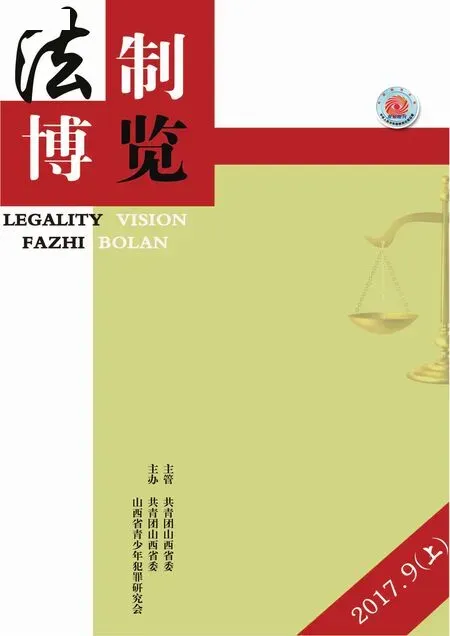職務侵占罪和侵占罪該如何界分
——以何某侵占一案為例
張貴湘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1
職務侵占罪和侵占罪該如何界分
——以何某侵占一案為例
張貴湘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1
職務侵占罪與侵占罪的認定,在理論研究與司法適用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難題。本文以何某侵占一案為例,從犯罪構成的角度去分析職務侵占罪和侵占罪,并結合對委托和私力救濟等法律關系的甄別,最終合理界分二者。
職務侵占罪;侵占罪;委托;私力救濟
一、案情簡介
何某與某公司同時簽訂了勞動合同和《銷售人員責任書》,其中,約定何某在離職時,按照某公司規定追繳所有應收貨款,或交接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某日,某公司通報解除與何某的勞動合同關系。之后,何某向公司交接了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但是,何某與某公司在勞動報酬數額問題上發生糾紛(何某認為公司欠其40多萬報酬未給付,公司拒不承認),久拖未決。一日(解除合同后),何某接到某公司銷售工程師朱某(接任了何某的工作)通知,去南豐某公司取其經手的支票(金額11萬余元),并允諾付給其相應的報酬。取到支票后,何某給某公司經理耿某通電說支票在其手中,讓某公司先償清欠款并與其簽訂一個協議之后,再將支票給公司。由于沒有談成,何某遂將支票自留,并托關系將支票兌換成現金。之后,某公司報案,公訴機關以職務侵占罪起訴何某。
二、爭議焦點
本案中,公訴機關以職務侵占罪提起公訴,并從職務侵占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上進行了詳細論證。但是,筆者認為公訴機關的論證存在以下矛盾:
第一、混淆了“職務性行為”與“職務行為”。公訴機關認為何某“對外還是以某公司人員的名義從事職務性行為”,筆者認為公訴機關將“職務性行為”與構成要件中的“職務行為”相混淆。職務性行為并不等同于職務行為,職務行為要求行為主體必須具備特殊主體身份,而職務性行為只要具備職務行為的外觀即可,其行為主體不一定具備特殊主體身份。第二、由職務性行為草率推導出行為主體具備職務侵占罪要求的特殊主體身份。公訴機關認為:職務侵占罪中,只要犯罪行為人實施了職務性行為,就能夠推導出其具有職務侵占罪要求的特殊主體身份。筆者認為這是邏輯上的推理錯誤,由前述可知,履行職務行為的人是適格主體,但履行職務性行為的人則不一定是適格主體。所以,由職務性行為不能直接反推出行為人具備特殊主體身份。第三、公訴機關錯誤認為何某協助追繳欠款行為的權利來源是基于勞動合同中的“《銷售人員責任書》”,并由此認定何某在作出該行為時具備特殊主體身份。由案情簡介可知,何某與某公司之間的勞動關系這一基礎性關系,在雙方解除勞動合同時就已經歸于消滅。何某在離職后協助追繳欠款行為是基于某公司新的委托而行使的委托權,非基于單位人員主體身份而履行的職務行為。
綜上,筆者認為何某不構成職務侵占罪,下文將對相關問題進行具體闡述和論證。
三、定罪分析
(一)何某追繳欠款的權力來源?
本案中,認定何某是否成立職務侵占罪,其中一個關鍵點在于何某追繳欠款的權力來自何處?
從本案證據看來,有一份《銷售人員責任書》,其中第十四條規定:“乙方無論何種原因離職,均需按甲方規定追繳所有應收貨款,或交接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如沒有有效憑證必須追繳應收款,否則甲方有權要求乙方按造成甲方實際損失予以賠償”。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只要何某完成“追繳所有應收貨款”或者“交接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中的任意一條,就可以無責離職。由本案可知,何某在離職前已經交接了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根據《銷售人員責任書》的規定,已經不用再承擔追繳應收款的義務。何某繼續為公司追繳應收貨款的行為是基于,公司在何某離職后,重新與其達成的委托協議,是某公司委托何某幫助其追繳應收貨款。因此,《銷售人員責任書》延伸于何某身上的義務已經終結,其效力不能再及于何某后來追繳應收貨款的行為。所以,何某追繳應收貨款的權力來源不是《銷售人員責任書》,而是來源于后來的委托合同。
(二)何某是否具備職務侵占罪的特殊主體身份?
《刑法》第271條規定: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1]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占本單位財產,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僅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并不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因此得知,具備“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的適格主體身份,是構成職務侵占罪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
本案中,由前文可知,何某已經交接應收款的全部有效憑證,依照雙方簽署的《銷售人員責任書》規定,何某已實現法律意義上的清責。之后,何某繼續為某公司追繳欠款的行為,是基于與公司之間達成的另一個委托合同而行使的處理委托事務的權能,并非是基于適格主體身份而實施的職務行為。不能因為何某履行了一個與公司職員相類似的職務性行為,就反推出何某此時依然具有某公司職員的主體身份,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顯而易見,何某因不具備職務侵占罪所要求的特殊主體身份,所以不構成職務侵占罪。
(三)何某的行為是否成立私力救濟?
私力救濟,指行為人不求助于公權力,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單純依靠個人力量來救濟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權利。[2]私力救濟至今仍存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與公力救濟互為補充,共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民權益。私力救濟包括自助行為和自衛行為。自衛行為包括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
其中,自助行為的構成要件為:(1)行為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請求權。(2)當時情況緊急,行為人來不及請求公力救濟,并且如果不及時實施自助行為,請求權將難以實現。例如,若商店發現顧客偷盜商品,即將離店而去,附近又沒有警察可以及時求助,這就屬于來不及請求公力救濟的情形。此時,商店就有權禁止盜竊者離店,并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要求盜竊者交出所偷商品。(3)行為人的自助行為沒有超出法律規定的必要限度。具體而言,能扣留財物就不得毀壞財物;能毀壞財物就不得危及人身。(4)行為人實施自助行為后,必須及時請求公權力的救濟。
結合本案來看,首先,被告人何某擅留公司財物的行為雖為保護自己的請求權,但并未達到情勢緊迫,來不及請求公力救濟的程度。雖然何某對公司給予的勞動報酬有爭議,但是,完全可以通過訴訟等途徑以實現自己的合法權利。從本案來看,何某從始至終,并未尋求任何的公力救濟,當然也就不存在“如果不實施自助勢必導致請求權難以實現或者無從實現”的危險情形。其次,公司與何某對勞動報酬有所爭議,林峰公司事實上欠何某的工資到底為多少?何某私自占為己有的11萬余元,是否明顯超過公司的欠款額度等等?這些問題都還需要雙方當事人提供可以證明欠款數額的證據來予以解決。最后,何某在拿到現金支票后,仍就沒有及時尋求任何公力救濟。事后,何某雖與某公司經理耿某通話,以持有的公司支票為籌碼商談報酬事宜,但該行為并不構成公力救濟。綜上,何某擅自將公司財物占為己有、拒不交出的行為不成立私力救濟。
(四)何某是否必然構成侵占罪?
根據刑法第270條的規定,侵占罪是指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或者他人的遺忘物、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或者拒不交出的行為。[3]由法條可知,成立本罪,主觀上行為人需具有非法占有的直接故意,侵害的客體是他人對財物的所有權,客觀上實施了侵占行為。注意,構成侵占行為的前提是事先合法地持有他人財物[4]。在此前提之下,才有必要繼續認定何為“非法占有”、“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拒不退還”和“拒不交出”等問題。
具體而言,(1)“合法地持有他人財物”,應作行為人不是基于自己的違法行為而持有他人財物的理解,若行為人是將他人控制和管領下的財物非法據為己有,則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可能構成盜竊、搶奪、搶劫等重罪名。[5](2)“非法占有”是指沒有法律根據地取得和控制他人財物。[6](3)所謂“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應當指通過合法手段持有的所有權屬于他人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既包括短期持有也包括長期持有。從司法實踐來看,“代為保管他人財物”的客觀事實和法律行為主要包括委托、借用、租賃、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對擔保物的占有等情形。(4)拒不退還與拒不交出的行為,是構成侵占罪的必備要素。界定該行為的核心在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是否足以證明其具有永久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本案中,何某繼續代為追繳欠款的權力來自某公司的委托,收取他人轉賬支票是依法處理委托事務,所以何某是事先合法的占有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符合侵占行為所要求的前提條件。何某在拿到轉賬支票后,以工資未結清為由,拒不交出支票,并托關系兌換成現金取出據為己有的行為,屬于沒有法律根據的取得和控制他人財物,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外,侵占的金額為11萬余元,遠超過侵占罪要求數額較大的法定入罪標準。綜上,對何某侵占一案應以侵占罪定罪處罰。
[1]盧建平,邢永杰.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便利”認定中的若干爭議問題[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2):97-104.
[2]沃耘.民事私力救濟的邊界及其制度重建[J].中國法學,2013(5):178-190.
[3]劉三木.關于侵占罪客觀行為方面幾個爭議問題的探討[J].法學評論,2005(6):32-36.
[4]趙秉志.侵犯財產罪研究[M].第3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311.
[5]陳璇.論侵占罪處罰漏洞之填補[J].法商研究,2015(1):136-146.
[6]王鋼.不法原因給付與侵占罪[J].中外法學,2016(4):928-954.
D
A
2095-4379-(2017)25-0091-02
張貴湘(1993-),女,貴州興仁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