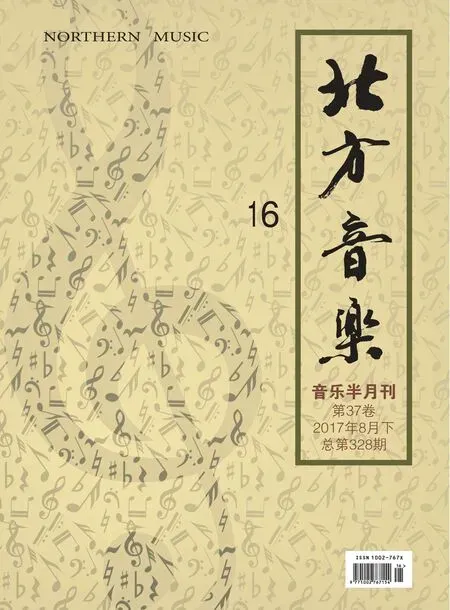論音樂表演的游戲因素
肖金勇
(廣東嘉應(yīng)學(xué)院音樂與舞蹈學(xué)院,廣東 梅州 514015)
論音樂表演的游戲因素
肖金勇
(廣東嘉應(yīng)學(xué)院音樂與舞蹈學(xué)院,廣東 梅州 514015)
在音樂表演實(shí)踐中借鑒游戲手法滲透進(jìn)某些游戲因素,又不至于使藝術(shù)的精神內(nèi)涵喪失于游戲的迷宮中。更多地汲取原生態(tài)音樂的率真質(zhì)樸和生命活力,使我們的民族聲樂事業(yè)在固有的大河中,以多樣化的姿態(tài)滾滾向前;使我們的美聲唱法,在共享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的基礎(chǔ)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使我們的流行唱法,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原生態(tài)音樂對(duì)接,使音樂表演藝術(shù)健康地、健全地發(fā)展。
音樂表演;游戲因素;游戲性;諧謔之美
藝術(shù)與游戲有不解之緣。它們不僅在起源上有親密的關(guān)系,而且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互補(bǔ)互利,攜手共進(jìn),伴隨著人類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今天,并展望璀璨的明天。正如柏拉圖在《法律篇》卷七中所指出:“每一個(gè)人都要依此為職責(zé)。讓美麗的游戲成為生活的真正內(nèi)涵。游戲、玩樂、文化——我們認(rèn)定這才是人生中最值得認(rèn)真對(duì)待的事。”[1]
一、音樂表演中的游戲因素
作為一種藝術(shù)本體論的“游戲說”,在美學(xué)史上正式開始于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由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jiǎn)》中予以發(fā)揚(yáng)光大。“游戲說——用游戲活動(dòng)揭示藝術(shù)起源和審美本質(zhì)的美學(xué)原理。認(rèn)為游戲在形態(tài)上多為對(duì)實(shí)際生活活動(dòng)的模仿,在性質(zhì)上是與純粹快感相結(jié)合的身心自由活動(dòng)。康德提出‘自由游戲’是審美快感的根源,席勒發(fā)展了這一論點(diǎn),認(rèn)為藝術(shù)沖動(dòng)是一種‘游戲沖動(dòng)’,表現(xiàn)為‘形式?jīng)_動(dòng)’和‘感性沖動(dòng)’的總和。游戲的根本特性是人性中理性與感性的和諧。游戲的狀態(tài)即自由審美狀態(tài),審美即游戲,藝術(shù)起源于這種游戲……朗格認(rèn)為,藝術(shù)是形式成熟的游戲。谷魯斯認(rèn)為“藝術(shù)是高級(jí)的游戲”[2]這是一種從藝術(shù)本體論角度出發(fā)的游戲觀,并非狹義的游戲的釋義。是一種宏觀的藝術(shù)游戲觀,是一種審美的游戲觀,對(duì)于音樂表演來說起碼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具有積極的啟迪作用:在想象力的自由翱翔、理解力的自由馳騁、創(chuàng)造力的自由心境方面給予音樂表演以有益的啟發(fā),有利于弘揚(yáng)音樂表演的詩性品質(zhì);游戲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同樣,音樂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因此,音樂表演要注重生命力的展示和釋放;游戲必須遵守游戲規(guī)則,音樂表演也要恪守音樂的內(nèi)在規(guī)則及規(guī)律,以及音樂表演的規(guī)則。游戲活動(dòng)中,藝術(shù)地運(yùn)用技術(shù)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這也是作為成人游戲主要形式的各種球類運(yùn)動(dòng)和下棋等活動(dòng),能給我們以樂趣的原因所在。
二、游戲因素在音樂表演中的作用
音樂表演是以技術(shù)運(yùn)用為基礎(chǔ)的。在音樂表演中,技術(shù)與表達(dá)是一對(duì)難以把握的矛盾,成功的音樂表演者是把握這對(duì)矛盾的高手,技術(shù)與表達(dá)的辯證統(tǒng)一,技術(shù)與表達(dá)的和諧融合,是音樂表演的最高境界。如中央電視臺(tái)舉辦的第13屆青歌賽上,歌手演唱、表演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均與上述三個(gè)方面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從音樂表演的角度來看,原生態(tài)歌手及流行歌手的表演相對(duì)于美聲唱法及民族唱法的歌手,在想象力的自由翱翔,創(chuàng)造力的自由心境,生命力的展示及釋放方面有著極大的優(yōu)勢(shì)。相較之下,一些美聲唱法的歌手及民族唱法的歌手往往端著架子、繃著臉在演唱,呆板的表演削弱了音樂表演的魅力。以致有人認(rèn)為“青歌賽”的亮點(diǎn)在于余秋雨評(píng)委的文化知識(shí)的點(diǎn)評(píng)。盡管這種說法有其片面性,但從宏觀的藝術(shù)游戲觀、審美的游戲觀的角度來看,一些歌手缺乏超功利的自由心境、放松的表演心態(tài),豐富想象力和理解力,這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在青歌賽上,新疆喀什地區(qū)原生態(tài)組合演唱的《刀郎木卡姆》給人以為之一振的藝術(shù)沖擊力。他們上臺(tái)來張口就唱,唱即入情,入情便沉醉,原本在生活中,他們就是這樣率真地歌唱,分不清這是生活狀態(tài),還是舞臺(tái)藝術(shù)狀態(tài),沒有虛情,沒有假意,沒有包裝,沒有宣傳,生命的活力與張力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正應(yīng)了那句古話——唯樂不可以為偽。他們質(zhì)樸、活潑、狂放、自在的演唱及對(duì)生命力的展示和釋放深深地打動(dòng)了觀眾和評(píng)委,他們的演唱獲得高分自然在情理之中。原始藝術(shù)的粗獷的生命張力,質(zhì)樸的田野氣息,活潑生動(dòng)的游戲沖動(dòng),自在自得的愉悅心境應(yīng)該為被稱作為“高雅藝術(shù)”的美聲唱法及民族唱法“充電”、輸血。
與此遙遙相對(duì)的是現(xiàn)代商品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催生的通俗音樂。作為理解當(dāng)代審美文化的捷徑。它的出現(xiàn),與當(dāng)代社會(huì)歷史條件所產(chǎn)生的變化密切相關(guān),可以定位為在當(dāng)代社會(huì)條件下所出現(xiàn)的公共藝術(shù)的重要門類之一。它的文化、美學(xué)函義,可稱之為人的還原,美的還原,人類童年的游戲精神的還原。真實(shí)的生活往往是具體的,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崇高,也不卑下,于是,它著力為具體的生活立法,把傳統(tǒng)認(rèn)為有意義的東西還原為無意義,又在無意義中展示出新的意義,追尋著具體的纏綿、具體的溫柔、具體的傷感、具體的美麗……使人們不再仰望,而是平視;不再說教,而是娛樂;不再敬畏,而是參與,廣義的游戲精神和狹義的游戲精神盡顯其中。因而,敏捷地激活了人們的生存意識(shí),激活了瀕臨僵死的傳統(tǒng)美學(xué),激活了藝術(shù)中的游戲意識(shí),稟賦了一種異常的親和力。它的自然率真,它的俚俗親和,它的沒有距離感,實(shí)現(xiàn)了與原生態(tài)歌唱的對(duì)接。廣義的游戲感和狹義的游戲感是原生態(tài)音樂與流行音樂遙相呼應(yīng)的紐帶。《刀郎木卡姆》中那手鼓敲擊的強(qiáng)烈個(gè)性化的節(jié)奏不正是對(duì)映著流行音樂中架子鼓震撼人心的節(jié)奏嗎?原生態(tài)演唱中的載歌載舞的形式不正是在流行音樂表演中的大幅度舞動(dòng),無拘無束的歌舞中頻頻“顯靈”嗎?自由想象的馳騁,自由心境的放飛,創(chuàng)造力的勃發(fā),自娛自樂的游戲精神彌漫于原生態(tài)及流行音樂的音樂表演中。
相比之下,兩極之中的西方美聲唱法及中國(guó)當(dāng)代民族唱法(“青歌賽”上有人稱之為“學(xué)院派民族唱法”)在音樂表演上游戲因素的缺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絲毫沒有貶低美聲唱法、當(dāng)代民族唱法的意圖。傳統(tǒng)的美聲唱法及當(dāng)代民族唱法毫無疑問是一種美的結(jié)晶。否則,傳統(tǒng)美聲唱法不會(huì)延續(xù)幾百年,為世界上許多國(guó)家的演唱者所接受,所傳承。同樣,當(dāng)代中國(guó)民族唱法倘若沒有生命力也不會(huì)有那么多傳承者。它有一批有成就的,為廣大聽眾所喜愛的歌唱家,積累了一批為歌唱家及聽眾喜愛的曲目,已經(jīng)成為我國(guó)當(dāng)代民族唱法的主流唱法(至少在目前是這樣)。這兩種唱法在長(zhǎng)期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比較科學(xué)的,能夠系統(tǒng)地進(jìn)行教學(xué)的,有文本積累的聲樂藝術(shù)。他們的任何一次演唱,都意味著演唱者有數(shù)年、數(shù)十年的美的聲樂訓(xùn)練基礎(chǔ)。你一旦聽到這種歌聲,就會(huì)清醒地意識(shí)到——留給你的位置是在一定距離外的靜靜欣賞。我們也會(huì)看到一些美聲及民族唱法的歌手端著架子,繃緊臉面,在功利及技術(shù)壓力下的非自主、非自在的音樂表演。在這樣的音樂表演中藝術(shù)的游戲因素則蕩然無存,這是必須引起我們注意的音樂表演狀況。
我們褒揚(yáng)音樂表演的游戲因素及游戲性,并不說明我們贊同藝術(shù)起源于游戲的觀點(diǎn)。游戲只是藝術(shù)發(fā)生的動(dòng)力之一,藝術(shù)發(fā)生的根本動(dòng)力是人類的勞動(dòng)生產(chǎn)實(shí)踐。藝術(shù)發(fā)生的動(dòng)力是復(fù)雜的,不是單一的,勞動(dòng)、情感、巫術(shù)、想象、游戲、模仿等等原始社會(huì)的一切,他們互相聯(lián)系,互相制約,構(gòu)成了一個(gè)系統(tǒng),組成一個(gè)合力,推動(dòng)著藝術(shù)的發(fā)展。
三、游戲因素與音樂表演的關(guān)系
游戲既有廣義的概念,也有狹義的概念。這就是具體的游戲。關(guān)于游戲,《辭海》的釋義是:“體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娛樂的一種。有發(fā)展智力的游戲和發(fā)展體力的游戲兩類。前者包括文字游戲、圖畫游戲、數(shù)字游戲等,習(xí)稱‘智力游戲’;后者包括活動(dòng)性游戲(如‘捉迷藏’、搬運(yùn)接力等)和競(jìng)賽性游戲(如足球、籃球、乒乓球等)。”[3]這種游戲是人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通過這種游戲使人們得到休息,得到快感,得到愉悅。因而,音樂表演中的游戲因素往往使音樂在美學(xué)形態(tài)上呈現(xiàn)一種諧謔之美。諧者,詼諧;謔者,戲謔也。它是一種愉快的風(fēng)格,一種輕松活潑的意趣,也是美學(xué)范疇的喜劇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音樂自身(器樂、聲樂)在對(duì)喜劇的體現(xiàn)中有一定的可能性。適用于音樂的喜劇的范圍異常廣泛:從無憂無慮的、疏忽大意的、善良的幽默到狂放的嬉戲(如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xié)奏曲》和貝多芬《第七交響曲》末樂章);以兒童的惡作劇到怪誕離奇、辛辣諷刺等;從機(jī)智幽默、樂觀戲謔的木偶片《阿凡提》的主題歌到焦躁、宣泄的通俗歌曲《別擠了》;從調(diào)皮、嘲諷的《愛挑剔的大姑娘》到嘲弄、輕蔑,辛辣諷刺的《跳蚤之歌》,都說明了諧謔之美在聲樂領(lǐng)域中得到了獨(dú)特的體現(xiàn)。在我國(guó)浩如煙海的各民族民歌的海洋中躍動(dòng)著具有諧謔之美的浪花。如《回娘家》、《龍船調(diào)》、《阿拉木罕》、《大坂城的姑娘》等;表演唱中的《逛新城》、《歌唱光榮的八大員》、《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吉祥三寶》等;舞蹈音樂《洗衣歌》等等。
游戲中十分注重游戲規(guī)則,沒有規(guī)則就不成為游戲,不遵守游戲規(guī)則,游戲的愉悅感就喪失殆盡。音樂在結(jié)構(gòu)內(nèi)部也有嚴(yán)密的規(guī)則,在音樂表演上同樣有需要共同遵守的規(guī)則。所謂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在以相應(yīng)規(guī)則為前提的游戲活動(dòng)中,技術(shù)的運(yùn)用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作為游戲主要形式的各種球類運(yùn)動(dòng)和下棋等活動(dòng),能給我們樂趣的原因所在。音樂藝術(shù)是講究技術(shù)的藝術(shù),技術(shù)成熟與否,技術(shù)運(yùn)用的合理與否,技術(shù)與藝術(shù)表達(dá)的融合與否決定著音樂表演藝術(shù)的成敗。在音樂中要體現(xiàn)游戲因素,取得戲劇性效果也有相應(yīng)的技術(shù)手段,如故意破壞音樂發(fā)展的習(xí)慣邏輯,破壞聽眾感知的既定慣性,節(jié)奏上、力度上、音調(diào)上的夸大,糾纏不休的反復(fù),“粗野的”對(duì)比與夸張的模仿等等,從而營(yíng)造喜劇性的效果,體現(xiàn)音樂表演的諧謔之美。
我們強(qiáng)調(diào)了音樂表演的游戲因素、游戲感,強(qiáng)調(diào)了游戲與藝術(shù)的深刻聯(lián)系,但這并不說明音樂藝術(shù)、文學(xué)藝術(shù)等同于游戲。
藝術(shù)與游戲是一種雙向互利的關(guān)系。藝術(shù)盡管具有某些游戲因素,但根本上并非純粹的游戲。倘若游戲就是藝術(shù),那么,“為什么早期人類除了游戲活動(dòng)之外又從中進(jìn)一步衍生出藝術(shù)行為,并且使之隨著文明的發(fā)展而不斷獲得進(jìn)步?”[4]同重在消遣休閑的游戲相比,藝術(shù)蘊(yùn)含更多的精神內(nèi)涵。與游戲活動(dòng)中注重當(dāng)下的歡樂時(shí)刻不同,一切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意識(shí)享受都伴隨著心靈內(nèi)在地提高的狀態(tài)。“如果我們把藝術(shù)與游戲的相似當(dāng)作等同,將兩者一視同仁,那就會(huì)遮蔽藝術(shù)精神的實(shí)質(zhì)。‘當(dāng)孜孜不倦地游戲時(shí),便退化為它誕生之初的那種平凡狀態(tài)。’”“游戲?qū)τ谒囆g(shù)的意義其實(shí)是搭建一個(gè)精神的平臺(tái),以便讓人們以輕松的方式‘在無阻礙的游戲領(lǐng)域里認(rèn)識(shí)自己。’諸如下棋、打球、躲貓貓、猜字謎,以及開碰碰車、坐過山車等游戲活動(dòng),這是我們世俗旅途上不可缺少的無數(shù)客棧,而藝術(shù)則是我們最后也是唯一的精神家園。”[5]
游戲是“避重就輕”;藝術(shù)是“舉重若輕”。藝術(shù)中具有游戲性,又有對(duì)游戲性的拒絕。明白這個(gè)道理我們就能辯證地把握音樂表演中游戲性的“度”。我們既要在音樂表演實(shí)踐中借鑒游戲手法滲透進(jìn)某些游戲因素,又不能使藝術(shù)的精神內(nèi)涵喪失于游戲的迷宮中。使音樂表演藝術(shù)健康地、健全地發(fā)展。
我們論述音樂表演中的游戲因素,游戲性,是要人們關(guān)注在音樂表演中借鑒某些游戲手法滲透進(jìn)游戲因素,使我們的音樂表演更具想象的自由翱翔,心境的自由放飛,創(chuàng)造力的勃勃生氣,生命力的展示與釋放。更多地汲取原生態(tài)音樂的生命活力,率真質(zhì)樸,使我們的民族聲樂事業(yè)在固有的大河中,以多樣化的姿態(tài)滾滾向前;使我們的美聲唱法,在共享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的基礎(chǔ)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使我們的流行唱法,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原生態(tài)音樂對(duì)接,從而在總體上體現(xiàn)中華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藝術(shù)精神、文化內(nèi)涵、詩性品質(zhì),及技術(shù)含量,為人類的精神文明作出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
[1]加塞爾.什么是哲學(xué)[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4:67-68.
[2]美學(xué)小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272.
[3]辭海(縮印本1989年版)[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1099.
[4]徐岱.藝術(shù)新概念——消費(fèi)時(shí)代的人文關(guān)懷[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6:101.
[5]徐岱.藝術(shù)新概念——消費(fèi)時(shí)代的人文關(guān)懷[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6:102-103.
J604.6
A
肖金勇(1980—),男,漢族,甘肅隴南人,本科,講師,廣東嘉應(yīng)學(xué)院音樂與舞蹈學(xué)院,研究方向:聲樂教學(xué)、聲樂表演和藝術(shù)實(shí)踐教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