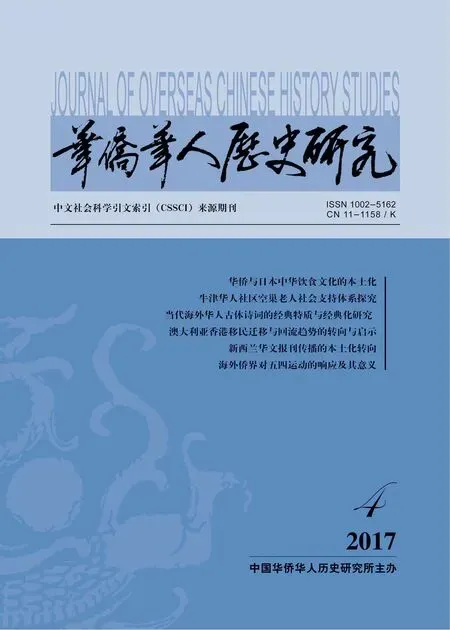批信局研究新探—從政商關系視角的考察*
周瑜斌
(上海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39)
批信局研究新探—從政商關系視角的考察*
周瑜斌
(上海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39)
國民政府;僑批;批信局;僑務工作;僑務委員會;政商關系
論文剖析了批信局與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的關系,認為國民政府的僑務活動是功利導向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華僑的經濟力量。批信局聯系起了僑匯、僑民和僑眷,而僑匯才是政府關注的重點。僑民和僑眷的地位與僑匯相關。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雖因僑相連,卻因利而相關。批信局與郵政產生矛盾時,僑務委員會以保僑的名義介入,但其行動卻以保匯為主要目的。名實不符使得僑務委員會不能為批信局提供穩定的保障。抗戰爆發之后,重慶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因爭取華僑經濟力量而使得批信局與之關系密切,但汪偽政府僑務機構的壓迫卻讓批信局經歷了發展過程中的最低潮。從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政商關系考察政僑關系,可知民國政府的僑務政策是功利導向的。華僑尤其是中下層華僑及其背后的僑眷,背負著不可承受之重。A
批信,又稱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海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的匯款暨家書,是一種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在2013年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后,僑批檔案引發世界關注。批信局是閩粵地區為僑民服務的商業機構,以寄送僑民的信件和僑匯為業。批信局專注僑民匯款,是連結華僑與僑眷的主要渠道。批信業本身也是僑商投資的重點行業之一。[1]僑務委員會是民國時期負責僑務工作的中央部級機構。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關系既涉及政僑關系,也涉及政商關系。從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關系的角度來分析政府的僑務活動,可以深入挖掘僑務活動背后的經濟動因,揭示民國時期政府僑務活動背后的執政邏輯。
從批信局角度研究華僑史的成果有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文化領域,經濟和政治方面雖有涉及,但成果較少。杜桂芳分析僑批的產生和源流及其與潮汕地區家族觀念的關系;[2]吳潤填、何敏波、杜式敏則以僑批檔案為對象,分別研究潮汕地區的家族觀和義務觀、商業觀念、女性觀念。[3]肖文評、鄧銳考察了華僑與廣東客家文化之間的關系。[4]陳麗園則通過僑批研究跨國華人的教育與文化傳承,其另一篇文章則以取締批信局這一政治事件入手分析海外華僑社會的構建。[5]對僑務委員會的研究側重于政治方面,主要關注政府通過其發動華僑支持國內建設和抗戰,其中涉及到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以實現政治目的的一些內容。陳國威認為,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十分重視華僑的經濟力量,但僑務委員會因為種種原因自身發展不佳,未能完全實現政府的目標。[6]任貴祥和冀滿紅、趙金文都認為,僑務委員會在抗戰時期積極動員華僑的經濟力量支援國內抗戰,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7]
通過對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關系的深入挖掘,本文認為,民國時期政府的僑務活動是功利導向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華僑的經濟力量。批信局聯系起了僑匯、僑民和僑眷,而僑匯才是政府關注的重點。僑民和僑眷的地位與僑匯相關。僑務委員會的《組織法》中明文規定,以保育華僑為主要職責。這不僅僅是僑務委員會的設立原則,也是國民政府對華僑的承諾。但是,在面對華僑的吁求時,僑務委員會的表現并不稱職。抗戰時期,為鼓勵華僑支持抗戰,國民政府向華僑和僑眷宣傳保匯即救國的思想,希望爭取華僑的經濟支持,因而這時期的僑務政策呈現出功利化的傾向。
一、批信局、僑務委員會與郵政:三方關系的形成
批信局內涵的界定是一個基本問題。批信局這一概念是在1929年郵政準備取締民信局時才提出來的。現在絕大部分研究者都將閩粵地區在19世紀中后期產生的、以經營南洋華僑信件和小額匯款為主的民間通訊機構稱之為批信局,實際上是為了研究方便,從而將這一概念擴展至其前身。當地按習慣對其有多種稱呼,例如批館、信局、銀信局、信莊、僑批局等。根據批信局的從業者自述,批局、批信局等名稱都是由郵政提出來的。[8]這一概念形成于1929年,之前的所謂批信局與其他地區的民信局并無本質不同,僅僅是客戶群體的差別導致了業務重心的差別。①上海地區的民信局也收發批信和僑匯,閩粵地區的批信局也收發平信。這就證明了兩者之間沒有業務區隔,從而也就間接證明了兩者的同一性。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放棄取締這些批信局,并不是因為這些批信局在性質上有什么特殊之處,主要原因在于華僑的大力爭取和郵政難以取代其功能。批信局業務的專門化由市場發展導致,但卻是政府行政命令使得批信局徹底從民信局中分離出來。其業務徹底專業化之后,這些批信局才與現代學者所認定的批信局概念相符。當然,從研究的便利性角度考慮,將其擴展至前身并無不可。本文也沿用了學術界一貫的界定方法。
僑務委員會成立于1926年,起先隸屬于國民政府,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僑務委員會組織法》,[9]將其歸由行政院管理。根據該法,僑務委員會負責管理中華民國僑民之保育事務。在行政級別上是與交通部平級的部級機構,高于郵政總局。批信局因與華僑關系密切,從而與僑務委員會產生聯系,但這一關系較為松散。抗戰時期,汪偽政府另組僑務委員會,與重慶政府的僑務委員會并立,且積極干預批信局事務,意圖控制僑匯,并利用批信局拉攏華僑與僑眷。
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關系之所以復雜,原因在于有一個重要的第三方—郵政。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關系根據是否與郵政相關,可以分為三方關系和雙方關系。郵政自晚清時期就已經成為批信局的監管者。從業務關聯上講,郵政與批信局的關系更為密切。但是兩者存在著一定的業務競爭關系,所以經常發生郵政利用行政特權對批信局進行打壓的事件。僑務委員會以保育僑民為主要工作責任,因此成為批信局在與郵政發生沖突之后主要的乞援對象。在現存的各種檔案文獻中,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有相當數量的往來是因為郵政而引起的。由于郵政總局的級別相對較低,僑務委員會在接到批信局的呈報之后會向同級別的交通部致函,因此在三方關系中包括了四個主體。批信局為一方,僑務委員會為一方,郵政和交通部為一方。雙方關系下的兩者關系體現為僑務委員會對批信局的直接管理。在海外設立的批信局,以華商企業和華僑商會成員的身份受僑務委員會的監管。抗戰時期,重慶政府以僑務機構為工具,爭取華僑的經濟力量。批信局作為僑匯的主要流通渠道,也因此與僑務委員會關系密切起來。
二、抗戰前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之關系
抗戰以前,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關系繞不開郵政。在三方層面下,僑務委員會與郵政的監管目的卻存在著嚴重的沖突。僑務委員會對批信局的監管目的在于保障其正常經營以促進僑匯流回國內,郵政的監管目的則在于限制乃至最終取締批信局。批信局既可以利用這種沖突為自身謀利,又可能會因這種沖突而陷于困境。批信局利用各類華僑團體和華僑領袖向僑務委員會申訴以爭取支持,可以迫使郵政作出一定的讓步從而維護自身利益。但批信局在僑務委員會與郵政爭奪監管權波及自身經營時,則受困于這一沖突難以解脫。
(一 )批信局受益于監管沖突
批信局與政府的關系因為雙重監管的緣故比一般企業更為復雜。在常規監管關系中,郵政是第一監管者,僑務委員會是第二監管者。這種格局限制了僑務委員會的監管作用。此外,僑務委員會的關照主要是為了利益而非情感,對批信局的保護甚為有限。除了保障生存這一最基本的需求之外,僑務委員會也只會根據個別事例依情況提供相應的幫助,但制度化的行政扶持始終未能構建。
1.總包制度存廢的博弈
總包制度是郵政為民信局量身定做的一套制度。根據1899年頒布的《大清郵政民局章程》,總包制度包括了三個方面:基本內容、寄遞資費、寄遞之法。基本內容包括以下四點:一是已注冊民信局不得直接利用火車、輪船代寄信件,必須將信件打包成總包,由郵局代轉;二是未注冊民信局無權遞交總包;三是郵政只將總包轉交給已注冊民信局,收轉方如果為未注冊民信局,按正常資費收費;四是收轉方民信局必須自行前往郵局領取。在資費方面,將最初設立的按重量繳費的規則,改為按件計費,且為國內信函減半收費,國外信函正常收費。郵政在處理總包的時候,參照包裹的相關規定執行。[10]總包制度在清政府覆亡之后,依然被長期沿用。批信局作為民信局的一支,也遵循此例。
總包是批信局在海外活動的制度基礎。海外郵政機構參照大清郵政的總包規定管理批信局海外分支機構的相應活動。因此,如果中國郵政機構取消總包,則批信局在海外也就無法營業。故而兩者關于總包的矛盾絕非單純的利益之爭,乃是關乎批信局存亡的大事。對此,無論是批信局自身,還是華僑社團與華僑領袖,均知其利害,因而在這一點上據理力爭、毫不退讓。僑務委員會明白其中意義,更深知批信局對于僑匯回流的作用。因此,其與交通部公文往來頻繁,在這類事務的處理上可謂盡心盡力。
在僑委員會成立之前,郵政與批信局圍繞總包制度就已經爆發了多次沖突。沖突的焦點包括資費、執行細則和制度存廢等,其中以制度存廢最為關鍵。因為沒有專職的僑務機構,批信局一般利用僑團組織出面協調。①在僑務委員會成立以前,民國時期北京政府也設立過一些華僑管理機構,但大多流于形式未能真正開展工作。1912年,郵政總局向南洋地區的殖民地政府發出照會,決定取消南洋地區民信局的總包制度,改為按件收費。僑民起初以為是殖民地政府的動議,最終卻發現是中國政府不體恤僑民,單方面提出廢除總包制度。批信局通過南洋地區的商會組織聯合北京的潮州會館向北洋政府陳情,才使得郵政收回成命。[11]總包制度是批信局海外分支機構經營的政策基礎,因此批信局高度維護總包制度。大約在1923年,②此處所依據的資料系追記而成,作者亦未能確認具體時間。加之目前尚未找到其他相關材料,所以不能確定具體時間。郵政總局向南洋殖民地政府照會,準備取消總包制度,華僑批信按普通信件繳納資費。[12]為推卸責任郵政還向僑民謊稱該動議由殖民地政府提出,但之后被殖民地政府揭穿謊言。批信局通過南洋華僑團體居中調解,最后以總包費用上漲了結此事。過了一兩年之后,郵政總局故伎重演,批信局借助華僑團體的努力得以保留總包制度,但是其費用與普通信件相比已無優惠。
僑務委員會成立之后,批信局通過僑民和華僑團體利用其轉交致交通部的呈文。僑務委員會得以以第二監管者的身份,從中協調批信局與郵政的關于總包的矛盾。1928年10月,南洋地區的殖民政府決定取消總包制度。廈門地區批信局向交通部和僑務委員會請求交涉,為華僑爭取利益。在交通部回復給僑務委員會的公函中,先指責批信局污蔑,“近年以來民信局走私信件日多一日,郵政收入大受影響。去年七月起奉令用嚴厲辦法取締此項走私信件,一面按章從嚴科罰,一面懸賞激勵。查緝其風稍遏,廈局收入亦增。該民局等因不正當之利源被塞,不遂其私,故用捏辭控吿,憑空虛構毫無事實可指等語”,又將責任完全推給外國郵政,“和(荷)屬東印第斯來函以該地國內法律不容許有信包(即總包)之辦法,業經職局呈奉鈞部指令第1130號準予停止”,并想借此機會徹底取締總包,“交換信包辦法本不合于國際郵政公約之規定,則各國如相繼要求取此項辦法,我國殊無拒絕理由”。[13]郵政意欲通過這一方式限制信局發展并進而將其取締。到了12月,交通部才決定派人前往汕頭、廈門兩地協商此事。[14]但派往汕頭地區的特派員與當地批信局的關系十分惡劣,以致于難以開展工作,不得不在第二年3月更換特派員。[15]就在幾天之后,新加坡殖民政府告知華僑,取締總包是應中國政府的要求。這讓交通部大為尷尬,不得不向國民政府辯解,“坡督及郵政總監謂此次發端實自中國政府來函要求取締等語,按此次取締民局系英屬郵政于去年八月起迭次函電要求,報載各節核與事實不符”。[16]此事令華僑十分憤怒,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種損害華僑利益的事,居然是祖國政府提出來的。華僑指責政府“欺侮華僑,瞞騙國人”。[17]這就使得交通部準備在汕頭、廈門兩地改組批信局(實質是為了徹底控制批信局)的計劃遭受了極大的外部壓力,最終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交通部向汕頭、廈門兩地派出特派員負責協調處理此事。[18]到了4月份,交通部向僑務委員會通報,將繼續就南洋總包問題與外方進行協商。[19]及至6月份,交通部決定維持原有的總包制度不變,且批信局可以長期營業、不被取締。[20]回顧整個過程,批信局本身與郵政并無多少直接交涉,但通過僑務委員會的轉呈,對于事情最終朝有利于批信局方向的解決,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基層郵政與批信局的總包糾紛也需要僑務委員會的協調。1933年,廈門信業公會向福建郵政管理局申訴廈門郵局不允許建美信局及其分號收發南洋寄來的總包,引發行業震動。郵政則以專營權反駁,并指出批信局雖然被允許繼續營業,但經營上必須受到限制。批信局不得不通過新加坡總商會向僑務委員會進呈。總商會在呈文中首先批評郵政未能提供優質服務,只有批信局能為僑民和僑眷提供貼心的服務。然后指出郵政的規定不合理,設置在南洋的批信局作為外國企業,不應受中國郵政的管轄。最后痛陳利弊,聲稱其對僑眷的生活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新加坡總商會因此呈請僑務委員會幫助取消禁令。僑務委員會將呈文轉發給交通部,并向新加坡總商會表示會催請辦理。但在咨文中未表示嚴重關切,僅作程式化處置。廈門華僑同業公會主席楊顯甫后又以個人身份向僑務委員會致電,再次申訴新規的不合理之處。交通部僅回復僑務委員會,“令郵政總局,轉飭查明分別具報各在案”。[21]此事在檔案中再無下文,但之后批信局繼續營業,可知事件以政府常見的和稀泥方式結束。大體是批信局認罰,但郵政繼續維持總包制度。
在僑務委員會積極介入之前,批信局難以保障其自身利益。由此可見,僑務委員會的協調并非出于保僑,而是保匯。當郵政的苛政并未嚴重影響外匯流入時,僑務委員會的反應是消極的。
2.一般權益的申訴
郵政對批信局的非法限制有兩類:一類是苛限,批信局本身無過,卻被郵政刁難,讓其難以經營;另一類是苛罰,批信局本身有過,但郵政借題發揮,意在迫使相關批信局停止營業。批信局利用僑務委員會申訴后,一般可以得到相對公正的處理。但是一事一議,批信局始終缺乏制度化的保護,主要原因在于僑務委員會缺乏這種意愿。背后反映的是僑務委員會行政的重點在于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對于保護中下層僑民的利益則不那么熱心。對于批信局而言,請僑務委員會出面的成本也不低,因此只在不得已的時候才乞援。對于非嚴重事件則只能自行忍受。
地方郵局在注冊方面刁難信局,有時也需要僑務委員會出面調解。1932年初,廣東澄海的鄭成順利振記信局通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和暹羅中華總商會請求僑務委員會向交通部致函,希望“移設分局于汕頭”,懇請“郵政總局準予掛號領照”,[22]交通部表示“尚可準予掛號領照”。[23]這本是基層郵局就可以處理的事務,卻興師動眾,原因不言自明。
除注冊以外,加強信件檢查的力度是另一種限制。1934年3月,“汕頭郵局,以香港地方,不在批信局營業范圍之內,該處經營國外批信者,不得收寄香港批信,倘有收寄情事,即以走私處罰”。旅港潮州八邑商會為批信局求情,“查僑批營業地方,向來并無范圍,近亦未聞郵政總局有何規定公布”,因此“特懇俯順輿情,將該案取銷”。[24]而僑務委員會也因此案向交通部咨文乞寬,“據香港嶺東華僑互助社,呈請轉咨交通部,令郵政總局轉令汕頭郵政局,撤銷取締香港批信,以保僑益,而恤民生”。郵政總局認為汕頭郵局并無過錯,“查批信局寄往香港批信,向系封作總包,按照總包重量,繳納郵費。惟近來常有利用香港郵政,收費較低,將寄往國外他處之批信,封入包封內,送由香港寄遞,以圖省費,故曾令飭廣東管埋局予以取締”。但還是做出了一些讓步,“民信局結束之后,批信局業呈準暫行繼續營業,該汕頭經營香港批信局,自亦可暫行準予繼續營業,惟擬飭其將收寄往香港之批信,一律按照寄費淸單第八資(每封重二十公分收費五分)逐封繳納郵費后,仍準封作總包寄遞,不得攙入寄往國外他處之批信,所有郵票,粘貼總包封面,與寄往南洋羣島馬來聯郵等處之批信,同樣.辦理,以防發生弊端”。[25]從此案來看,該批信局雖然未能免于處罰,但是爭取到了繼續經營的許可,僑務委員會居中協調依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根據郵政的分業規定,批信局不得兼營平信的寄遞。1934年7月,汕頭地區一家批信局私寄平信,新加坡潮僑匯兌公會和汕頭市僑批業公會通過僑務委員會致函交通部陳情,“汕郵局檢查各民信局,于代送華僑之家屬民信中,發現有附帶兩封之函件,處罰信局,且宣布罰及三次,當即取消營業執照”,所以“據情懇轉請交通部,迅令汕頭市郵局從寬辦埋”。[26]新加坡總商會也因此呈文,請求從寬處理。郵政總局回應,“國外寄來郵件,查有夾帶情弊,現均從寬照欠資郵件處罰,至批信局因收夾帶之間而被取消執照者,則并未執行”。雖與批信局的說法完全不同,但這一說法也表明郵政降低了違規批信局的處理。交通部表示,“(郵政總局)辦理已屬格外從寬”。[27]相比較而言,批信局的陳述更為可信。若非執照被吊銷,其必然不會大費周章地申訴。僑務委員會的介入讓郵政依法行政,批信局因此得到了相對公正的處理。
(二 )批信局受困于監管沖突
批信局在僑務委員會下屬汕頭僑務局與郵政爭奪監管權的時候,因居于其中受了不少池魚之禍。汪偽時期,由僑務委員會管理批信局。抗戰勝利后,汕頭僑務局有心沿襲這一舊例,但與僑務委員會意見不一,未得其支持。一些批信局在抗戰勝利后要重新開業,便沿襲汪偽政府的管理習慣,向汕頭僑務局申請經營執照。該局隨后將其轉呈給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卻回復此事“應呈請地方機構處理”,然而,僑務局并不甘心放棄權力,在隨后對批信局的答復中,刻意隱匿僑務委員會的真實指令,謊稱“業經轉呈核辦在案”。[28]除了注冊之外,汕頭市僑務局要求汕頭僑批業公會,將組織章程、職員名單、會員名冊、業務狀況據實上報。汕頭市僑務局還自行制定了《批信事務處理辦法》。[29]由此可以看出,僑務委員會認為,監管體制應該恢復到戰前;汕頭僑務局則認為,應當延續汪偽時期的監管制度。對此,僑務局以“此間僑批業因未登記,央行不予收購匯票”答復。批信局因為爭權而不能復業,也因此連累了許多華僑與僑眷。而僑務委員會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依然表示此事交由汕頭市政府處理。[30]數月之后,僑務委員會再次訓令汕頭僑務局,明確指出“僑批商執照由當地郵政局核發”。[31]
僑務局之所以極力爭權,目的就在于爭取利益而非保護華僑。1947年5月,汕頭市僑務局再次向僑務委員會呈文,先說明僑匯與中國經濟有莫大關系,接著表示僑批又影響僑眷,“若一僑批商辦理不善,職局有未據法而糾正,則影響僑眷生活,實匪淺鮮”,最后言辭激烈地指出:“(毋庸訂定辦法)未免與護僑之旨相刺謬,且此為財、交兩部又已同意在先,似應請把握時機,早日核定管理辦法俾而管理,而利僑匯”。僑務委員會再次回復,“毋庸訂定辦法”,但“如僑批局收寄僑款延不交付可報告僑務局代為查問”。[32]僑務委員會之所以反對,皆因爭取監管批信局主要得利者在基層僑務局,但卻會因此讓其與交通部、郵政總局發生沖突。僑務局爭權是為圖利,僑務委員會放權則是因為利不及自身。
監管權的爭奪歷時近半年,對批信局的正常經營構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批信局在面對僑務局和郵政時無所適從,難以正確處理相互關系,平白遭受了池魚之禍。
三、抗戰時期:保匯即救國
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之間在和平時期聯系并不緊密,但在戰爭時期卻因為特殊原因而形成了密切的關系。批信局作為一種商業機構,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必須要與僑務委員會進行聯系的時刻并不多見。按《僑務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在海外設立的華僑團體組織必須向當地國民黨黨部注冊,沒有黨部的可以向僑務委員會注冊,接受兩者的指導。批信局在海外的分支機構一般都會加入當地的華僑商會組織,批信局在較為集中的地方如新加坡會組織同業公會。通過這些組織,批信局受到僑務委員會的間接監管。但這種關系較為松散。僑務委員會本身并非專職的經濟管理機構,司局設置中也無經濟類的分支機構。但在向行政院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卻大量的出現僑資、僑匯的內容。[33]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高度重視華僑的經濟力量,僑匯更是重中之重。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關系變得突然密切起來。
(一 )國民政府努力爭取僑匯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下屬的各僑務局或內遷、或撤銷。[34]而廈門與汕頭分別在1938年和1939年淪陷。自此開始,兩大批信業核心城市均被汪偽政府控制。汪偽政府在淪陷區另組僑務系統。[35]重慶政府對于淪陷區的批信局不能監管,又不能將僑匯拱手讓給日本人和汪偽政府,于是利用僑務系統向華僑和僑眷宣傳保匯即是救國的思想,希望以宣傳戰的形式開展反制。這既是為了給抗戰提供經濟支持,也是為了阻止日本利用僑匯侵華。而日本軍部和汪偽政府垂涎批信局掌控的大量僑匯,意欲全部侵吞。事實上,國民政府在開展宣傳戰、經濟戰時,過程十分艱辛。廈門的批信局在淪陷后普遍停業;汕頭的批信局雖然勉強開業,不少批信局卻被汪偽控制。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南京國民政府開始有意識地鼓勵華僑支持抗戰,而華僑的經濟力量最受重視。1938年,經濟學家黃元彬為南京國民政府擬定了《華僑匯款總動員運動意見》,明確指出僑匯不足會讓整個金融予以動搖,主張利用華僑團體和鄉鎮自治團體敦促僑民利用官方途徑向國內匯款。[36]由于官定匯率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因此只能寄希望于華僑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并利用傳統的宗族關系促成這一點。這是當年12月,僑務委員會向中國駐南洋各地大使館致電,針對日本蠱惑華僑的主要內容逐條予以批駁并請使館宣傳。其中第二條專門批駁日本所謂的“予通信匯兌之便利”承諾。先是向華僑表明:“各省匯款,亦非毫無辦法,又何須倚賴倭寇”,再強調保匯即是救國,如果僑匯“誤入敵人銀行”,則“以有用之金錢,資助敵人,侵略祖國,自困家鄉”。[37]汪偽政府成立之后,重慶政府針對汪偽政府開展了宣傳戰,希望以此挽回僑匯。1940年5月,僑務委員會向福建省政府密電,告知“經敵誘騙,多數僑胞已經墜入其彀中”,要求其“設法挽回,俾免被敵人利用”,并“迅飭地方銀行聯合民信局,推廣暹羅僑匯,以資救濟”。1941年,汪偽政府僑務委員會頒布《華僑捐款獎勵辦法》,意圖收編華僑的經濟力量。福建省政府因此要求下級政府,“加緊對華僑宣傳并設法予以摧毀”。[38]但重慶國民政府由于失去了對汕頭和廈門兩地的控制,僑匯的攬收并不順利。不過在國民政府和汕頭部分批信局的努力下,抗戰后期(1942年)開辟了東興僑路,①從廣西東興入境,故而得名。具體路線為從越南至廣西,再經廣東北部繞回汕頭地區。經營這一線路的批信局不在汪偽控制之下,其僑匯由國民政府管理。僑匯攬收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 )汪偽政府對僑匯的侵奪
汪偽政府利用統治之便,有意識、有步驟地侵占僑匯,為日本侵華服務,批信局則成為了主要目標。汪偽政府的僑務機構在確立監管權之后,對批信局進行嚴苛管制和盤剝,并利用其進行思想宣傳,對批信局的“違法行為”嚴厲處罰,通過這些措施以實現侵占僑匯的目的。批信局經營因此陷入困頓,大量華僑和僑眷為此蒙受苦難。
1942年,汪偽政府決定將批信局的監管權從郵政轉移至僑務委員會。同年,汪偽政府僑務委員會駐汕頭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甫一成立就頒布訓令,聲稱“本處值司僑務,凡與僑民有關團體,自應縝密考核,以定興革之方而收指臂之效”。其認為汕頭市僑批業同業公會“與僑民關系極(密)切”,要求僑批公會“將組織章程,職員、會員名籍、冊及會務概況等……呈繳來處,以憑核飭”。[39]同年8月,辦事處又召開座談會,除了將汕頭地區批信業的主要代表召集起來之外,日本軍部代表、汕頭市縣兩級政府首長一并到會。在這次會議中,日本軍部代表明確了辦事處的監管權,“僑批業屬于僑務委員駐汕辦事處直接監督下之團體,故辦事處得行使其職權,對批業要時加監督”。[40]
該年10月份,辦事處開始制定具體的僑批業管理規則,開始對批信局進行嚴酷管制。與過去相比,增加了很多限制措施。具體有五項:一是領取批信的申報制度,“各商號在僑批寄抵汕頭市時,應向本處填具申報書,以憑核發領取批信證,憑證向郵政局領取批信”;二是批信總包的檢查制度,“各商號領取批信后,務將批信原包呈送本處核查,驗蓋后由各商號領回發送,其屬非一和平區批信,則概行扣留,不予領回”;三是批腳的通行證制度。批腳需要辦理通行證才可以派送批信,但通行證的審核嚴格而有效期短(六個月);四是發送批信的區域限制,“各商號批腳不得前赴非和平區”;五是臺灣銀行壟斷僑匯的結算。早在抗戰爆發前,臺灣銀行就派遣專人調查南洋華僑的僑匯情況,認為“移居南洋的中國人三百五十萬,在南洋發跡到處可見,特別是經濟上之勢力遠超原住民”,并設想了業務開展的要點,“值我銀行(臺灣銀行)向南洋一帶擴展業務時,所到之處,皆為中國人商業勢力范圍,因此特別注意其影響力,百事以中國人為服務對象,業務才得發展”。[41]兩地淪陷后,臺灣銀行借機壟斷僑匯。在管制過程中,辦事處還巧立名目收取多項不合理費用。
批信局本身又是通訊機構,可以傳播信息。因此,日本軍部和汪偽政府為了控制輿論,就不能僅對批信局進行經濟監管。日本軍部和汪偽政府認為可以利用其來拉攏人心,不僅有利于控制中國國內的淪陷地區,也有助于控制南洋地區。日本軍部欺騙批信業者,“現在泰國馬來南洋多處,均與日本協力合作,即各地華僑,六年聯絡結合中,華僑一切行動,均甚協力日本軍,為獻金等舉,均其表現之乃實也”,并虛偽地承諾“對于潮汕地道僑眷,應加之保護”。實意卻是利用僑眷脅迫華僑與之合作。除此之外,辦事處還要求批信局參與宣傳,鼓動僑眷支持汪偽政府和日本侵略者,與重慶政府展開宣傳戰。“諸位營業,即以急于推進華僑家眷參加和平之責任,僑批雖屬營業性質,但辦理宣傳工作,亦甚有力,故爾等生意,固為要緊,而宣傳工作,亦系相當要緊,不比其他普通營業,此能誠意辦理宣傳工作,結果必使華僑受益,此即和平工作之偉大也”。[42]目前留存下來的一封當時的批信上蓋有辦事處的宣傳章,內容為“與日本合作,可以振興僑胞在南洋之勢力”,可以作為實例。[43]
辦事處對于違規批信局的處罰極為嚴酷。為了震懾批信局,辦事處在1943年8月26日焚毀了2047件從泰國寄來的“非和平區”①日本軍部和汪偽政府將自己控制的區域稱為“和平區”,否則就稱為“非和平區”。批信。[44]雖然表示“匯款由原批局照章退還原寄匯人”,但這一承諾并不可信。匯款的最終去向因為無資料記載,成為謎團。
嚴酷管制嚴重干擾了批信局的經營。批信局希望監管能夠稍加松弛,但被辦事處拒絕。批信局領取總包之后,不能直接發送,必須將總包送至僑務委員會辦事處檢查。檢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扣押“非和平區”的批信。否則一經發現,接收總包的批信局就要受到處分。這一不合理的規矩,讓很多批信局難以接受。[45]“僑務委員會駐汕辦事處拆包檢查處置嚴密,實絕無取巧之可能,不過華僑未明底蘊,一旦有弄巧反拙者,會員等因收受批包關系,勢又被政府之詰責,茲為防患于未然,減輕責任起見,特聯名投請公會提出聲明,嗣后會員等收受批包,惟遵照條例繳送檢查便為盡職,至于批包內容如何及檢查復后有何發現違反條例之批信,會員等處于收受人地位概不負其責任,庶免無辜受過”。[46]辦事處雖然部分認可,但并不愿放松監管。汕頭地區批信局的同業公會再次向辦事處呈文,認為條件過于苛刻,希望能略為放寬,不過其建議未被采納。
四、結語
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的關系表明,國民政府僑務政策的出發點在于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僑匯是華僑經濟力量的具體體現,也是近代中國外匯的主要來源,因此是最受政府重視的對象。僑務委員會關注批信局,主要是因為看中其經濟功能。僑務委員會介入批信局與郵政的矛盾,保匯的意圖實在保僑之上。地近則利近,故地方僑務局爭取僑匯的表現要比僑務委員會更直白和迫切。批信局雖然利用僑務委員會爭取了一些權益,但未能徹底改變與郵政的非正常關系,有時反而受害于監管沖突。促使批信局與僑務委員會在特殊時期關系密切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僑匯。為了支持抗戰,重慶國民政府的僑務機構對汪偽政府的僑務機構發動了各種宣傳戰、經濟戰。這雖然是必要的,卻又使得批信局無辜受禍。從研究角度而言,僑務政策的經濟動因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得更為明顯。
功利化僑務政策的形成既有歷史根源,也有現實根源。第一個歷史根源是華僑主動捐助的傳統。從晚清起,華僑就主動捐助國內的革命事業。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在早期發展階段受惠于華僑甚多。孫中山直言華僑是革命之母。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領導的十次武裝斗爭主要軍費均來自于華僑,比例在八成以上。[47]華僑捐助革命的熱情由此可見一斑。從這一時期起,海外華僑就形成了捐助國內的傳統。這種傳統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也是功利化僑務政策得以確立的主要外部因素。
華僑基于報國之心主動提供捐助形成傳統之后,卻被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視為理所當然之舉,將善舉等同于義務,進而苛求華僑。這是第二個歷史根源。對于華僑的愛國行為,政府在大多數時候只是提供一些榮譽性的虛銜作為回報,對于華僑真正關心之事物和切身利益,卻沒有足夠的關注。華僑的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政界人士對此并非沒有認識,但并沒有主動改革積弊的行動。1940年,時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雄在一次公開談話中就承認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存在缺陷,“過去政府未盡宣傳與聯絡之功,亦即過去政府未能深切了解華僑,保障華僑”。[48]主政者或不自覺,認為華僑熱心國內事業,不求回報;或自覺但不愿改變,因改革積弊本身對于官員和政府無利可圖。這是功利化僑務政策形成的主要內部因素。
南京國民政府的天然缺陷是現實根源所在。作為一個弱勢政府,其所能掌控的各種資源并不豐富。加之國內經濟不發達,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對華僑的經濟力量十分倚重。為了盡可能地發揮這種力量的價值,其自然會推行高度功利化的僑務政策。近代中國外貿長期逆差,僑匯對于彌補貿易赤字的作用甚大。1931—1940年間,僑匯占貿易赤字的比例大都在五成以上,是最主要的外貿入超平衡因素。[49]南京國民政府選擇功利化的僑務政策具有一定的現實性。
功利化僑務政策形成之后長期延續,雖然讓南京國民政府取得了一些短期收益,但是卻讓廣大華僑承擔了超過義務的責任。中下層華僑及其僑眷作為華僑的主體,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他們既要面對外國的歧視,又要面對本國的苛求,生活自然陷入困境。他們對于政府不體恤僑民,早就多有不滿。[50]功利化僑務政策的真正結束是在華僑經濟力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式微之際,而這本身也是功利主義的另一種體現。從經濟角度、企業角度來分析政僑關系,相比政治角度能夠更細致、深入地展現兩者關系的內涵。從這一視角開拓華僑史研究,除了擴展史料來源之外,也有助于對既有史料的二次挖掘。
[注釋]
[1] 黃美緣:《清末和民國時期華僑在廈門的投資》,《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 杜桂芳:《僑批—潮汕歷史文化的奇觀》,《東南亞研究》1995年第6期。
[3] 吳潤填:《僑批—潮汕文化底蘊的折射》,《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何敏波:《簡述僑批業發展過程中的潮商精神》,《八桂僑刊》2009年第1期;杜式敏:《從潮汕僑批看海外潮人的女性觀》,《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4] 肖文評:《粵東客家山村的水客、僑批與僑鄉社會—以民國時期大埔縣百侯村為個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鄧銳:《試論僑批對客家文化的影響》,《廣東檔案》2012年第1期。
[5] 陳麗園:《從僑批看跨國華人的教育與文化傳承》,《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4期;《近代跨國華人社會建構的事例分析—1929—1930年新加坡保留民信局與減輕民信郵費全僑大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袁丁、陳麗園:《1946—1949國民政府對僑批局的政策》,《南洋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 陳國威:《1932—1945年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論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年第4期。
[7] 任貴祥:《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工作述評》,《史學月刊》2016年第1期;冀滿紅、趙金文:《略論抗戰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東南亞研究》2014年第3期。
[8]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頁。
[9] 楊建成主編:《三十年代南洋華僑團體調查報告書》,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27~29頁。
[10] 仇潤喜編:《天津郵政史料》第1輯,北京航空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88~95頁。
[11] 《民信局史實略記》,《南洋中華匯業總會年刊》1947年總第1期,第12~14頁。
[12] 《民信局史實略記》,《南洋中華匯業總會年刊》1947年總第1期,第12~14頁。
[13] 《國民政府交通部公函:第七六五號(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交通公報》1928年總第35期,第2~3頁。
[14] 《交通部代電:第一二九號(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交通公報》1929年總第107期,第47~48頁。
[15] 《交通部指令:第九七三號(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六日)》,《交通公報》1930年總第131期,第13~14頁。
[16] 《交通部公函:第三○四號(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交通公報》1930年總第130期,第25~26頁。
[17] 《為取締民信局之呼吁》,《申報》,1930年4月10日第13版。
[18] 《交通部公函:第三一二號(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交通公報》1930年總第131期,第65~66頁。
[19] 《交通部公函:第三八四號(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四日)》,《交通公報》1930年總第134期,第50~51頁。
[20] 《僑信局仍照舊章辦理》,《申報》1930年7月13日。
[21] 《本會辦理廈門民信局糾紛經過之文件》,《華僑周報》1993年第41期,第36~39頁。
[22] 《交通部公函:第一三九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交通公報》1932年總第326期,第10頁。
[23] 《交通部公函:第三六六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交通公報》1932年總第345期,第20頁。
[24] 《交通部訓令:第一一六三號(二十三年三月八日)》,《交通公報》1934年總第542期,第2~3頁。
[25] 《交通部公函:第一零零七號(二十三年四月七日)》,《交通公報》1934年總第551期,第28~29頁。
[26] 《交通部公函:第二零五三號(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交通公報》1934年總第584期,第15頁。
[27] 《交通部批:第二九二四號(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一日)》,《交通公報》1934年總第594期,第34~35頁。
[28]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71~276頁。
[29]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86~288頁。
[30]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95頁。
[31]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79頁。
[32]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97~299頁。
[3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95~596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第617、619~620頁。
[34] 謝國富:《僑務委員會組織概況》,《民國檔案》1992年第4期。
[3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第690~692頁。
[36]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華僑檔案史料(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第412~414頁。
[3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四),第681頁。
[38]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華僑檔案史料(上)》,第414~417頁。
[39]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21頁。
[40]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44頁。
[41]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51~53頁。
[42]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43~44頁。
[43] 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文化局、汕頭市圖書館編:《潮汕地區僑批業資料》,汕頭:內部印刷資料,2004年,第106~107頁。
[44]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 第107頁。
[45]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86~87頁。
[46] 王煒中主編:《潮汕僑批業檔案選編(1942-1949)》,第88頁。
[47] 江滿情:《論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動對華僑力量的依靠—以籌款活動為中心(1894-1911年)》,《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48]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華僑檔案史料》(上),第454頁。
[49] 林金枝:《僑匯對中國經濟發展與僑鄉建設的作用》,《南洋問題研究》1992年第4期。
[50]《為取締民信局之呼吁》,《申報》1930年4月10日。
A New Point of View on the Research of Pixinju——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ZHOU Yu-b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9, China)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Qiaopi(remittance); Pixinju(remittance enterpris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xinju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CAC).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l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re utilitarian-oriented,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to obtai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Pixinju builds connections among overseas remittances, expatriates and overseas Chinese dependents, and remittances attracted the real focus of the government. The social status of expatriates and rela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is related to remittances.Though the Pixinju and the OCAC are connected due to overseas Chinese, their interests are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en there wa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ixinju and the postal service, the OCAC would intervene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overseas Chinese, but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protect the remittance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name and the practice causes the OCAC unable to provide a stable protection for the Pixinju.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secure the support from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c power, the OCAC of Chongqing government built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ixinju. However,the oppression of Wang puppet government caused the Pixinju to experience the lowest situation during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ixinju and the OCAC,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s utilitarian.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at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 and their relatives, are burdened with unbearable weight due to this policy.
D634.1
A
1002-5162(2017)04-0074-10
2017-03-20;
2017-08-08
周瑜斌(1985—),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郵電史、金融史。
*本文系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編號CXJJ-2013-365)項目成果。
[責任編輯:密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