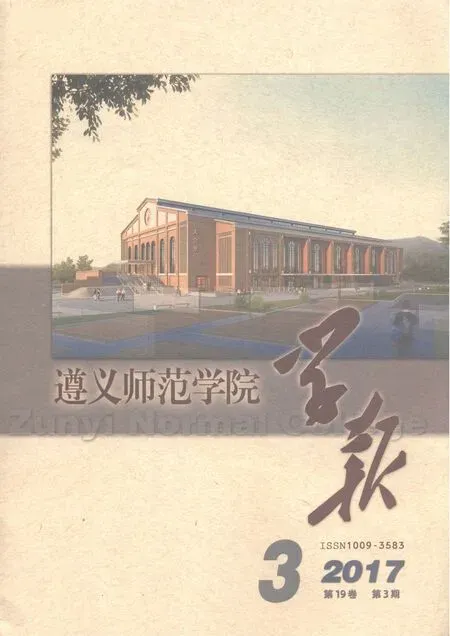關(guān)于“長征學”構(gòu)建的框架問題
馬強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400715)
關(guān)于“長征學”構(gòu)建的框架問題
馬強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400715)
在討論“長征學”理論與方法中,其構(gòu)建框架是最基本的內(nèi)容與基礎。文章認為,“長征學”應由長征學術(shù)史與長征文獻史料學、長征軍事學、長征歷史地理學、長征文藝學、長征歷史人物、長征歷史事件、長征精神與思想、長征歷史遺跡的保護與開發(fā)等組成,而長征學術(shù)史的回顧、總結(jié)、梳理與長征文獻史料的匯編是目前奠定這一新學科的當務之急。此外,長征的研究應該突破傳統(tǒng)黨史、軍史和政治史的思維模式。構(gòu)建“長征學”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學術(shù)工程,需要所有有志于長征研究的學者共同努力。長征學的理論建設與學術(shù)框架的構(gòu)建是其中兩個主要構(gòu)件,前者首先基于對長征更有高度的歷史哲學審視及其歷史終極意義的思考,還包括中國與世界歷史上同類事件的比較研究。
紅軍;長征學;學科構(gòu)建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史詩。今天,長征的意義早已超越軍史、黨史、政治史范疇,成為中華民族克難攻堅、奮發(fā)向上的精神符號,當然也成為以歷史學為主的多學科研究對象。以1936年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最后到達陜北為標志,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迄今已經(jīng)整整過去80周年。以更概括性的話語來說,長征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紅軍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軍離開各自的蘇區(qū)根據(jù)地北上陜甘的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長征更是深刻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走向,并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長久的影響。紅軍長征勝利至今已經(jīng)整整80年,歲月的流逝不僅沒有使紅軍長征從歷史記憶中淡出,反而在經(jīng)歷了80年之久的歷史變遷后顯得愈加厚重。
紅軍長征的研究實際從紅軍到達陜北不久就已開始,而且很快為國際社會所關(guān)注。近80年來出版、發(fā)表回憶、宣傳、研究紅軍長征的著作、論文層出不窮,據(jù)學者不完全統(tǒng)計,早在2006年有關(guān)紅軍長征的論著就多達19000部(篇)①吳曉軍、董漢河:《十年來紅軍長征研究綜述(上)》,《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的不斷開放寬松,許多禁區(qū)被打破,對于長征的研究也日趨客觀、求真、平實、多元,這使得長征的研究隨著時代語境的與時俱進不斷推陳出新,出現(xiàn)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長征研究逐漸打破傳統(tǒng)“左”的教條束縛從政治層面開始走向?qū)W術(shù)層面,突破了純粹歌頌與宣傳式的早期模式;第二,從宣傳、歌頌轉(zhuǎn)向復原、重構(gòu)、求真與反思;第三,紅軍長征出現(xiàn)多元思維與多學科研究態(tài)勢;第四,長征研究向細化、具體化、個案化發(fā)展。上述種種現(xiàn)象表明,長征研究已經(jīng)不再是單一的中共黨史與軍事史學的研究,已經(jīng)形成一門有特定內(nèi)涵而外延在不斷延伸擴大的專門學問,這就需要對長征和因長征而衍生的諸多歷史文化現(xiàn)象進行專門研究。
構(gòu)建長征學學科體系的條件目前已經(jīng)成熟,近年來四川、甘肅、貴州等地不斷有學者提出創(chuàng)建“長征學”學科體系問題,并進行了理論探討①胡學舉、李滿意、李后強等:《呼吁建立“長征學”》,《四川日報》2012年12月26日;吳曉軍、張發(fā):《繼承革命傳統(tǒng)構(gòu)建“長征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4日。其中裴恒濤《“長征學”建構(gòu)的相關(guān)問題探析》(《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對長征學的若干研究現(xiàn)狀、學術(shù)史及其理論與方法等作了較大范圍的探討。貴州省遵義市2015年還成立了“中國(遵義)長征學學會”,選舉產(chǎn)生第一屆學會的理事會,會議選舉曾祥銑為會長,黃先榮為常務副會長、秘書長,參見《人民網(wǎng)·遵義》2015年1月25日報道。,長征學作為一個新的專門研究學科呼之欲出,需要我們從理論與實踐方面加以系統(tǒng)反思與建構(gòu)。筆者不揣淺陋,將近年有關(guān)“長征學”建構(gòu)中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初步陳述如下,以期拋磚引玉,希冀學界更多同行關(guān)注并研究。
一、關(guān)于長征學術(shù)史與長征文獻史料學研究
長征學,顧名思義是有關(guān)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的學問。一個專門學問從學理上是否能夠成立,是否能夠成為學術(shù)研究對象,首先取決于其是否有較長時段的學術(shù)研究歷程并且有相當豐富的學術(shù)成果積累。長征的研究幾乎可以追溯到長征尚未結(jié)束之時。陳云于1935年8月赴莫斯科共產(chǎn)國際作《關(guān)于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向共產(chǎn)國際匯報中央紅軍北上轉(zhuǎn)移的艱難過程。《報告》經(jīng)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為題于1936年在共產(chǎn)國際主辦的機關(guān)刊物《共產(chǎn)國際》上發(fā)表;隨后又以“廉臣”名義在巴黎《全民月刊》發(fā)表《隨軍西行見聞錄》,是最早以長征親歷者身份發(fā)表的宣傳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紀實性文章,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文獻價值。1936年為配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陜北保安采訪,毛澤東曾號召經(jīng)歷過長征的同志寫長征回憶錄,于是就有了1942年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這部十分珍貴的早期紅軍長征文獻。2004年劉統(tǒng)整理、注釋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尤其值得重視。此書以1954年出版的內(nèi)部資料《紅軍長征記》為底本,重新收入了多篇解放后被刪掉的紅軍回憶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歷史原貌。
《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由中央總政治部宣傳部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刊印發(fā)行。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就經(jīng)過在延安采訪紅軍領(lǐng)袖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China),又名《西行漫記》。1935年7月至1936年5月年范長江以《大公報》記者身份深入西北采訪,公開報道紅軍長征與西北社會,并在系列新聞報道基礎上匯編成《中國西北角》,具有重要的新聞史價值。新中國成立后,紅軍長征成為最重要的紅色革命史內(nèi)容,上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索爾滋伯里重走長征路寫作出版《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前不久發(fā)現(xiàn)的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英文雜志《Life》用7個8開整版報道了中國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消息,其中有介紹延安紅軍的照片多幅。
長征的學術(shù)史研究是構(gòu)建“長征學”首先要回顧總結(jié)梳理的工作。建國60多年以來,隨著共和國前進中的風風雨雨,長征的研究也走過了曲折變遷的歷程。不同階段的政治語境下長征研究的側(cè)重面也各有特色。近年來隨著紅軍長征研究日益向求真、復原方向發(fā)展,一批紀實性質(zhì)的早期紅軍長征文獻及其研究著作得以整理和出版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紅軍長征記》(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二萬五千里》(珍藏本)(上、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親歷記》,都是以最早的長征回憶錄《紅軍長征記》(1942年內(nèi)部印發(fā))的不同版本或以之為底本的匯編資料。還有一些史料編輯成果,如楊勝群、陳晉主編《紅軍長征重大決策見證錄》,王聚英、黃敏主編《大會師——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史料選編》,吳德坤主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政治工作資料選編》等,為長征研究提供了更多基礎性材料。紅軍所經(jīng)過地區(qū)的地方長征史資料近年來也不斷出版,如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紅軍長征西征在寧夏》、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黔中紅流——紅軍長征過貴州》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全史》(1-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朱林著《紅軍長征的民間記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著作的出版,為長征學的構(gòu)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對長征學術(shù)史回顧、總結(jié)、反思卻仍然十分薄弱。個中原因除了以往過分強調(diào)長征研究的政治性、強調(diào)長征史研究為政治服務的一元化思維長期占據(jù)主導地位外,也與相當長時期內(nèi)未能將長征學作為一個新的專門學問、甚至反對將長征問題學術(shù)化對待有密切關(guān)系。
長征文獻的搜集整理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包括中央電報、檔案、紅軍標語、長征親歷者的回憶錄、日記、詩詞、繪畫,新聞等。隨著歲月的流逝,紅軍長征文獻日益珍稀,長征文獻的再現(xiàn)與重大發(fā)現(xiàn)會愈來愈少。當務之急是首先在全國進行長征文獻收藏調(diào)查與摸底,重點除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外,各個與當年紅軍長征途經(jīng)的地區(qū)及其紅軍將士后裔家庭珍藏文獻與文物也要盡快搜集存檔。比如目前保存在冕寧博物館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布告》系1935年5月紅軍到達川滇交界的冕寧后宣傳、動員彝族群眾參加紅軍所作。類似這樣的紅軍長征文獻現(xiàn)在已經(jīng)十分罕見。
在全面整理的基礎上,有組織、有計劃地整理出版長征文獻叢書,以使長征文獻這樣具有特殊革命意義的紅色記憶能夠長存史冊。但紅軍長征文獻的整理受不同時代政治語境和諸多忌諱的影響,也經(jīng)歷了“選擇性”、“凈化性”過程,如《紅軍長征記》從1942年初版起,不同年代的版本與文章入選變化都很大,實際上把不少保存有早期面貌的長征記述資料剔除在外,這是十分遺憾的。這一現(xiàn)象即使是一些紅軍長征親歷者的回憶錄也概莫能外,如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一氓回憶錄》對紅軍在遵義期間的回憶就非常完整①據(jù)劉統(tǒng)研究,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寫了很多生活的樂趣,比如到了會理,他們打土豪,一邊吃臘肉一邊看《桃花扇》,這些生動的描寫后來在1954年再版的《紅軍長征記》中都給刪了。1990年代出版的《李一氓回憶錄》引用的仍然還是刪節(jié)版。。另外一些曾經(jīng)參加長征并且具有重要影響的領(lǐng)導人,后來脫離了革命陣營,或者犯了“路線錯誤”解放后長期被“黜廢”的長征重要人物的生平資料,如張國燾、陳昌浩等人的長征資料就長期無人問津,面臨湮滅消亡的危險,這是需要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在紅軍長征文獻搜集整理中,應該超越政治斗爭的是非曲直糾葛,而不應該厚此薄彼。
二、關(guān)于紅軍長征軍事學
首先,長征是軍事行動,紅軍長征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悲壯而傳奇的篇章。在裝備、人數(shù)均處于懸殊條件下,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軍沖破國民黨數(shù)十萬重兵的圍追堵截,艱難穿越在西部崇山峻嶺,越雪山,過草地,經(jīng)歷大大小小數(shù)百戰(zhàn),創(chuàng)造了血戰(zhàn)湘江、四渡赤水、勇奪婁山關(guān)、飛奪瀘定橋、突破臘子口、奠基直羅鎮(zhèn)、強渡嘉陵江等著名經(jīng)典戰(zhàn)役,最后終于沖破敵軍的重重圍剿,勝利到達陜北。這其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徐向前等紅軍將領(lǐng)非凡的軍事指揮藝術(shù),紅軍將士英勇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等,都是一筆重要的歷史軍事文化遺產(chǎn),值得研究總結(jié)。當然紅軍長征途中的軍事,有勝利,也有失敗,如悲壯慘烈的湘江戰(zhàn)役,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指揮的首戰(zhàn)—土城之役,紅軍均受到巨大損失,但失敗與勝利有時又是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互為因果的,正是土城之役的失敗,才有了毛澤東率領(lǐng)紅軍在黔北山區(qū)“四渡赤水”,反復穿越,創(chuàng)造了長征史上的神來之筆,紅軍也就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衷心敬佩。關(guān)于紅軍長征軍事史,徐占權(quán)、陳力、翟清華、王建強編著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其中包括《中央紅軍征戰(zhàn)記》、《紅二方面軍征戰(zhàn)記》、《紅四方面軍征戰(zhàn)記》、《紅二十五軍征戰(zhàn)記》、《三大主力紅軍大會師》五大分冊,是第一部涵蓋紅軍長征全過程的軍事史著作。但該書出版距今已經(jīng)二十多年,無論是對紅軍長征全局的總體把握,還是評價側(cè)重包括資料征引方面現(xiàn)在看來都存在一些明顯不足,有大而不高、全而不細的缺陷。尤其對紅四方面軍長征史的記述比重較小,且在對紅四方面軍歷史作用評價方面仍然帶有傳統(tǒng)“左”的印痕。在紅軍長征軍事研究中,一要加強研究紅軍軍事戰(zhàn)略的演變。紅軍從撤出瑞金開始長征,但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的失敗是長征的直接起因,因此第五次反圍剿及其軍事失敗應該是紅軍長征軍事史研究的源頭。從瑞金蘇區(qū)到遵義會議前的長征是在李德、博古、周恩來“最高三人核心團”指揮之下,開始的軍事遠征目標是去湘、鄂西與紅二方面軍會合。這一階段過去在所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思維的束縛下,實際上缺乏客觀研究,大多給予簡單的否定。遵義會議前,紅軍敗多勝少是事實,但也并非完全失敗,李德等也并非一無是處。如突破前三道封鎖線中,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小組還是運用一系列軍事斗爭謀略,取得了一些勝利。李德早在廣昌戰(zhàn)役失敗后就提出要撤離中央蘇區(qū),周恩來利用內(nèi)線成功與廣西軍閥陳濟棠達成秘密協(xié)議,得以“借道”通過粵北,使紅軍安全通過蔣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鎖線。謝一彪考證早在1934年3月底,李德就向博古提出要準備一次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廣昌戰(zhàn)役失利后,中央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李德再次提出主力紅軍進行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建議。迫于嚴峻形勢,臨時中央不得不考慮戰(zhàn)略轉(zhuǎn)移問題。李德受中央委托,起草相關(guān)的戰(zhàn)略計劃。福建事變發(fā)生后,李德、博古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事變的分析還是比較正確的,但由于中央軍委大多數(shù)同志不同意在軍事上直接支持十九路軍,再加上受中央上海局和共產(chǎn)國際錯誤觀點的影響,李德拒絕與十九路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進而實行打擊“中間派”的關(guān)門主義,失去了聯(lián)合反蔣的大好時機,使蘇區(qū)反“圍剿”戰(zhàn)爭形勢惡化①謝一彪:《中央蘇區(qū)時期的李德》,《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其次要深入研究紅軍突破敵人重兵包圍的軍事藝術(shù)。紅軍長征面對重兵圍追堵截,幾乎無日不戰(zhàn),數(shù)度陷入絕境,卻多次化險為夷,這其中是怎樣屢屢渡過難關(guān)、化解險情的?應該將這些傳奇般的勝利一一剔除神秘化歌頌,轉(zhuǎn)化為基于歷史地理實際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結(jié)合的研究。
再次,要重視對紅軍戰(zhàn)斗力與戰(zhàn)斗精神的研究。突破烏江天險,飛奪瀘定橋、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突破臘子口、奇襲婁山關(guān)等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軍事史上的奇跡,這一“奇跡”的必然性是什么?應該從軍事學上給予合理的解釋。“四渡赤水”亦奇亦幻,出神入化,至今要繪制“四渡赤水”行軍路線圖都非易事,何況當時全靠紅軍將士雙腳來回穿梭。紅軍這些經(jīng)典戰(zhàn)役的勝利,固然毛澤東等紅軍領(lǐng)袖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shù)發(fā)揮了“領(lǐng)導”層面上的重要作用,但紅軍指戰(zhàn)員飽滿而激情的戰(zhàn)斗精神也不可或缺。如飛奪瀘定橋的“二十二勇士”,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為了這場決定紅軍前程命運生死時速的較量,完全是將生命置之度外。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冒著槍林彈雨在險江寒索上英勇前進,最終沖過鐵索橋,紅軍進占天全城,大獲全勝,也宣告了蔣介石企圖讓紅軍重蹈石達開覆轍的幻想化為泡影。無論是飛奪瀘定橋,還是強渡大渡河,應該說都是步步驚心的險棋,長征中紅軍如果沒有如此堅定勇敢的革命斗志,要突破險關(guān)、走完長征是不可想象的。
三、關(guān)于長征歷史地理學
長征的成敗與地理環(huán)境有密切的關(guān)系。紅軍撤離蘇區(qū)走上長征的地理原因值得深入研究。現(xiàn)在看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也并非皆因王明路線的錯誤所致。從地形因素看,紅色蘇區(qū)大部分分散于湘、贛、閩、鄂、陜、川邊界山區(qū)地帶,資源十分有限,在國民黨軍步步合圍封鎖下,到紅軍長征前夕,中央蘇區(qū)根據(jù)地經(jīng)濟資源實際上已經(jīng)近于枯竭。瞿秋白被捕后,宋希濂曾經(jīng)與之談話,說何以蘇區(qū)經(jīng)濟蕭條、百姓貧困?瞿秋白坦然承認蘇區(qū)土地荒蕪、人口逃亡的事實,只是將原因歸之于國民黨對蘇區(qū)的圍剿②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見蘇區(qū)的經(jīng)濟地理上的貧困與蕭條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黨中央在陜北十三年,與陜北寬闊縱深的地理形勢和煤炭、石油、畜牧等資源優(yōu)勢有很大關(guān)系。
長征成敗與地理環(huán)境。紅軍長征所經(jīng)大部分為贛、桂、滇、黔、川、陜南山地,但這些環(huán)境封閉、交通難行的西部山地為紅軍的生存并展開靈活的游擊戰(zhàn)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四渡赤水正是毛澤東成功憑借黔東北山地有利地形的軍事杰作。紅軍長征路線中的雪山、草地地區(qū)屬于人煙罕至、環(huán)境惡劣地帶。長征的地理環(huán)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紅軍的長途跋涉充滿艱難困苦,但也使國民黨軍的軍事裝備無法完全施展,加之面對惡劣的氣候和山地、草地、沼澤、雪山地理環(huán)境,國民黨軍在吃苦耐勞方面與紅軍相差甚遠,這也是國民黨軍始終無法真正戰(zhàn)勝紅軍的重要原因之一。過去對長征中領(lǐng)袖人物的軍事思想研究過多地集中在毛澤東個人,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賀龍等往往只是陪襯,以至于一些表現(xiàn)紅軍長征的歷史題材電影中,在研究軍事策略與方案時,毛澤東胸有成竹,指揮若定,而朱、周等只是頻頻點頭,隨聲附和,這當然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但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確有過人之處,善于因地制宜利用具體地形因素及其特殊地理條件,顯示了他過人的軍事智慧。長征軍事地理學今后應加強研究毛澤東、朱德、徐向前、劉伯承等人的集體軍事智慧和軍事地理思想。軍事戰(zhàn)爭總是在一定的空間地域展開,歷史上杰出的軍事家無不重視對地形、地貌的利用,因而軍事家必然要具有豐富的地理知識。而決定戰(zhàn)爭、戰(zhàn)役的成敗除了軍事指揮者的智慧與韜略之外,是否成功利用具體地形因素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地理的重要關(guān)系早在《孫子兵法》中就有明確的揭示,《孫子兵法》有《地形篇》,專講六種不同的作戰(zhàn)地形及相應的戰(zhàn)術(shù)要求。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軍事家,在戰(zhàn)爭年代尤其注重軍事地理知識的運用。毛澤東軍事地理思想目前研究尚十分薄弱,其他紅軍重要軍事將領(lǐng)的研究更是幾近空白。其次,長征軍事地理學還應加強研究紅軍長征重點戰(zhàn)役發(fā)生地的地理環(huán)境,如地形、地貌、關(guān)隘、河流、湖泊、交通、人口、農(nóng)業(yè)等自然與人文地理環(huán)境,這樣才能對長征得出更加科學的結(jié)論。
四、長征文藝學
長征文藝包括頌揚、宣傳、再現(xiàn)長征的詩歌、音樂、小說、戲劇、電影、電視劇等。建國以來由于對文化宣傳領(lǐng)域的重視,六十多年來有關(guān)紅軍長征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數(shù)量頗巨,但缺少統(tǒng)計、整理與系統(tǒng)研究。從長征學的角度進行紅軍長征文學藝術(shù)作品的整理、研究是一項艱苦而繁重的工作。
紅軍長征詩歌。長征詩詞以毛澤東的長征詩詞最為著名,而長征詩詞是毛澤東詩詞的重要篇章,《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guān)》、《清平樂·六盤山》、《清平樂·會昌》、《沁園春·雪》、《十六字令·三首》、《念奴驕·昆侖》都是膾炙人口的革命詩篇。除了毛澤東外,朱德、葉劍英、徐特立、陳毅等也有長征詩詞,應該注意搜集整理。
長征音樂舞蹈。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領(lǐng)導下排練并隆重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曾經(jīng)以重要篇幅藝術(shù)再現(xiàn)了紅軍長征的悲壯歷史;同樣在1965年,中央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之際,由蕭華作詞、生茂等作曲的《長征組歌》就曾公開發(fā)表,并由總政歌舞團排演成功,在北京民族宮禮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轟動。隨后在京、津、滬、寧等城市及部隊巡回演出50多場次,場場爆滿。反映之強烈,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后因江青等恣意破壞而中止。1974年為紀念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四十周年,總政歌舞團再次排演并精彩演出大型音樂舞臺史詩《長征組歌》,是文革中難得的以舞臺藝術(shù)全面再現(xiàn)紅軍長征英雄歷程的經(jīng)典作品,全劇由《告別》、《突破封鎖線》、《遵義會議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飛越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吳起鎮(zhèn)》等組成,樂曲格調(diào)雄壯優(yōu)美,氣勢磅礴,藝術(shù)再現(xiàn)了紅軍長征可歌可泣的英雄歷史。1984年中央歌舞團創(chuàng)作演出的《中國革命之歌》對長征也作了新的藝術(shù)詮釋,但影響沒有前兩部作品廣泛。這些舞臺作品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高揚理想主義旗幟,唱響英雄主義主旋律。《長征組歌》等至今仍然在一些重要革命紀念性節(jié)日里上演不衰,其中的幾乎所有歌曲皆膾炙人口,廣為傳唱,說明其長久的藝術(shù)生命力。但目前對三個不同年代的《東方紅》、《長征組歌》再到《中國革命之歌》中反映長征的政治背景、取材角度與審美傾向等缺乏應有的學術(shù)研究。
長征電影、電視。建國以來電影作為國人喜聞樂見的藝術(shù)形式,在藝術(shù)再現(xiàn)紅軍長征故事方面可謂居功甚偉,成就非凡。表現(xiàn)紅軍長征題材的電影早期有文革前的《萬水千山》、《突破烏江》、《金沙江畔》,文革后有《紅軍不怕遠征難》、《冰山雪蓮》。黎明、王昊和王愿堅等創(chuàng)作的《四渡赤水》,第一次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形象搬上銀幕;王愿堅和師偉編導的《過草地》獨具匠心,讓一群“紅小鬼”成為長征路上的主角;而集體編劇、林農(nóng)導演的《大渡河》則再現(xiàn)了用生命鋪就勝利之路的英雄壯舉。
大型電視連續(xù)劇《長征》,以史詩般的格調(diào)再現(xiàn)了中央紅軍的悲壯歷史,特別重點表現(xiàn)毛澤東由邊緣化的人物逐步重回領(lǐng)導崗位的演變過程,把領(lǐng)袖和政黨作為故事推進的主線和人物思想的主脈糾葛在一起,塑造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的紅軍統(tǒng)帥形象。作品沒有回避長征途中黨內(nèi)高級領(lǐng)導人之間的矛盾,如毛澤東與張國燾、博古、李德、凱豐等人激烈的爭吵,也塑造了朱德、周恩來、博古、張聞天、劉伯承、楊尚昆、林彪、彭德懷等一系列紅軍將領(lǐng)各異的精神風采,革命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交相輝映,是新時期長征題材不可多得的佳作。
長征小說。建國以后,小說是較早表現(xiàn)長征故事的藝術(shù)。王愿堅是以創(chuàng)作長征題材而知名的作家,他的《金色的魚鉤》、《七根火柴》、《黨費》、《草》、《路標》、《足跡》、《標準》等小說作品曾經(jīng)產(chǎn)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黎汝清的《湘江之戰(zhàn)》和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相繼問世。這兩部長篇小說的結(jié)構(gòu)框架完全不同,但卻有著驚人相似的開頭,都把長征途中最慘烈的湘江戰(zhàn)役作為故事和其主要人物的起點。前者是第一次站在歷史發(fā)展和歷史思辨的立場上,沒有回避戰(zhàn)爭的殘酷性,以真實的筆墨再現(xiàn)了血戰(zhàn)湘江的悲壯情景,使作品富有濃重的悲劇色彩。后者則是第一次以全景的方式表現(xiàn)中央紅軍長征險途的波瀾壯闊,將詩的情思和史傳文學的傳統(tǒng)有機結(jié)合起來,把對敵斗爭、黨內(nèi)斗爭和與惡劣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斗爭縱橫交錯在一起,賦予作品以史詩般的品質(zhì)。陸定一回憶長征的《老山界》雖然不是小說,但卻有小說般的感人細節(jié),曾長期被選入中小學課本,在幾代青少年中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王樹增的歷史報告文學《長征》以紀實的手法與生動的描寫從歷史的新高度重新審視長征的重要意義,用文學的形象、紀實的方式細膩全面再現(xiàn)了長征全景畫面①張西南:《關(guān)于長征題材文藝作品的回顧與思考》,《文藝報》2016年9月28日。。
對紅軍長征中普通人物命運的關(guān)注與反思,是新時期長征題材小說較早萌動的思維。喬良的中篇小說《靈旗》②喬良:《靈旗》,《解放軍文藝》1988年第10期。,同樣取材于長征史上敗得最慘烈、意義最深遠的湘江血戰(zhàn)。把一個歷經(jīng)坎坷、飽覽滄桑老人的知覺、幻覺和記憶構(gòu)成的時間和空間作為作品的框架,使過去和現(xiàn)在都越過各自特定的時空而于同一時刻顯現(xiàn),把人物的情感和欲望、善良和殘忍、崇高和渺小、智慧和愚鈍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而塑造出了“青果老爹”這一個極其特別又有血有肉的“逃兵”形象。這部作品把普通人的靈魂的卑微引向了崇高的升華,對人性的深層意識和人的本質(zhì)作了深刻揭示,使革命戰(zhàn)爭歷史文學關(guān)于人的“崇高”的概念獲得了有價值的轉(zhuǎn)換和拓展。誠如作家自己所言,“在湘江邊,我認識了另外一種戰(zhàn)爭”。江奇濤的中篇小說《馬蹄聲碎》③江奇濤:《馬蹄聲碎》,昆侖出版社1991年出版。與《靈旗》著重展示人在歷史、社會、戰(zhàn)爭中“自我”行為的價值表現(xiàn)不同,更多的是通過對少枝等紅軍女戰(zhàn)士如何擺脫死亡的追逐、渴望生存的描寫,特別是通過對女性中人性意識的細致入微的刻畫,展示出了一種生命的力和美,進而強化了人物最終的悲劇命運并增強了歷史的悲劇氛圍,使這些女兵的形象成為歷史悲劇的承受者、體現(xiàn)者,具有強烈的靈魂啟悟和震撼。
五、長征人物研究
艱苦卓絕的長征過程中,不僅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紅軍領(lǐng)袖人物,也涌現(xiàn)出不少具有傳奇色彩的普通人物及其感人故事,犧牲者可歌可泣,幸存者則都是寶貴的革命財富,也使得從長征走過來的大批人物成為日后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八路軍和人民解放軍重要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建國以后成為黨和國家重要領(lǐng)導人。過去對長征領(lǐng)袖人物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等少數(shù)領(lǐng)袖人物上,這固然是由毛澤東同志在紅軍長征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以后舉足輕重的領(lǐng)導地位所決定的,但長征勝利并非少數(shù)人的豐功偉績可以取代,長征領(lǐng)導核心與骨干是一個英雄的群體,今后應該更多研究長征中其他重要人物及其作用,如朱德、張國燾、博古、張聞天、陳云、鄧小平、葉劍英、徐向前、賀龍、陸定一、彭德懷、李先念、賈拓夫等人在長征中的經(jīng)歷、作用及其貢獻也應深入挖掘與宣傳。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作用問題由于受到張國燾叛逃的影響過去研究較為薄弱,同時也影響到對紅四方面軍一些重要人物的評價,如陳昌浩、李特、傅鐘、黃超、劉士模、何畏等有爭議人物,應該如實給予評價并深入探討。紅四方面軍人物的命運后來較為復雜,前程歸宿各不相同,包括徐向前、劉伯承、程子華、李先念、許世友等在建國以后各自的沉浮起落,應該具體人物具體分析。紅軍長征人物研究要突破過去那種回憶錄式的敘述模式,而應當進行客觀的個案追蹤式研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的長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觀概括,而趨向細化與以小見大,更加真實生動。如以往涉及長征時期鄧小平的研究多散見于鄧小平的傳記、自述或戰(zhàn)友、女兒的回憶錄與傳記之中,幾乎都采用了歷史敘述的方式,而未能系統(tǒng)深入去探討鄧小平在長征時期的具體實際地位、景況與貢獻。黃遠聲的《長征時期鄧小平的歷史貢獻探析》對此進行了嘗試,指出作為長征親歷者的鄧小平,在長征期間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宣傳、群眾、政治教育等工作有重要貢獻①王毅、燕文堂:《近十年來紅軍長征新進展新認識》,《半月談》2016年10月24日。,就是一種鄧小平研究有益的嘗試。
長征人物研究除了重要知名人物外,一些經(jīng)歷過長征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同樣值得重視。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報道過的老紅軍女戰(zhàn)士黃海云的回憶②《女紅軍黃海云三過草地的悲壯經(jīng)歷》,《紅潮網(wǎng)》2013年10月29日。,西征軍女紅軍團長王泉嬡坎坷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長征一家人》③蕭青:《長征一家人》,《黨史文匯》1995年第9期。中陜南寧羌縣女紅軍陳亞民一家追隨紅軍生死相依的生命悲歌等,這些小人物的經(jīng)歷雖然算不上轟轟烈烈,但更有傳奇性,更為感人,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與教育意義。
六、長征重大事件研究
長征重大事件包括長征中經(jīng)歷的重要會議、重大戰(zhàn)役、中共黨內(nèi)高層斗爭等。重大戰(zhàn)役如紅一方面軍的湘江之戰(zhàn)、強渡大渡河、臘子口戰(zhàn)役、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東征戰(zhàn)役、西征戰(zhàn)役,過去研究較多,而紅二方面軍的澧水戰(zhàn)役、烏江戰(zhàn)役、甘南戰(zhàn)役,紅四方面軍的強渡嘉陵江戰(zhàn)役,土門戰(zhàn)役、百丈關(guān)戰(zhàn)役、包座戰(zhàn)役、綏崇丹懋戰(zhàn)役,天蘆名雅邛大戰(zhàn)役的具體過程過去則研究較少。實際上這些戰(zhàn)役作為紅軍長征途中的重大事件,不應以非毛澤東指揮就不予重視,無論從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意義作用,還是從戰(zhàn)役過程及因果關(guān)系皆值得深入研究與復原。長征途中的重要會議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會理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榜羅鎮(zhèn)會議等,這些會議過去只是在宏觀敘述中提及,缺少個案的具體研究。有的地方長期以訛傳訛,如俄界會議的具體地點、巴西會議的確切名稱,近年來通過專家學者的實地考察,才進一步得以澄清,研究較過去更為具體確切。
其他如長征與情報信息、長征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長征與國際關(guān)系、長征歷史遺址、長征精神、長征勝利的保障機制、三大根據(jù)地的始末過程與意義評估等也是長征學建構(gòu)的重要內(nèi)容,限于篇幅,一篇論文難以一一道及,但也應具體研究。只有這樣,將來才有可能集眾多學者之手寫出一部《紅軍長征全史》。
七、結(jié)語
“長征學”是一個正在提倡關(guān)注并嘗試構(gòu)建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其理論和方法及其內(nèi)涵、外延均尚在探討之中。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僅僅著眼于長征研究在當代的政治意義層面,而是基于長征及其衍生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早已超越了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本身。
構(gòu)建“長征學”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學術(shù)工程,需要所有有志于長征的學者共同努力。長征學的理論建設與學術(shù)框架的構(gòu)建是其中兩個主要構(gòu)件,前者首先基于對長征更有高度的歷史哲學審視及其歷史終極意義的思考,還包括中國與世界歷史上同類事件的比較研究。隨著歲月的流逝,長征當事人日漸稀少,紅軍長征時代會漸行漸遠,后人對長征的認識也會與時俱進,認識觀念與價值取向也會發(fā)生變遷,但長征作為20世紀一筆重要的歷史遺產(chǎn)卻永遠不會過時與褪色,只是其價值與意義會更多地向精神文化與審美層面轉(zhuǎn)化。在學術(shù)框架的構(gòu)建上,除了繼續(xù)擴大研究的層次外,組織編修大型長征歷史文獻與研究文獻集成是兩項艱辛而巨量的主要工作。研究方法上則需要更加注重多學科、多維度的現(xiàn)代科學方法,如長征文獻的大數(shù)據(jù)庫與電子技術(shù)處理,長征過程的電子虛擬全息空間再現(xiàn)等,雖任重道遠,也大有可為。
(責任編輯:婁剛)
On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Long March Studies”
MA Qia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Constructing framework is the basic content and foundation in discussing“Long March Studi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Long March Studies”should include academic history and literature history about Long March,military studies of Long March,geopolitical studies of Long March,literary and artistic history of Long March,the preserv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ites about Long March,among which review,summary and the sorting of academic history about Long March as well as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bout Long March are the most urgent tasks in establishing the studies.Besides,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for CPC history,milita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be broken through.Constructing“Long March Studies”is a huge project,requiring scholars’concerted efforts.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framework are the major components,with the former on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view of Long March as well as the pondering o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ong March an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incidents in the world history.
Red Army;Long March Studies;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K264.4
A
1009-3583(2017)-0004-07
2016-12-23
馬強,男,陜西漢中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