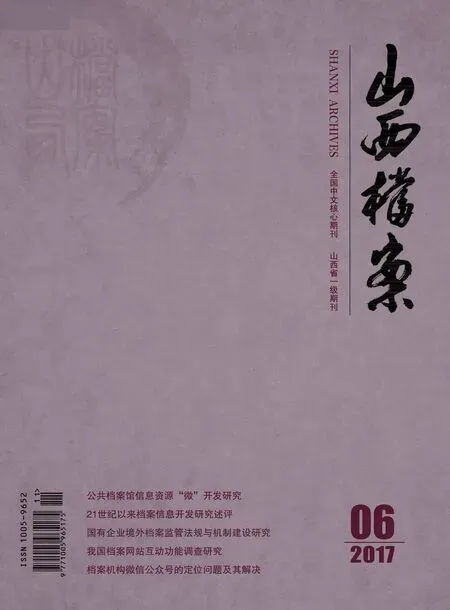論檔案學研究的使命困境
文 / 高大偉
檔案學的研究任務由社會需求決定,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務可被強調為“使命”。檔案學的使命表現為:其一是外在使命,要求研究者總結實踐經驗,將經驗上升為理論,以深刻和普遍的理論來指導直接、具體的實踐,為實踐服務,突出表現為應用理論研究,亦即“檔案科學”的主要內容;其二是內在使命,要求研究者關心檔案學自身的問題,尤其以應用理論為分析對象,檢驗其出發的起點、理論的功能與界限,揭示評價檔案現象的價值準則,即在哲學反思中形成以規范理論為核心的“檔案哲學”,進而完善檔案學理論體系,促進完整意義上學科形態的形成,最終確立檔案學學科地位。檔案學的內在使命與外在使命相互依賴、缺一不可,要求研究者應科學地處理理論與實踐、應用理論與規范理論的關系。
回顧學科史,中國檔案學自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走出蒙昧,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跋涉攀登,體察并滿足著實踐的需求,思考并構建著自身的學科體系;發端于十九世紀初的外國檔案學,從古典走向現代、從現代步入當代,也無不延續著它的創立者的傳統——“尊重全宗”的實踐原則和把檔案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學術自覺。雖然在學科史中這兩項使命的履行都有一定的體現,但檔案學的發展仍受“使命困境”的羈絆。
一、理論與實踐
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檔案學研究中常被議論的重要問題便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1]。在這個問題上,被批評最多的學術研究是理論脫離實踐,“人們對檔案學理論脫離實際(引者注:這里的實際主要是檔案工作的實踐)的批評連續不斷,甚至可以說幾乎難得有不批評檔案學理論脫離實際的時候”[2]。筆者認為,在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確實存在一些故弄玄虛、故意拔高的研究情況,有的研究成果疏遠了社會現實,成為了某種私人的無意義的“理論游戲”,表現為被人詬病的應用理論研究蒼白和不實[3]。對此,研究者們常開出“實事求是”[4]的藥方以求根治。然而,檔案學的外在使命,即應用理論研究陷入的最嚴重的困境,乃是實踐對理論的傾軋。之所以筆者持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在一門應用學科中,理論脫離實踐的問題雖然可能有廣發性,但也不具備根本性,揣摩一下“實事求是”這個“廣譜性”藥方就能明白這一點,虛空的理論不會獲得什么應用的“市場”,自然難成氣候。而對于一門科學而言,實踐對理論的傾軋則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常表現為研究群體的方向性失誤,并且這種傾軋也是導致理論脫離實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具體研究中,雖然檔案學的應用性較強,但并不能對理論持輕視與排斥的態度[5]。可惜,很多研究對此并沒有重視,檔案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基本要求常被“敷衍”。一些研究或過于注重實踐,片面強調經驗對檔案工作實踐的意義;或認為,如果檔案學不能直接解決實踐的操作性問題、技術性問題,便是理論脫離實踐;或追捧學科理論實用和功利,并以此作為檢驗理論的標準,比如盲目追逐某一時期的政治話語、國家政策和實踐項目。這三種態度和做法,以飽受爭議的符合論真理觀來要求理論符合實踐,殊不知理論與實踐雖有聯系,但本為兩物。這些態度和做法,雖然有些已經被學界糾正,有些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注意,但它們并沒有徹底消失,它們時常將自己隱藏起來,在理論研究背景發生變化時,以及在檔案學研究者梯隊更新和學術分工模糊時,便侵擾學術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在某些新事物出現時,以實踐工作的思路來對待檔案學理論研究的做法是相當危險的,它暴露出研究者“在思維模式與社會角色之間的錯誤”[6],“如果檔案學的理論工作者在潛意識中始終認為,他們的價值只有在‘參與政務’中才能實現的話,那么結果只有兩種,其一是造成兩種不同主體沖突不斷……其二,造成理論主體對實踐主題的從思想到人身的依附,具體變現為前者的理論永遠是后者附庸,是對政策的忠實解釋和補充”[7]。
這也就是說,檔案工作實踐所需求的法律、經濟、政策和技術等要素,檔案工作實踐在新形勢下的某種可能“出場”狀態,不能沒有節制地不考慮具體情況而統統放到檔案學理論的架閣之上并樹立為檔案學研究的最高理想。很多問題本屬于一種組織工作范疇,只有實際的組織才具備角色優勢和相關資源,很多價值的訴求或許只是研究者個人的追求而非學科本身所需。雖然檔案事業常被視為檔案學發展前進的強大動力,檔案事業也在謀求與時代的進步合拍,檔案學也被認為應該與檔案事業水乳交融[8],但兩者并不是沒有邊界的。檔案學者應該與檔案事業保持適當的距離,而不能使應用理論研究成為檔案工作的注解[9]。反之,如果檔案學者過分焦慮于某一時期檔案工作實踐的方方面面,必然會在實踐中擇選出一些熱門領域,圈劃出一些熱門詞語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極易產生出一些空洞概念甚至是偽命題,也往往會因自己知識結構、社會角色的問題而使承接的某種實踐任務不可能完成;反過來,這些空洞概念、偽命題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會在理論脫離實踐的問題上火上澆油,影響引導學術研究的各種“規劃”、“指南”的方向性,也會產生廣為學界詬病的脫離社會現實的“某某檔案學”、“檔案某某學”或者“某某學”,使得檔案學的理論體系看似包羅萬象又“與時俱進”,實際正在以龐大架構下的自我陶醉去傷害學科價值。
實踐對理論的傾軋,直接影響了檔案學外在使命的完成,使檔案學的重要功能輸出時而表現為方向性錯誤,時而價值大打折扣。不僅如此,這種傾軋也影響到了內在使命的履行。
二、應用理論與規范理論
檔案學面臨著的第二個“使命困境”,是由外在使命而來的應用理論染指于鼎,干擾了檔案學研究的科學思維,造成言說著的決定學科前途與命運的語言虛弱無力,即外在使命嚴重擠壓了內在使命的存在空間。
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檔案學自應在滿足應用的問題上下大功夫。我國檔案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有近五分之四是應用理論領域的具體問題[10],筆者在CNKI數據中進行了粗略搜索,屬于“檔案事業”類目的論文也占了所有檔案學論文數量的五分之四左右。但應該注意,正如軟件產品既需要滿足用戶業務需求,也應具備良好的可靠性、可操控性、可擴充性和人機界面等一樣,倘若檔案學的研究成果僅僅停留于外在使命,在內在使命的完成情況捉襟見肘,那么很有可能淹沒外在使命給“用戶”所帶來的價值——不協調的理論近于沒有理論,甚至其危害也大于沒有理論。
內在使命的捉襟見肘是顯而易見的。目前我國檔案學研究的重點是解決檔案管理的具體問題,忽視檔案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與理論層次的提升[11]。回到檔案學史中,研究者對檔案學自身問題的探索欠缺是檔案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問題[12]。也有觀點鮮明地指出,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檔案學界大多放棄了對基礎理論的研究,轉而去追逐那些功利性、應用性強的對象,嚴重削弱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力量,而基礎理論之中卻仍然有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亟待解決[13]。還原這種現象,相比應用理論的龐大,規范理論表現為嚴重貧乏,相當多的研究者重“術”而輕“學”,習慣于“低頭趕路”,而不知道“抬頭看路”。
在一些研究文本的意識或潛意識里,既然檔案學是一門應用科學,那么只有應用研究才是檔案學研究真正有價值的內容。也就是說,雖然這些研究信守檔案學是一門應用科學的承諾,卻忘記了即便在應用學科內部也有規范理論研究、應用理論研究與技術研究的結構需求。這種完整的學科理論結構的需求,常在“它的理論內容不可能像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那樣抽象和豐富,它不是理論的學科,檔案學終究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研究和學習檔案學及其理論只有與檔案工作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有堅實的基礎”[14]的習慣參照體系的對比中被消解,使得思想的沖力“總是自在自為地向著精神所形成的思想本身的至高處而邁進”[15]。這對檔案學研究來說是難以接受的洪水猛獸。在這些研究看來,檔案學的所有內容似乎都能在應用的沃土中豐收,檔案學者的任務無非是這里插一片水稻,那里播一頃小麥,根本不用考慮培種育苗和市場行情;檔案學的所有內容又似乎都能在應用的管道中流出,檔案學者只需擬定取水、管水、用水的原則,休論好水、壞水、什么是水。這并不是過于偏激的指責,正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稍有深度的理論研究,往往被指責為‘脫離實際’,……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進行深刻的基礎理論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搞理論研究的人,不是力求理論的深刻,而是怕理論的高深,結果只能流于浮泛”[16],“長期以來,對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檔案學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研究環境比較惡劣。一方面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對檔案學基礎理論缺乏了解和認識甚至抱有某種偏見,從而導致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無辜地背上了‘玄’、‘虛’、‘空’的惡名,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者也得不到學界的尊重與承認,所做的工作也被認為是一種‘務虛’和‘無用’的浪費行為”[17]。
對學科內在使命的這種輕視和偏見態度,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學術自覺,只能尊其為“應用自覺”。或許會有人質疑道,“我們解決了實踐問題,奠定了工作原則!”、“實踐問題那么多,豈能坐而空談?”“我們在滿足實踐需求中締造了檔案學!”“理論為什么要那么復雜呢?”誠然,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有滿足實踐需求的外在使命。但若僅僅將從實踐得來的知識填放在那看似條理清晰實則存在著概念模糊、矛盾,理論不全面、不深刻的應用理論系統;若只滿足于沉浸在這系統之中,對支配應用理論研究的規范理論缺乏必要的反思,從不曾認識到自己所出發的思想的前提假設及其局限性,難道我們不應對其反思嗎?難道學者們不應在思想上經歷一番邏輯的洗練或自我批評,檢驗已建立理論的可證偽性嗎?這正是我們的內在使命。倘若我們能扭轉對檔案學自身問題研究的偏見,真正將其視為學科之所需,將有助于我們擺脫內在使命的困境。
三、結語
在檔案學學科體系中,由于各種原因,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的主流分類思路應被審慎對待。在這種分類思路下,基礎理論已經成為應用理論的藏身之所。檔案學的主體內容只能是屬于應用理論的檔案事業管理學、科技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尤以檔案管理學最為強勢。其表現為,目前通行的各種“檔案學概論”(也就是目前的基礎理論)類教材的很多重要內容(比如“檔案事業”的部分)應屬于檔案管理學的范疇;檔案學的宗旨也被視為“解決檔案尤其是檔案管理實踐中的原理、原則、方法、技術等方面的理論問題,為人們認識檔案與檔案管理現象、做好檔案管理工作提供理論武器”[18]。雖有研究者指出,檔案學形成了以應用檔案學和理論檔案學為兩大類的檔案學學科體系,涉及基礎理論、應用理論和應用技術[19],但這里的理論檔案學也不過是基礎理論的別名,非為本文所談的規范理論。筆者認為,既然我們認識到了目前對學科自身問題研究的不足,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行動:如果仍要繼續使用基礎理論這一名稱,就必須對目前的基礎理論做出梳理,本該屬于應用理論的就還給檔案管理學等分支學科,而基礎理論應以規范理論為主,在檔案學理論體系中十分有必要為應用理論與規范理論劃清界限,消弭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的隱患;如果將“檔案學概論”視作一種面向剛跨入檔案學領域的初學者教材,那么它可以有應用理論的內容介紹,但如果將“檔案學概論”視作一種檔案學的“終極”,那么它應以規范理論為主,“檔案學概論”也就類似于“檔案哲學(引論)”、“檔案認識論(知識論)”、“檔案學觀”等。
還應注意,以前曾有過關于檔案定義、檔案學研究方法(比如“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檔案學的價值等基礎性問題的大量討論。除了這些問題,在今天也出現了對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的發掘和探索,可以說有關檔案學內在使命的研究沒有發生完全的歷史斷裂或消失。然而,經得起時間考驗和理論證偽的成果數量并不樂觀,很多研究成果的內容與價值常被學者們所質疑。就連認為一味追求理論完善是沒有出路的一些研究文本,也常帶些矛盾的心理:檔案學仍處于前科學,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在理論研究中也出現了一批追趕時髦、熱門理論和術語的學術泡沫。對于這些現象,有學者總結認為,目前檔案學術研究存在開創性成果不多、理論深度不夠、學術活動偏少、團隊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有待拓展和學術規范亟待建立的問題[20]。當然,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使命困境”了,而是更多地涉及檔案學的價值、研究環境等內容了。
[1][4]王景高.改革開放與檔案學理論建設[J].檔案學通訊,1998(6):22.
[2]陳永生.檔案學論衡[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105.
[3][17]蔣冠.對當前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思考[J].檔案學研究,2006(4):13-17.
[5]張輯哲.當代中國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J].檔案學通訊,1996(4):26.
[6][7]胡鴻杰.化腐朽為神奇 中國檔案學評析[M].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74.
[8]張輯哲.當代中國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J].檔案學通訊,1996(4):23.
[9]管先海.對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若干思考[J].北京檔案,2006(4):26.
[10]王景高.關于十年來我國檔案學發展的評價問題:回顧與展望[M].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23.
[11]王應解.檔案學的嬗變[J].檔案學通訊,2006(4):8.
[12]陳永生.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檔案學關于自身問題研究的回顧與評價[J].檔案學通訊,1999(4):16-20.
[13]管先海.檔案學理論研究價值取向的理性思考[J].浙江檔案,2006(2):5.
[14]吳寶康.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125.
[15]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2.
[16]王李蘇,周毅.回顧與展望——對我國檔案學發展的歷史考察[J].上海檔案,1988(9):7.
[18]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36.
[19]馮惠玲.走向輝煌(之十)——檔案學理論的發展與繁榮[J].中國檔案,1999(10):6.
[20]周耀林,等.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價值、存在的問題及發展趨勢[J].圖書情報知識,2009(7):32-33.